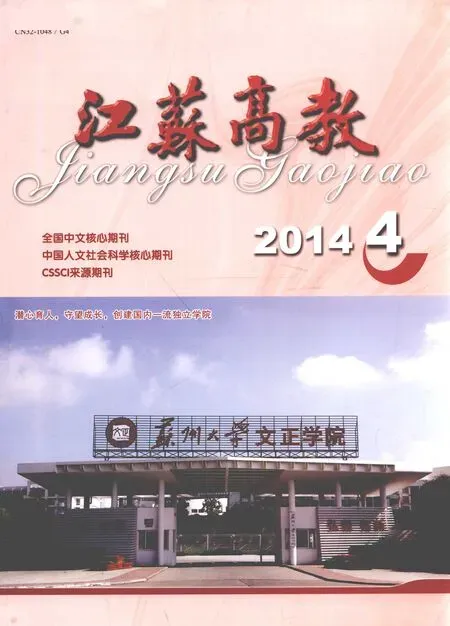蔣夢麟個性主義教育思想及其實踐
韓立云
(南京大學歷史系,南京210093)
蔣夢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幼年時期讀私塾,熟知中國傳統文化,后又留學美國九年,在美國尤其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過程中,蔣夢麟逐漸認識到中國教育的問題所在,在其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中,他一再強調個人教育的價值,他認為,“欲解決中國社會之基本問題,非尊重個人之價值不為功。吾國文化,較諸先進之國,相形見絀。吾人其欲追而及之乎,則必養成適當之特才。欲養成適當之特才,非發展個性不為功”[1]。就是要改革傳統的忽視個體和個體價值的傳統教育,要實施“個性主義”教育。
一、蔣夢麟的個性主義教育思想體系
(一)“健全個人”是個性主義教育的目標
1919年2月,蔣夢麟在《新教育》創刊號中明確提出“以教育為方法,養成健全之個人,使國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擔重大之責任”[2]。這是他個性主義教育目標的具體內容。
1.養成獨立不移的精神。蔣夢麟認為“吾國青年最大之惡德有二:一萎靡不振,一依賴成性”。萎靡不振就會遇事畏難,欲望減縮,事情無論大小必不會成功;依賴成性,則事事隨別人后面,人云亦云,不可能有新事業的創造。因此要開展新教育,必須要培養具有高尚的精神、凡事須進一步想的、勇往直前的具有獨立不移之精神的青年,這種青年越多,社會進化速度就越快。
2.養成精確明晰的思考力。蔣夢麟認為中國人最缺乏思考力,在《和平與教育》一文中,蔣夢麟感嘆:“甚矣,吾國人之不思也!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斷,或奴于成見,或出于感情。故全國擾攘,是非莫衷。其斷事也,不曰大約如此,則曰差不多如此”,為此,蔣夢麟提出“以教育方法解決中國之問題,當養成精確明晰之思考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事事當以‘何以如此’為前提。學校之中,當注重論理學科學兩者,以為思考之基礎。”也就是說,要養成學生的思考習慣,事事都要問“為什么?做什么?這個是什么?究竟做什么?”培養學生對事物的懷疑精神,對知識要求得精確。在蔣夢麟看來“欲養成頭腦清楚之國民,科學其圣藥也。”
3.養成健全的人格。蔣夢麟認為,健全的人格既包括身體的健全,也包括精神的健全,要保持二者的平衡。對于“身體雖弱,不可過于愛惜,精神愈用而愈出”的觀點,他認為當有界限,要適度。“逸居飽食,以養精神,則精神必僵;若但用精神,不強體力,則終亦必踣”,更何況是在近代文明非常復雜的情況下,枵朽的身體是絕不能擔當的。結合自己的經歷和中國的傳統狀況,蔣夢麟非常重視學生要進行各種“活潑運動”,改變過去舊式教育把兒童都變成“枯落的秋草”式的教育,使學生真正成為體力、腦力、感情等方面自我發展的活潑潑的人。因此,蔣夢麟主張在重視科學教育的同時,還要重視體育和美育,以發展學生的體力和感情。
4.具有改良社會的能力。蔣夢麟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角度指出,社會的狀況與個人的幸福有很大關系,“若我但把個人發展,忘卻了社會,個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因此,學生應當具備改良社會的能力,學校則要承擔起“養成學生改良社會的能力”的責任。一般父母送孩子讀書有兩種希望,一是光宗耀祖,一是拯世救民。蔣夢麟雖不完全反對這種認識,但他認為這不應當是學校的注重點,學校的宗旨是“養成社會良好的分子,為社會求進化”。
5.具有生產的能力。中國以前的教育培養的不過是迷信政策的人或者是奴役國民、魚肉百姓的“主人翁”,今后的新教育要培養“要講生產,要講服務,要知道勞工神圣”的人才。社會的生產是每個人勞動的結果,如果每個人都能勞動,則社會的生產自然就豐富了;如果大多數人都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社會將無法生存。而且只有使國民有獨立生產的能力,才能不畏強權,不需要當權者施仁政。
(二)“尊重個人”是個性主義教育的前提
蔣夢麟認為個人的價值存在于每個人的天賦秉性當中,新教育就是要尊重個人的價值。“吾人若視教育為增進文明之方法,則當自尊重個人始。”而所謂的“自由”、“平等”、“民權”、“共和”、“言論自由”、“選舉權”、“代議機關”等都是尊重個人價值的表現和結果。
(三)“自動自治”是個性主義教育的方法
蔣夢麟非常重視學生自動自治,“我愿辦學校的人獎勵學生自治”。對于自動的人才,他是這樣解釋的“具有遠大的眼光,進取的精神。事事改良,著著求進步。人未能敢行者,我獨行之,人未能及知者,吾獨察先機而知之。此所謂自動的人才也。”他說“好的生活是自動的,他人帶動的不是好的生活,學生自治是自動的一個方法”,也就是說,蔣夢麟希望通過學生自治來實現把學生培養成健全個人的目標。至于具體如何去培養,蔣夢麟在《學生自治》一文中作出了詳細的說明:
首先,要培養學生自治的精神。他認為,精神是全體一致到處都是的一種公共意志,這種意志是一個團體形成的基礎,也是自治的基礎。學生自治并不是一種時髦的運動,也不是反對教員的運動,也不是一種機械性的組織,而是在自治精神基礎上形成的組織,“是愛國的運動,是‘移風易俗’的運動,是養成活潑潑地一個精神的運動”。這種自治精神我們在學校里可以稱其為學風。
其次,培養學生自治的責任。學生自治是要大家去干自治的事業,這樣大家就負有了重大的責任,這些責任包括四種:(1)提高學術程度的責任。對于學術的提高,學生應當從自身做起,學生問問自己是否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不是把責任推到教師身上,做到了這一點才是真正的自覺。(2)公共服務的責任。自治是自愿的、自動的對于團體的服務,對團體做公益的事情。這種服務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積極的互助,是做對團體有益的事,是增進公共利益的辦法;另一個是消極的自制,是不做對團體有害的事,是消除亂源的辦法。(3)產生文化的責任。學生自治團體要多生產文化,也就是要多設各種學術研究團體,如演說競爭會、學生講演會、戲劇會、音樂會等,互相研究,倡導各種文化生產事業。(4)改良社會的責任。學生自治團體不僅要在校內負有責任,還需要與社會接觸,學生要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改良社會,使社會文明程度慢慢提高。
最后,注意學生自治中的問題。要處理好幾種關系。第一,學生個人和教職員個人或團體的關系,學生個人行為不當,學生團體應當干涉,教職員也應當幫助,共同維護學校的名譽;第二,學生團體與教職員個人的關系,學生團體應該歡迎教職員的忠告;第三,學生自治團體和教職員團體的關系,如果雙方出現沖突,兩方要平心靜氣,推誠布公,大家來共同討論解決問題。注意到了這幾方面的問題,學生自治活動就能夠順利進行。
(四)增進個人價值,促進社會文明是個性主義教育的意義
蔣夢麟認為,個性主義教育就是要發展個體的特性,以教育的方法增進個人的價值,同時教育涉及種種問題,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做人之道”,即增進人類之價值,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欲言人類之價值,當先言個人之價值……人類云者,不過合個人而抽象以言之耳”,因此他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來說明個人的價值問題。他認為動物群中各個個體沒有什么大的差別,而人之所以比動物高貴,在于人具有人類的共性之外,還具有其特殊的個性,這個人與那個人相差甚遠,“有上智,有下愚;有大勇,有小勇,有無勇;有善舞,有善弈,有善射,有善御:皆以秉性與環境之不同,而各成其材也。”將你、我、他每個人所稟賦的特性發展“至大至剛”,也就養成了有價值的個人,增進了個人的價值;而今日文明先進國家的社會,都是由個人結合而成的,因此個人價值越高,人類價值、社會價值就越高,“個人之價值愈高,則文明之進步愈速”。
二、蔣夢麟個性主義人才培養的實踐
蔣夢麟不僅有系統的教育思想,也有著豐富的教育實踐經歷。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學歷任教務長、代理校長、校長職務,對于北京大學的組織體制、管理體系與人才培養體系都非常熟悉,在重振北京大學的過程中,他繼承了蔡元培時期的一些基本理念,同時又結合當時的教育思潮與他自己的辦學理念,對北京大學的教學科研與行政管理體系進行了改革和發展。在人才培養方面,除了繼續強調學術與健全人格的養成外,蔣夢麟還特別強調專業化人才的培養與大學生改造社會的能力,突出學生個性的發展。為此,他調整院系結構、加強理科各系的建設,為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的中興奠定了基礎,也為個性化人才的培養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實踐體系。
為了更好地培養健全個人,在課程設置方面,蔣夢麟除了重視培養學生基本知識的基礎課程外,還特別重視專業化課程的設置。蔣夢麟在課程上采取“精純主義”原則,“北大以前課程失之廣泛,不但應有盡有,而且不應有亦盡有。其不需要之課程,徒耗國家財力,并廢學生有用光陰,于其研究之專科,并無裨益,故近來對此種課程,毅然裁去”[3]。因此,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課程經過整合后,更突出了其專業性,這體現了蔣夢麟加強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
蔣夢麟要培養的具有健全個性的人才,不僅要有研究學術的興趣和能力,同時要有改造社會的能力,這就要求對學生進行專業化培養。以史學系為例,其具體的做法是將四年的課程分兩部分進行,前兩年主要教授史學之基本科學及通史,后兩年學生則可以選一種專史進行專門研究,由原來的通史學習進而進入到專門史的研究中。當時這種專門史的研究包括中國分代史研究、中國百年史研究和西洋百年史研究,其中以中國分代史研究為重點。學生可以在三年級跟隨教師研究分代史如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選擇其中之一,共同研究,專攻兩年;如果是在四年級選則只能就某一分代史作部分的研究,而中國近百年史分成民國前和民國后兩部,西洋近百年史分為歐戰前和歐戰后兩部,對此不專重教授,而重在指導學生搜集史料及新發生的史實,進行組織記載練習。這種在基本知識和方法教授基礎上的分類培養的方法,在沒有進行專業設置的情況下,對于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一種很好的嘗試。
要服務社會,必須一方面要了解社會,另一方面要將知識運用于社會,因此蔣夢麟時期的北京大學繼續了蔡元培時期的做法,組織學生進行社會實踐,包括參觀、考察、旅行等多種方式。1932年經濟系參觀團43人在唐山、大沽、天津等處參觀新興產業、生產營業、勞工狀況及各地歷史變遷,各項考查都有詳細的筆記。同年,北京大學教育系四年級學生教育參觀團二十多人,由教授楊亮功領導,赴華北各地參觀,先至天津,后至濟南、開封、太原等地,該團體分文書、交際、事務、攝影四組,分別負責資料記錄整理、與當地教育機關及學校聯系交流等各項事務。此外其他各系,如地質、政治、法律、化學、史學、物理等系學生都會有一些參觀考察的經歷。要求學生在考察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并預先參考一定書籍,考察回校后必須有詳細報告,于考試前交本系教授會評閱,并將成績以較高的百分率計算于畢業成績內,可見當時北京大學對于學生實習的要求非常嚴格。
此外,蔣夢麟主持時的北京大學還注重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動研究能力的培養。在教學方法上除了純演講式外,還采取讓學生自主學習研究,定期做讀書報告的方式。有些教授為培養學生的研究與寫作能力,所授課程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比如1931年胡適布置的《中國哲學史》的論文題目有:(1)試述《抱樸子》的思想;(2)試論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地位;(3)試從道宣的《廣弘明集》及《續高僧傳》的“護法”一部中鉤出北周至唐初佛道兩教斗爭的歷史;(4)試述王安石的重要思想;(5)試述顏元的重要思想[4]。從這些題目來看,任何一個問題都不是幾句話就能闡述清楚的,也不是從哪本參考書上能夠找到現成答案的,這就要求學生在對教授所提出的要求閱讀的材料有一個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礎上進行概括和總結才能得出比較完整、系統的答案。這對于學生閱讀能力、寫作能力以及邏輯能力的培養都是很有幫助的。
三、結語
蔣夢麟個性主義教育思想既是對杜威教育哲學的繼承,也是對中國社會和教育的反思;既是其個人對當時教育改革的認識,也是對當時教育思潮的反映。杜威強調教育要以兒童為中心,反對教師為中心,蔣夢麟認為教育必須從受教育者自身固有的特性來發展,即是對杜威思想的繼承。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破了中國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個體解放、個人自由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在教育上個性教育也發展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當時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5]。此外,胡適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也都紛紛提出發展個性教育,以至于1922年新學制的標準中就有“謀個性之發展”一條,可見發展個性教育是當時教育發展的潮流趨向。這種教育思想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也成就了一大批專業化人才,為社會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在當下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發展學生固有特性的這種教育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1] 蔣夢麟.蔣夢麟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 張愛梅.蔣夢麟教育思想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06.
[3] 蔣夢麟將赴歐參觀教育[N].申報,1934-07-13.
[4] 北京大學日刊(2842號)[N].1932-05-26.
[5] 蔡元培.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4: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