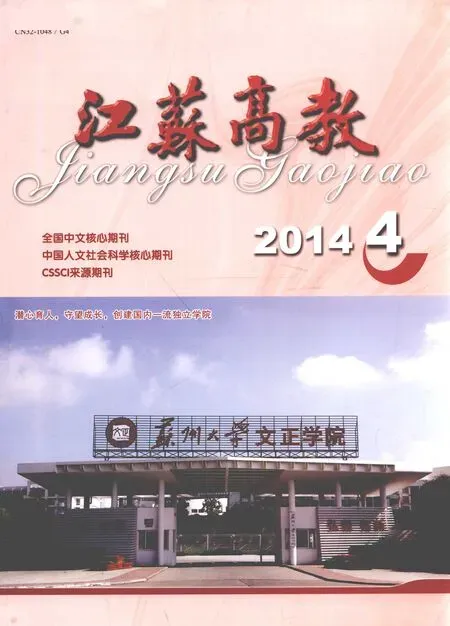蒙古國教師專業發展困境探析
馬少美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210093)
一、文字改革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蒙古國文字是表音文字,它是適應游牧經濟的發展需要而創造并得以使用,是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體系。因政治需要,蒙古國文字進行了兩次改革,一次是西里爾文改革,一次是文字拉丁化改革,而蒙古國文字的文化載體作用在蒙古國的教育發展過程中卻被忽略。目前,蒙古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語同文不同的國家,一種語言同時使用三種文字。這三種文字是傳統回骼蒙古文、西里爾蒙古文和拉丁蒙古文。
回骼蒙古文屬阿爾泰語系,它的書寫方式自上而下,從右向左,這種文字在中國內蒙古地區普遍使用。在蘇聯授意下,1946年1月1日,蒙古改用西里爾文,成為官方文字。西里爾蒙古文酷似俄語,該文有35個字母,13個元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1個硬化字母和1個軟化字母。西里爾文發音與回骼蒙古文一樣,表達意義與俄語不同。這次文字改革與教育改革同步進行,其課程目標、課程知識、課程內容、教學法、教學評價等全改為蘇聯模式,改革由蘇聯專家指導,全國統一用蘇聯認可的教材及圖書資料,這是蒙古國現代教育改革的一個起點,這次教育改革大約持續了20年左右[1]。由于改革的跨度太大,文字結構,包括語法、語義、語用等方面結構的消失,原有的感知外界的途徑也隨之喪失,文字改革摧毀了蒙古國人的心理基礎,造成文化傳承的斷層,基本達到了“去中國化”的目的。
蘇聯解體后,蒙古國開始有限范圍使用回骼蒙古文。1990年6月蒙古國政府作出《關于組織全民學習傳統文字的活動》的決定。1995年政府又通過回骼蒙古文國家計劃。在小學課程改革中,回骼蒙古文課程得到恢復。
早在1930至1941年間,蒙古國曾醞釀文字改革,并成立拉丁文字研究委員會,旨在使傳統文字拉丁化,為文字改革進行必要的準備,因蘇聯方面干預而未果。20世紀90年代,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網絡通信的需要,蒙古國開始使用拉丁字母拼寫蒙古語,拉丁蒙古文現已普遍運用于網絡。2003年,蒙古國大呼拉爾頒布了“拉丁字母國家計劃”。2003年12月23日,經國家標準與計量委員會批準,2004年1月1日開始執行“用拉丁字母轉寫西里爾蒙古文的標準”。至此,蒙古國形成了三種文字并存的局面[2]。
美國教師專業發展理論代表者波亞茲和科伯認為,教師生涯成長模式是由低到高模式,即完成任務模式、學習模式和發展模式。完成任務模式的教師以完成工作為目標,學習模式的教師追求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發展模式的教師則努力達到自己設定的最高目標[3]。語言是社會的黏合劑,是文化的基礎,是教育的工具,新語言文字的出現,直接影響課堂師生的交流及教學效果。在蒙古國文字改革的適應期,教師勢必以完成工作為目標,西里爾文改革如此,拉丁文改革亦是如此,這是文字改革后教師專業發展所處的應然狀態。
二、“教育券”培訓制改革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曾在美國名校就讀的現任蒙古國政府高官,竭力將本國的教育政策與體系全面西化。美國當代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密爾頓·費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思想,即政府的教育經費以教育券的形式撥給消費者。蒙古國運用“教育券”思想,將在職教師教育納入市場化、民主化,旨在通過競爭,提高在職教師教育質量。1998年、2001年蒙古國政府先后起草并頒布了關于教師“教育券”法令,實行在職教師培訓的“教育券”改革。
教師培訓的“教育券”改革是蒙古國擺脫教育財政困境的舉措。蒙古國外債高筑,自1991年至2009年蒙古國外債已增加至26億美元[4],國家財政難堪重負,經濟嚴重依賴外援。政府允許多邊國際組織、非政府機構、私人、地方企業和大學參與教師培訓,教師“教育券”培訓制納入蒙古國在職教師培訓中。蒙古國只保留一所由國家投資的師資培訓機構——在職教師教育發展學校。
“教育券”改革是在職教師培訓觀念的變革。蘇蒙友好時期,蒙古國的教師在職培訓由國家負擔,每五年一次。“教育券”打破國家壟斷,核心是賦予教師“選擇權”,獲得“教育券”的教師先閱讀各個培訓機構的公告,然后依據自己的專業興趣選擇培訓機構[5],在職教師機會均等培訓體制徹底消失。
“教育券”改革是在職教師培訓形式的變革。蒙古國在首都、省會、縣城建立“教育文化中心”,作為教師培訓組織機構。“教育券”法明確提出教育部與財政部每年聯合確定第二年“教育券”的數量,定出每種形式的教師培訓份額,由各級“教育文化中心”直接交給教師或管理人員。1998年“教育券”法規定了教師和行政人員在職培訓中券的管理、分配核算的具體程序,確定了三種培訓形式,即中央研討班、省級研討班和正規的獨立學習“垂直型”的培訓形式。
“教育券”改革強調競爭性,選擇性,忽視了公平性。“教育券”改革后出現了諸多問題。由于制度不健全,“教育券”在分配過程中難免行賄受賄,任人唯親,權力缺少制約,“教育券”難以惠及普通教師及貧窮落后地區教師;教師間沒有共同交流、學習提高;“教育券”培訓內容抽象,很難貼近實際教學,教師知識來源于外來專家的研究,教師以接受這些知識為目的,由于缺少專家面授的培訓交流機會,現在的校本培訓已成為人與微機交流的獨立學習狀態。“教育券”改革無論是“教育券”的獲取還是知識的獲得,受益的只是高級教師,蒙古國教師群體專業發展極不平衡。
三、后殖民化的教師專業發展
課程知識、課程內容作為傳承前人文化經驗的重要工具,受制于國家的權力和意識形態。教學法、教學評價則體現教師、學生和課程政策制定者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培養師資著稱的蒙古國立教育大學(原蒙古國立師范大學)公共課以哲學、政治研究、財政理論、社會邏輯學等課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西化后的蒙古國課程目標、課程知識、課程內容、教學法、教學評價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
蒙古國奉行多邊外交政策,并明確美國為“政治鄰國”、“戰略鄰國”,歐洲國家為“教育鄰國”,業已表明蒙古國全面西化。美歐一手操縱蒙古國文字拉丁化,旨在從語言上打開缺口,加速對其文化和思想的影響,蒙古國成為西亞的土耳其,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等美歐列強的殖民統治國家為期不遠[6]。
蒙古國的文字改革與教師“教育券”培訓制改革,是典型個案,也是其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改革的一個縮影。教師專業具有獨特的社會功能,承擔社會責任,體現社會價值并在教育行動與教育活動領域得以呈現。凱爾克特曼把教師專業發展看作一個高度個體化的學習過程,是個體教師與空間情境及時間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教師專業發展的空間情境是指教師工作于其中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環境,教師專業發展的時間情境由教師個人生活經歷和教學生涯構成[7]。蒙古國傳統文字斯拉夫化用了20多年時間,至今西里文尚在使用,拉丁化已有十多年時間,拉丁蒙古文還不完善,但文字拉丁化是大勢所趨。文字改革嚴重制約蒙古國教師專業發展,國際教育形勢發展迅猛,蒙古國教師正在失去教師專業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教師“教育券”培訓制改革難以立竿見影。在現代教育制度下,國家為公民提供教育機會而形成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教師無論是在教學還是在謀求自身提高方面都無完全的自主權,因為政治變革,教育發展路徑中途易轍,直接導致蒙古國教師專業發展舉步維艱。
實行民主化后,蒙古國政府不斷易主,在政治博弈中親美歐派勢力越來越強,蒙古國由親蘇轉而親美歐,教育思想、發展觀念進行了徹底的變革。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曾有過文化傳承被割裂的歷史教訓,蒙古國精英們深刻意識到本民族性格中的依賴性對國家發展的侵蝕,努力實現民族教育的復興。世界本就是多元文化的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能走向世界,不必把“拿來主義”奉若神明,削足適履,數典忘祖。
[1] LKhamsuren Tumenbaatar.蒙古、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比較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3.
[2] [6]齊心.蒙古國文字:一個文化傳承與政治取向問題[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9):50-54.
[3] 肖麗萍.國內外教師專業發展研究述評[J].中國教育學刊,2002,(5):58-60.
[4] 文虎.蒙古經濟發展現狀及困境[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11,(4):31-35.
[5] Gita Steiner-Khamsi.Vouchers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in Mongolia:Transitional,Postsocialist or Antisocialist Explanation.[J].Chicago Journals.Vol.49,No.2,May 2005.
[7] 盧乃桂,鐘亞妮.國際視野中的教師專業發展[J].比較教育研究,2006,(2):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