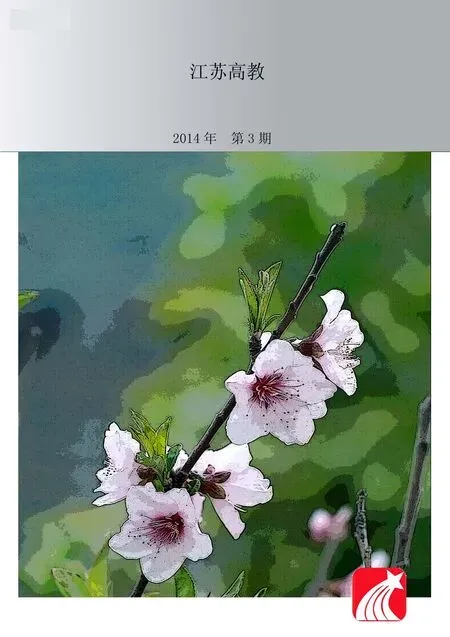論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與戰略支點的選擇
高樹仁,宋 丹
(1.遼寧教育研究院 教育史研究所,沈陽 110034;2.大連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與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發展方式是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熱點問題。隨著我國社會轉型和教育制度變遷,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加速對高等教育的強力滲透,關于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話題被不斷提及,并已成為根植于教育改革和發展實踐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我們對于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態度,關系到現階段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評價,也涉及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走勢。要解決或緩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道路上日漸尖銳的老問題和日益復雜的新問題,必須拓展到轉變發展方式的框架中去尋找對策。因此,建構新的發展方式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
一、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根本內涵及其規律
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確是需要進行理論探討、百家爭鳴、形成社會共識的一個概念。高等教育作為不斷嬗變、動態發展的教育形式,與其他社會活動一樣,存在自身運動發展的方式。正是這種方式的不斷更替,推動著高等教育在自身內部邏輯活動中,持續不斷地演進和發展。所謂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呈現的諸多發展性特征的總和,是實現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的方法、手段和模式的統一,它包括了從微觀教學到宏觀決策的諸多領域。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是高等教育組織機構為適應環境、實現目標而采取的路徑選擇,其實質是秉持什么理念,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動力,通過什么途徑,體現什么價值,實現怎樣的發展。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從根本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在起點、過程、結果等多個角度呈現的總體特征,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在規模、速度、結構、質量、效果等方面是否實現了理性發展。
高等教育經歷了漫長歷史演進過程,并依然處于變革和發展運動中。適切的發展方式對于不同階段高等教育的改革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毫無疑問,高等教育的發展源自外部社會力量的推動,也源自對自身發展方式的不斷反思。改革開放三十余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在制度建構、結構優化和規模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發展方式理性化程度不足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在高等教育發展的低級階段,對教育發展目標的關注常常局限在一些外在的顯性目標上,如教育規模、發展速度、學校數量等;只有當高等教育發展進入更高階段,才會更注重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隱含目標和適應性等問題。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學習、調整和創新的動態過程。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改革想要取得較好的效果,我們需要對高等教育發展方式進行詳盡的系統分析,了解目前高等教育系統發展方式的現狀及所存在的問題,識別影響改革的關鍵因素,并最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實可行的建議[1]。總結我國學術界對高等教育發展問題的研究,我們認為實現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需要遵循以下規律性的要求。
首先,要考慮三個基本要素:質量要素,其實質是我國高等教育在規模發展之后的一種更高追求,是質量不斷提升的過程,這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務和剛性要求;結構要素,高等教育自身存在各種結構關系,高等教育結構又與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產業布局結構等發生著密切聯系,只有處理好各種關系,在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的復合系統中,才可能實現高等教育的自我完善和社會適應性的整體提升;公平要素,即以包容性協調增長為核心,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整以不斷實現高等教育權益的均衡,將高等教育的公平理性“公共化”。
其次,要考慮三個基本規定:創新驅動,旨在關注高等教育發展的創新,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實踐的有效集成,是整合內涵式發展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未來教育等主題教育,聚合而成的一股新的教育思潮總匯;協同推進,旨在改變原有相對單向、封閉的發展思維,建立科學合理、均衡發展、包容合作、知識共享、開放共建的高等教育體系[2];以人為本,指新的發展方式應突出“學生中心”的價值取向,其基本問題是觀念的更新換代,從見“物”不見“人”的“外延式”發展轉向“以人為本”的內涵式發展。
最后,要堅持三個基本原則:效益性原則,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利益協調機制,對辦學要素進行整體優化,提高現有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益[3];可持續性原則,立足于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重新審視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動力,推進教育實踐邁向新境界;自主性原則,從根本上解決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動力問題,超越政府為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直接推動,實現高等教育的自主調整與自我優化。以上三要素、三規定和三原則是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依據。
二、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維度與路徑
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突破點往往發生在社會需要和高等教育內在發展邏輯的交叉點上。高等教育各種發展要素是承接社會需要的載體,也必然成為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最基本變量。教育要素在結構方面的變化、內涵方面的優化以及組合方式上調整成為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基于此,本文以高等教育發展所依靠的教育要素作為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將要素所共有的結構維度(structure)、制度維度(system)、技術維度(skill)確定為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三重維度(簡化為“3S”維度)。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就是高等教育在結構屬性、制度屬性和技術屬性三個維度尋找最佳耦合或最滿意耦合的過程,以此構建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模型。
高等教育發展要素的耦合有三個維度,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也相應地存在三種路徑。
其一,教育要素組合方式轉變型,主要指在“結構維度”上教育要素組合方式的轉變。轉變教育發展方式,必然涉及對教育發展過程要素的重新組合和調配。而調整教育結構為發展要素的有序流動與有效組合提供了宏觀框架。調整高等教育結構,提高教育體系的整體效能,是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對于高等教育協調發展至關重要,在諸種轉變方式中具有首要地位。
其二,教育要素運作方式轉變型,主要指在“制度維度”上教育要素運作方式的轉變。制度帶有穩定性、長遠性特點,它關系到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續的發展[4],是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關鍵和核心內容。制度設計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突破口。落后的制度使各種教育要素結合松散,不可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制度創新能夠改變管理落后的狀態,也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
其三,教育要素作用方式轉變型,主要指在“技術維度”上教育要素作用于教育對象的方式的轉變。教育必然涉及技術、途徑和手段的選擇,這直接影響甚至決定教育要素作用于教育對象的質量、速度和效果。基于技術維度的教育要素作用方式轉變,必須整體考慮教育技術、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教育技能等方面的內在聯系,通過系統性的變革,改造教育過程,煥發教育、教學的生機與活力。
以上分析,是出于論證需要而把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維度和路徑從系統中分離開來討論。事實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是一個多維的支撐系統,結構是前提,技術是基礎,制度是保障[4]。這些維度與路徑在對高等教育發展轉型中的作用是交互作用實現整體效能的。三種路徑在各自維度上通過各自力量的整體一致或此消彼長,便發生了推動或抑制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演進的效果。總之,在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過程中,諸多因素的作用通常以這幾種方式發生:或者其中一種在某個歷史階段、某種情況下顯著突出,并暫時掩蓋其他路徑的效用;或者幾種路徑此消彼長;或者幾種路徑發生共時作用,盡管作用力并不均衡。合適的路徑選擇,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情境決定的。
三、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支點
教育發展方式研究的核心是戰略選擇問題,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要立足于結構維度、制度維度與技術維度,尋找與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路徑相契合的戰略突破口。我國要想實現由高教大國向高教強國的轉變,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以教育結構、教育制度、教學模式為支點牽動教育全局,實現教育發展方式的漸進性變革。
(一)以結構優化為戰略支點,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要素的有效流動與組合
教育結構對于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動態的歷史過程來看,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存量改造和以增量帶動結構優化的復合式發展道路。在大眾化初期,如果說以增量發展為主,存量改革為輔,主要依靠擴大規模、增加投入實現發展的話,那么新時期轉變高等教育發展則需要為以存量改革為主,加強對教育結構優化、質量提高、效益發揮的關注,引導教育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因此,必須強化“結構優勢”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采用宏觀、中觀、微觀相結合的方法,把高等教育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放在高等教育發展全局的高度去重視,實現以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為主的內涵發展道路。在宏觀層面,政府要把結構布局調整作為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戰略性工作,推動大學科學定位與合理分層;在中觀層面,把科類結構調整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著力點,創新評價模式和資源配置方式,引導大學特色發展;在微觀層面,把專業結構調整作為轉變大學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實現高等教育結構優勢與我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資本結構、城鄉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和持續的變化有效對接。整體上,將實現高等教育的科學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各項工作的落腳點,使政府對于高等教育結構的規劃和調控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針對我國高等教育結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切實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結構理論的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從而為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宏觀調控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以制度創新為戰略支點,依靠制度建設驅動內涵轉變
制度創新是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邏輯起點。適宜的制度不僅是促進教育自身發展,增強教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性和實現學生全面發展的根本保障,還是通過影響教育要素投入和要素效率來重塑教育發展的動力。如何獲取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制度功能,已成為推動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也必然成為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高等教育的制度建設主要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完善制度體系,規范政府行為。現有的國家政策文本相對宏觀,對于教育制度、體制的規定還有不完善、不充實的突出問題;地方各級教育政策則明顯“單薄”,省級統籌制度尚在初級探索階段[5]。當前,亟需頂層的制度設計,加強中央和地方以及各部門之間政策措施協調以及改革步調的銜接。二是完善制度內容,處理好五種關系,即政府調控與市場調節的關系、政府宏觀管理與高校自主辦學的關系、全國一盤棋調控與地方積極性發揮的關系、轉變評價方式與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的關系以及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6]。三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增值教育變革的內生動力。我國高等教育正經歷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系、由集權管理向分權管理、由大學行政化向去行政化運作的三大轉型,我國大學的發展也理應回應這種轉型,通過喚醒學校主體意識、增強變革能力、拓展自主發展空間為主要任務,以現代大學章程為載體,以現代大學治理結構為依托,以合理的權力結構為保障,把深化大學制度改革與轉變發展方式一同部署,進而建立有利于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體系,系統推進改革。
(三)以教學模式改革為戰略支點,以質量內驅力對接公眾教育需求
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不僅涉及制度因素的生長和結構性變動,也必然會引起實踐層面教學模式的變化。教學模式改革包含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過程中微觀實踐層面的技術、方式、手段、技能等綜合因素。教學模式改革攸關教育改革的方向與成敗,是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型的又一戰略支點。影響教學模式改革的“變量”眾多,其中,教育技術是承載教育改革與發展向前飛奔的一條軌道。目前在教學領域,最活躍的因素,也是變化最快、討論最多的可能就是教育技術。教育技術變革了教師教學方式,創新了課程的表現方式,也顛覆了學生的學習方式。我們很欣慰地看到,在高等教育大發展進程中,教育技術也沿著有利于優化教學模式、教學效率的軌跡而變化、發展和出新。然而,教育技術的進步并不足以完全替代傳統教學形式。變革教育的方法和組織形式也是教學模式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通過優化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和要素,提升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和質量,扭轉僵化教學制度的失衡導向;變革教育組織形式,解除班級授課制和批量生產對教學組織的長期綁架,向個性化、分散化、遠程化的教育組織形式轉型,使教育回歸本源活力。另一方面,加強教師的技能培訓和教學研究,為教學模式改革提供人力支持與智力支持[7],為教學模式改革的專業性和科學性奠定基礎。通過現代教育技術與傳統教學手段的完美融合,形成高等教育內部的質量生成機制,是提升高等教育內驅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路徑。
[1]范 明,等.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的系統分析[J].江蘇高教,2013,(4):47.
[2]周 進.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國家高等教育理念的轉變與創新[J].江蘇高教,2013,(4):10.
[3]張德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高等教育的歷史責任[J].中國高教研究,2013,(2):2.
[4]高樹仁,張秀萍.高教強省的三重意蘊及其超越性[J].江蘇高教,2012,(1):45.
[5]楊潤勇.新背景下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政策調整問題研究[J].教育研究,2011,(3):28.
[6]劉國瑞,林 杰.關于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幾個問題[J].現代教育管理,2013,(2):16.
[7]賈繼娥,褚宏啟.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三條路徑[J].教育發展研究,20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