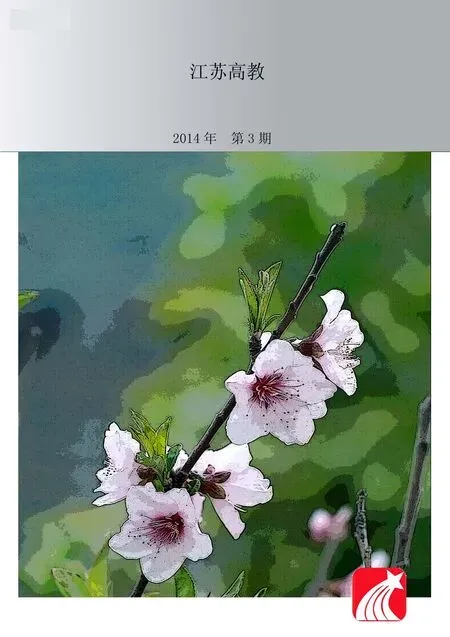高校去行政化:預算改革的路徑
劉家明
(嘉應學院 政法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
一、高校去行政化預算改革的必要性
高校去行政化的預算改革是牽涉到人的核心利益的問題,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中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但切中的是高校行政化的要害,不改不行。預算改革有助于從根本上走出高校行政化的困境,同時對于推動其他路徑的改革十分重要。
預算是一個涉及權力、權威、文化、協商一致和沖突的過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1]。預算也是一種討價還價、相互妥協的政治過程,是高校內部達成共識的契約。預算項目反映了政治價值和官僚行動的方向,預算過程及其方式反映了權力的較量和權利的配置。難怪威爾達夫斯基說,如果你不能制定預算,你怎么治理[2]?換言之,如果高校沒有一個好的預算體制,如何實現善治?因此,高等教育預算體制和高校預算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應成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基本路徑之一。
在高校行政化的基本動力因子中,主要有文化觀念(如官本位意識),也有制度(如集權體制)和結構因素(學術組織相對于官僚組織的天然劣勢)。其中,最根本的是對制度掩蓋下的權力和利益的追逐。可以說,趨利動機是高校行政化的最基本動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正是高校的財務預算和收入分配等經濟利益從根本上驅動著高校管理體制的行政化。高等教育領域和高校內部經費的分配也是高校行政化加速、加重的重要驅動因素,經費和黨政權力的結合足以主導、制約高校包括高校學術研究在內的幾乎所有工作和活動。因此,高等教育財政預算體制和高校內部的預算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二、高等教育財政預算體制改革
我國公立高校在辦學經費方面形成了以政府撥款為主的預算收入體制。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通過教育部及各省、市、自治區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來對資金進行配置。行政撥付資金的獲得,一方面憑借各高校自己到政府部門去跑關系、求人,行政級別的高低和高校自身名氣在撥款中舉足輕重;另一方面,財政撥款分為經常性經費與專項經費,專項經費比例較大,但很多專項經費卻因為行政指令并不能“專”,高校對專項經費的堅持往往會付出失去經費的代價,為了“保財”只能聽命于政府行政,自主權在利益驅動下遭遇重挫(王蘇琪,2010)。
具體來說,我國現行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基數加增長”的撥款方式,即地方高校部門預算按“兩大類”(基本支出、項目支出)、“三大塊”(人員經費、日常公用經費和項目經費)進行編制。在此基礎上,考慮當年事業發展與變化情況確定撥付的事業發展數額。二是“綜合定額+少量專項補助”的撥款方式,這是基于定員定額的原理,即按學生不同層次和專業折算的學生當量,以學校不同類型的生均定額標準核定高校正常經費,并設立少量專項資金。由上述財政撥款方式可以看出,學校實際得到的教育經費與學校的規模、辦學層次緊密相連,地方高校唯有通過“擴張”帶動發展(夏再興等,2010)。因此,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財政預算體制是政府干預高校的重要緣由和路徑,對政府財政投入過分依賴,也是推動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制度動因之一。
政府在財政預算方面干預高校表現在:確立投資規則,例如對高校內部的各種收費項目和標準進行審批、限制;對不同層次和科類的高校,實行不同的撥款方法和撥款標準,逐步實行基金制,并陸續設立“211工程”和“985工程”專項基金以及教學建設和改革專項基金[3];尤其是近些年,政府對專項撥款的規定有了較大的彈性,對專項撥款的使用時間、使用領域并沒有嚴格規定,以及由于提出預算和撥款到位之間存在較長的時間差,專項經費的年終預算、決算,什么時間批下來,什么時候到位都說不準,財政撥款嚴重滯后;再比如,高校編制人員的工資浮動機制,多久上漲、漲幅多大,也沒有固定和明確,往往需要高校領導通過與政府主管部門交涉、談判去解決。這就為政府的行政干預和高校行政化預設了空間和“理由”。
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方式和財政干預表明,高等教育預算投入體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有一些隨意性,其財政預算帶有很強的集權和人治色彩,以致有了“跑部錢進”、“校長的重要職責就是公關和要錢”,等等說法。這不僅造成高校的公關費用、公務接待費用的攀升和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成為政府和高校雙寡頭之間圍繞著預算撥款進行交易和博弈——政府干預高校、高校俘獲政府——的主要根源。在政治市場中,由于高校產出的非市場性質,以及信息不對稱,政府與高校官僚機構處于雙邊壟斷地位,為高校行政領導和政府主管官員都創造了謀求個人私利的機會和手段,成為高等教育領域尋租和腐敗的多發地帶。
盡管《教育法》規定了“兩個逐步提高”和三個增長,從而在法律上保障了政府的高等教育投入。但由于預算的增長沒有穩定、法定的浮動機制,為政府的行政干預留下了空間。這里對高等教育預算體制改革提出兩點建議。
首先,必須實施高等教育財政預算投入的政策立法,形成與GDP和財政收入掛鉤的高等教育剛性投資比例,并根據地區生活成本和物價指數制定固定的浮動機制,根據高等教育領域可供信息監測的指標,如學生人數及就業率、教師數量和質量等指標,進行預算約束;并對高校的舉債規模和比例相對于高校資產和預算收入做出限制。預算體制的相對剛性,保證了高校預算投入的可預期性,以及約束高等教育投入的自由裁量權,抑制政府和高校官員的個人作用,減少高校向政府的公關動力,意義重大。而且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適合于高等教育預算的政策立法,我國從2011年開始進入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當人均GNP達到一個較高水平以后,在技術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教育經費在GNP中的比例趨于穩定,那時教育投資與 GNP接近于同步增長[4]。
第二,由于不同“級別”的公立高校的投入經費來源不同,中央和地方的投入比例也不同,比例中較大部分來自直接的政府主管部門,而沒有形成統一的、全國性預算投入體制。雖然這樣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負擔,也考慮了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教育投資成本分擔的規律,但是造成了如下后果:驅動高校不斷提高自身的“級別”,找到財政收入上更有保障的“老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落實情況無人監管、無力監管;各地高校投入的嚴重失衡。因此,建議把高等教育的財政預算單列,原來的買單者不變,但撥款賬戶統一由財政部或教育部下屬的全國高校撥款委員會來直接管理、監督,及時公布、評估預算投入情況。通過統一的第三方監管,避免了政府主管部門對高校的直接財政干預以及“下屬”高校不受監管的局面。此外,要建立健全獨立、中立的社會機構的教育投資評價體系,基于不同區域、學校、項目和社會效益等不同維度的評價,不斷完善預算效益評價機制和對預算違規的問責機制。
三、高校內部的預算體制改革
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官僚是由上級任命的執行人,是自利的經濟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效用函數包括如下變量:薪金、所在機構或職員的規模、額外所得、權力和地位,而這些變量的大小又直接和預算撥款規模正相關。尼斯坎南認為,機構預算,包括定期撥款、資助,乃是高層官員的核心焦點,更多的預算在工資、額外補貼、聲望、權力、任免權和機構產出等方面增加了他們的福利,沒有利潤指標,官僚只能追求預算收入和支出的最大化[5]。因此,追求最大預算規模成了高校行政部門的目標,不惜增加工作量、下屬人數和資源浪費,也要實現規模擴張、預算增加和個人從中牟利。預算規模的增加不僅意味著更多的收益、報酬,還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支配權,更容易用資源來創制額外的特權以及官僚機構和職位的吸引力,引發人員增加、級別提高、規模擴張,誘致組織的官僚化。預算最大化動機引發的官僚化,不僅造成高校行政權力過度壟斷和資源浪費,而且容易造成學術行政化、行政利益化、高校庸俗化的后果。
高校的教育浪費現象實際是由高校的預算軟約束造成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所形成的高校財務權利與財務責任不匹配,使許多高校在辦學上追求大規模和高層次,導致學校負債過度和教育資源浪費。高校的行政“晉升”制度也會形成軟預算約束激勵。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模式十分強調職級權威和行政權力,組織中成員的權力直接與其工資、地位、職稱評定和其他待遇相聯系[6]。因此,在這種行政管理模式下,高校管理者很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到追求更高職位和行政權力上來,而職位的升遷通常又與高校管理者任期內的政績有關[7]。在高校財務管理和資金運作中,財務運行體系不夠透明,行政領導行政資源配制權、財權缺少監督、制約機制,財務問題上的違法亂紀現象屢禁不止。因此,高校內部的預算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匹配財務權力和財務責任,減少領導干部“尋租”和腐敗行為。一般性事務管理應與財務管理分開,財務應由單獨機構(例如學校董事會)進行單獨管理和審核,完善績效考核的約束機制,避免出現凡事“一把手”說了算的現象(夏再興等,2010)。
其次,加強經濟責任審計,由高校外部獨立的審計機構對高校財務支出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審計,審計結果實行公告和跟蹤制度,強化教育經費使用監督,保證審計結果公正。
再次,破除高校行政部門預算的漸進主義邏輯,嚴格限制公車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形式的在職消費,公示三公經費,啟動校內預算報告制度和問責機制,對支出項目、程序進行規制。
最后,強化官僚機構的解說責任和外在控制等民主、法治制度,在高校行政系統中引入競爭機制、公共品供給的市場機制、競爭性投標機制,樹立結果為本、競爭導向的績效預算制度,以民主、法治的手段,通過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制約行政高度集權的預算體制。
四、高校收入分配改革
當前的高校收入分配體制掩蓋了許多問題和矛盾,教師也默許高校的擴張和外部行政化的運作,因為高校教職工的收入相當部分來自教育撥款和收繳學費,學校的外部行政化和“擴張”對于全體教職工都有好處。此外,工資收入分配格局一定程度上也掩蓋了高校學術系統與行政系統間的矛盾沖突,表面上看不同級別教師和相應級別行政人員的薪水相差不大。根據雙因素理論,工資的相對公平,只是有助于消除不滿意,但并不能真正提高學術人員的積極性,即成為激勵因素。因為,高校中教師從事的是本位性、創造性的工作,而行政人員的工作是派生的輔助性、服務性的。如果學術人員沒有相對優厚的待遇以及與價值、貢獻相匹配的收入,是不可能真正起到激勵作用的。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必須改革高校收入分配的元制度,包括誰來制定分配政策,誰來執行,誰來監督等主體及其權力的劃分。要改變行政系統對資源和收入進行分配的絕對支配權,實現收入分配的相關權利在科學和民主的分工基礎上實現法治,降低集權和人治的程度。
其次,確定高校收入分配的原則和價值取向。必須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多勞多得、優勞優酬的分配原則,徹底改變基于身份的分配機制和大鍋飯現象,同時突出與高校核心競爭力密切相關的學術價值。具體到工資待遇與級別設置方面,中層行政人員的工資不得高于基層學術人員,中高層行政人員的工資不得高于中級學術人員,以此類推,從而強調學術人員的核心地位和體現大學的學術本位價值,這是從根本上解決高校內部“趨官若鶩”現象的舉措。
最后,將崗位管理和績效管理相結合,將績效考核與績效獎勵掛鉤,根據職責完成情況和創造的價值貢獻進行收入分配。明確部門目標和崗位責任,細化標準,推動績效考核體系的民主化、科學化與法治化建設,實行科學規范、公平合理的獎勵制度,通過基于績效的收入分配制度調動積極性。具體來說,包括幾個方面:一是要建立與能力、績效相適應的收入分配機制;二是建立與崗位相配套的獎懲體系,在收入分配中應堅持按崗定酬、以崗定薪、崗變薪變的具體原則,建立崗位工資與崗位津貼相結合的獎懲體系,實現工資管理由“身份工資”逐步轉向“績效工資”;三是設立向優秀人才和關鍵崗位傾斜的獎勵津貼。
[1]Aaron Wildavsky.Budgeting[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75.p.xiii.
[2][美]阿倫·威爾達夫斯基,布萊登·斯瓦德洛.預算與治理[M].茍燕楠,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302.
[3]陳 超.中國重點大學制度建設中的政府干預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1.
[4]劉志民.教育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52.
[5]Niskanen.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M].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p.8.
[6]周雪光.逆向軟預算約束:一個政府行為的組織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5,(2):135 -140.
[7]龐曉波,黃衛挺.高校預算軟約束的制度成因及其治理[J].中國高教研究,2009,(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