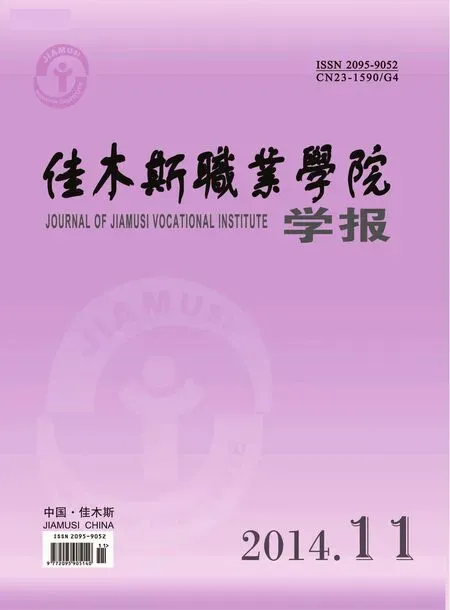霍布斯、盧梭社會契約理論之比較分析
朱慧嫣 陳文華
(廣東培正學院法學系 廣東廣州 510830)
霍布斯、盧梭社會契約理論之比較分析
朱慧嫣 陳文華
(廣東培正學院法學系 廣東廣州 510830)
社會契約理論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的關于國家起源及政府構建的系統理論闡述。在眾多社會契約理論中,其中以霍布斯與盧梭之思想最為突出,霍布斯主張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強大的君主集權制國家,其思想核心為“主權在君”;而盧梭則主張通過訂立契約建立民主共和國,其核心思想為“主權在民”。通過將霍布斯、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放在歷史長河中審視,并結合時代背景,比較契約訂立原因、授權范圍和主權行使方式,充分了解其優缺點,及其可行性,為現代政治生活提供借鑒和指導。
社會契約;主權在君;主權在民
一、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人類不但是自然動物,更為社會動物,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因此,霍布斯,盧梭所處的時代背景,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價值取向。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思想籠罩著集權主義與絕對主義的影子,這與他的生平經歷不無關聯。霍布斯生活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英國,此時,先前發生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會逐漸走下神壇;經濟上,重商主義崛起;政治上,新興資產階級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自1640年,英國深陷內戰泥潭,至1688年光榮革命后才恢復和平。可以說霍布斯的后半生都處在強烈的動蕩與不安中,這種長期的動蕩不安勢必影響其價值觀與人生觀。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說道:“任何政府形勢可能對全體人民普遍發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隨內戰而來的慘狀和可怕的災難相比起來,或跟那種無人統治,沒有服從法律與強制力量以約束其人民的掠奪與復仇之手的紊亂比起來,簡直小巫見大巫了。”[1]133戰爭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他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主權在君”,但他并不鼓吹極端的君主專制,甚至不贊成王位世襲。”[2]11同時,又由于霍布斯曾經擔任過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師,因此霍布斯的理論思想,既遭到教會的反對,又為保王黨所唾棄,更為革命者所不容。
與霍布斯不同,盧梭生活在18世紀中的法國。此時,法國的專制主義達到巔峰,等級分明,階級矛盾難以調和。出生低微的盧梭,一生顛沛流離,他曾擔任過許多職位以謀求生計,深刻地體會了底層人民的艱辛。因此,“平等是盧梭追求的首要目標,他不但主張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更謀求事實上的平等。”[2]14-15簡而言之,他的理想社會是“既不許有豪富,也不許有赤貧。”[3]66“沒有一個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購買另一人,也沒有公民窮得不得不出賣自身。”[3]66盧梭反對奴隸制,他認為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自由,即使再多的財富也無法彌補自由的缺失。放棄自由,等于放棄一切。
二、社會契約訂立原因與授權范圍
霍布斯認為,人性本惡,在自然狀態下,人人處于戰爭狀態。而這種戰爭狀態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敵對與防御,并且每個人都活在隨時喪命的恐懼當中。此時,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如果沒有一直能讓所有人都服從的權威,那么每個人都只會依據自身的欲望而行事,如此,便無法抵御共同的外敵和停止相互間的侵害。于是,理性的人們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聯合起來,每個人都與他人訂立契約,把自身所擁有的權利授予一個人或集體,而這個個人或集體便成為主權者,代表訂約者行使其權力。
霍布斯筆下的主權者具有絕對的權威,人民處于服從地位,對主權者施加的任何懲罰皆為不義,主權者幾乎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被推翻。原因有二:其一,由于主權者承擔訂約者的人格權利為單向授權,事實上主權者并不是訂立契約的一方,所以無論任何時候主權者都不會違反契約;其二,據霍布斯所言:“主權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對任何臣民都不可能構成侵害,而臣民中任何人也沒有理由控告他不義,因為一個人根據另一個人的授權做出任何事情時,在這一樁事情上不可能對授權者構成侵害。”[1]136簡而言之,每個人將自己的權利授予主權者后,主權者的行為便代表自己,而自己無法侵害自己,更無法推翻自己。
盧梭認為,人性本善,自我保全與憐憫是人類最基礎的品質。在自然狀態下,人們互不干涉,獨立生活,無所欲求。伴隨著私有財產與社會分工的出現,人們逐漸脫離野蠻狀態,不再滿足于匱乏的物質生活,因個體能力的差異,造成最初財富不均等的局面。由于存在著種種不安因素,人們為了保全財產與生命,相互聯合,訂立契約。契約條款是每個結合者將其自身與其所有的權利毫無保留地轉讓給整個集體,這個集體即為主權者。“所采取的結合形式能保證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雖全部轉讓給整個集體,但作為集體的一員,能從其他結合者那里獲得自己所讓渡的同樣的權利,從而也就得到了自己所喪失的一切東西的等價物以及更大的力量來保全自己的所有。”[3]20從而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就授權范圍而言,相較于洛克有保留的授權,霍布斯與盧梭都強調必須毫無保留地授權,即把所有權利都授予主權者。盧梭認為,若每個人都保有一部分權利,那么因個體所保留權利大小之差異,勢必會導致裁判的不公,而主權者也因為人民的權利有所保留,其權威亦會遭受挑戰。
三、主權行使方式
(一)主權在君
霍布斯認為,“公私利益結合得最緊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進也最大。”[1]144因為臣民的生存狀態決定著國家興衰與君
主尊榮,所以君主制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結合得最緊密的政體,是最不壞的政體。在霍布斯筆下,主權者享有維護和平權、防衛權、審定各種意見與學說權、立法權、司法權、稅權等各項權利,凡此種種權利皆為保全國家建立時的目的。一旦主權者喪失其中某項權利,或某種權利被分割,則其所處的狀態便會不再是和平狀態,而輕易退回戰爭狀態。
由于國家主權全部集于主權者手中,由此建立起來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優缺點顯而易見。鑒于主權者在其權限范圍內享有絕對權威,在任何情況下,主權者都能調動國內的所有力量,所以,主權者能夠輕而易舉的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抵御外敵或對抗國內的反動勢力,以維護人民的生命安全權。霍布斯認為,主權者之所以為主權者是因為他能夠保障人們的生命安全,如若安全不再,則主權者不再。并且,在主權者絕對權力的威懾下,任何其他人都不敢觸犯法律權威。
君主制的一大難題在于繼承人的選定,這一點霍布斯也意識到了,“君主政體還有一個流弊,是主權可能傳到一個孺子或不辨善惡的人手里。”[1]146但他認為,這種流弊不是君主政體所獨有的,在幾種不同的按約建立的國家中也存在著這種流弊,而這種流弊“只能歸咎于臣民的野心和他們對自身義務的一無所知。”[1]147因為在議會中,少數人不能違抗多數人就像幼主不能反對向他提出的咨議,而需聽從其監護人的意見一樣。
然而在霍布斯筆下,由于主權者并不是契約的參與者,主權的行使沒有任何的監督與限制,因此,這就無可避免的使政權的行使掉入專制的陷阱之中。正如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漢密斯頓認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不是天使而是人,否則,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者內在的控制了。”[4]98-99如果某個人或集體的地位高于其他所有人,他的權力行使不受任限制,那么,就如孟德斯鳩所言,在專制國家,人人也都是平等的,這是因為相較于主權者而言,其他人什么都不是,其生命與財產可以隨意被剝奪。
(二)主權在民
盧梭認為,主權即為立法權,法律不過是公意的宣告,行政權并不構成主權的一部分,“因為行政權力不外是把力量運用到法律而已。”[3]122因此,為了能夠充分保障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人民建立主權者的執行人——政府,并通過全體公民選舉而產生了執政官,行使集體共同授予的權力,保障國家機制的正常運轉。
那么,構成主權的唯一權力立法權是如何被行使的呢?盧梭認為,維持主權權威的關鍵在于人民定期集會,并且在集會上,永遠都應該是以兩個提案而宣告開始的,即“主權者愿意保留現有的政府形式嗎?”[3]129“人民愿意讓那些目前實際負擔責任的人們繼續當政嗎?”[3]129縱觀《社會契約論》一書,不難看出,盧梭極端反對代議制,他認為主權既不能被轉讓也不能被代表,因為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他斷言“凡是不曾經人民所親自批準的法律,都是無效的;那根本不是法律。”[3]120
盧梭似乎也意識到,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之所以能夠實行“直接民主制”的根源在于奴隸制的存在,這使得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公民有大量而充足的時間來辯論及集會。但他相信自由與奴役是不需要并存的,向往自由的人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在他看來,交通不便或是為了實現表決權而產生大量的額外費用等問題,與自由無法相提并論。當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有所沖突時,公共利益應放在首位。然而,他忽略的極重要一點是,人們在實現自己政治主張之前,都必須先解決溫飽問題,奴隸制的廢除使得公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事務上,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由于盧梭始終認為公意永遠是正確的,與公意相反的意志都是不自由的,如果與投票人相反的意志占了上風,只能證明投票人的意志錯了,他對公意有了錯誤的估計。而“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就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3]24-25這種“直接民主制”思想在法國大革命后泛濫成災,成為雅各賓派排擠政敵、實行恐怖統治的武器。
盧梭認為,“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3]84所以,事實上,就行政權的行使而言,盧梭更傾向于選舉而來的“貴族制”,而不是人民直接管理公共事務。
四、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霍布斯、盧梭所處的時代與我們相距甚遠,盡管其思想為歷史時代所局限,具有相當大的激進性、極端性和虛構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思想卻影響至今。其所描繪的社會理想藍圖,對近現代民主進程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國家權威
霍布斯筆下的主權者雖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也僅限于公權(維護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上,對于某些權利,尤其是私人領域的權利,如鑄幣權,監護權等,霍布斯主張由臣民保有,“只要是主權者沉默的地方,臣民就有相應的自由。”[5]事實上,《利維坦》依然具有相當的民主色彩。而在當代,竟出現逆轉的趨勢,隨著國家權力向各個領域的擴張,私人領域所受限制越來越多。
然而,政府以有限的人力與物力,對非公權(私人)領域進行事無巨細地管理,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國家權威也因此而不斷被削弱。古語云:國將亡,必多制。盧梭也認為“刑罰頻繁總是政府衰弱或者無能的一種標志。”[3]43在當代中國公權無處不在,人們事事幾乎訴諸于公權,一些不該由法律解決的私人問題也相繼立法。譬如《老年權益保護法》除了規定對老人要進行物質贍養,也提出了具有精神贍養性質的要求,如要滿足老人精神上的需求等。然而,就對老人進行精神贍養而言,其本身具有的強烈的道德性暫且不表,由于現實面臨的情況紛繁復雜,具體到個體又有所不同,關于何為精神上慰藉、精神需求的標準因人而異,難以界定。精神贍養存在的現實不可操縱性及執行難的問題只會不斷地損害司法權威,浪費司法資源,亦不能對孤寡老人進行切實有效的救濟。學者約翰·格雷認為,“現代國家太弱了,因為它的目標太高,而它本身已成為龐然大物。”[5]
“政治生命的原則就在于主權的權威”。[3]113“利維坦”之所以強大得無懈可擊,在于其權力在有限的領域即維護公共利益的范圍內行使,而不是將一切事物都集中在國家手中。政府施行其權力依賴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即稅收),而在一個國家中,每年的財政收入總是有限的,但這有限的財政收入卻要被分配到各個領域當中,因此,僅僅由于財力所限,就無法使政府在各個領域都能發揮其所希望的作用。為加強國家權威,政府在各個領域的財政預算與撥款
就要有所側重,而在有限的力量中,為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一方權力的加強,另一方的權力就勢必要有所減弱。因此,國家權威的加強,有賴于限制國家權力的無限制擴張,使國家權力專注于公共領域,而退出其不該管也管不好的領域。所以,在經濟領域內,應加強“無形的手”對社會主義市場的影響力,借助“無形的手”不斷完善我國市場競爭機制,對非國民支柱產業實行優勝劣汰。對于私人領域,應貫徹落實“私法自治”原則,減少公法對私權處分的干預,充分保障公民在私人領域內所享有的自治權。
(二)民主政治
盧梭認為,為確保公意的產生,國家應當采取“直接民主制”并且定期召開集會。而在許多城市的國家,為了保障每個公民的主權得以實現,他認為,應當在每個城市都輪流設立政府,再一一召開集會。但現實世界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如果完全依照盧梭的方法來實現民主政治,其機會是十分渺茫的,因此,絕大部分國家都是實行代議制。正如學者熊彼特所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統治是少數精英們的事情,他們通過自由競爭來爭取選民的選票。”[7]當前,我國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實現對國家的管理,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因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人民行使參政議政的權利過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就顯得尤其重要。
選舉,在本質上,就是選民將其手中對國家管理的權力授予給被選舉人,由被選舉人代表選民行使其權力。在我國,人民為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所以,在授權過程中,應當真實地反映出民眾的意愿。我國采取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制度。根據我國選舉法的相關規定,只有縣級以下的人大代表才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人民代表,而市級以上的人大代表則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如此一來,隨著不斷地委托與轉委托,民眾最初的意愿實在難以反映。而在人大代表的構成中,由于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推薦渠道單一,絕大部分的人大代表都是由組織推薦,因此黨員與官員占到其中的絕大比例,所謂廳級干部一走廊,局級干部一操場。工人農民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實在是微乎其微,而民眾對人大代表的實質情況更是知之甚少,鮮有候選人與選民主動見面與宣傳自己。
所以目前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最大的問題是人大代表誰也不代表,選民也找不到代表,代表也沒有自己真正的選民。”[8]接踵而來的問題在于,人大代表根本不清楚其究竟要對誰負責。為了反映民眾的真實意愿,增強人大代表的使命感,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應當適當減少間接選舉的層次。
當前,全國各地發展不平衡,許多地方還不具備實行大規模直接選舉的條件,但在經濟文化水平發達,人口集中,交通便利,信息網絡技術先進的地區,可以適當地擴大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從而減少間接選舉制層次。而對于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的構成上,應當主動降低或限制黨員與干部的比例,提高普通代表的人數比例,使人大代表民眾化。并在一定范圍內擴大差額選舉的范圍,拓寬成為人大代表候選人的非官方渠道,以此來提高人大代表選舉的競爭性,從而增強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與交流,提高民眾對民主選舉的參與熱情,如此,才能充分了解與代表民意,實現民主政治。
依據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而根據選舉法有關規定,選民和原選舉單位對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有罷免權,但在其內部框架內,并沒有其他國家機關監督制約人民代表大會,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應制定具體的人大代表內部管理辦法,以保障選民的知情權,落實選民的監督權。
通過比較分析社會契約思想,得知主權者接受權利的讓渡意味著一定的職責。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予,為人民所享有的權力代理人。在代理行為中,被代理人有權了解代理人職務的行使,代理人必須依據被代理人的授權范圍內行使權力,代理人在代理過程中也需盡勤勉謹慎的義務。因此,政府權力的行使應當限制在人民授權的范圍內,統籌全局,深謀遠慮,著眼于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也應當為人民私權利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障與便利,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1]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2]曹大為,趙世瑜.近代社會的民主與實踐[M].湖南:岳麗書社,2011.
[3]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4]周葉中.憲法(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申林.利維坦中國家主權與個人自我保全之間的張力[J].武漢大學學報,2014(03).
[6]艾克文.利維坦與現代民主制度[J].武漢大學學報.2010(05).
[7]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絳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8]張慎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對策思考[J].人民論壇,2013(11).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bbes and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Zhu Hui-yan, Chen Wen-hua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Department of Law,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30, China)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s put forward by the modern western thinkers about national origin theory and building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Hobbes argues that to enter into a contract to build a strong autocratic monarchy country, the core of his thought is "monarch has sovereignty"; Rousseau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core of his thought is "citizens have sovereignty". Look at Hobbes,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combined with times background, reason, scope of authorization, and compare their contracts sovereignty, fully understan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feasibility,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modern political life.
social contract; monarch has sovereignty; citizens have sovereignty
D031
:A
:1000-9795(2014)011-000038-03
[責任編輯:劉 乾]
朱慧嫣(1994-),女,廣東東莞人,廣東培正學院法學系2012級本科生;陳文華(1969-),男,廣東湛江人,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法哲學。
本文系朱慧嫣主持的廣東培正學院2013年度學生科研究課題霍布斯、盧梭社會契約理論之比較分析(課題編號:40)的最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