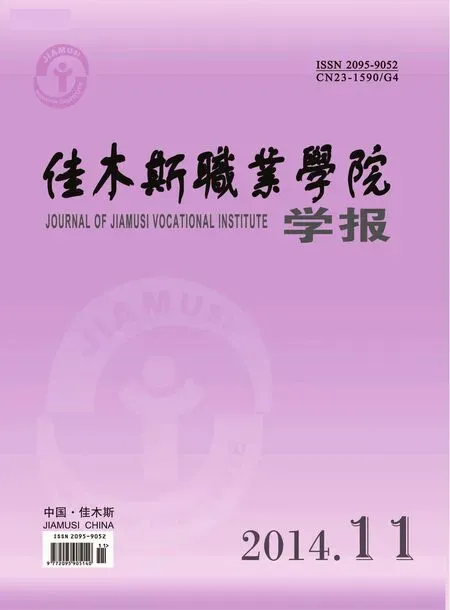外來詞翻譯中的文化認同
袁愛林 李玉英
(江西師范大學外語系 江西南昌 330022)
外來詞翻譯中的文化認同
袁愛林 李玉英
(江西師范大學外語系 江西南昌 330022)
外來詞是外來文化的使者,它是文化融合的產物,具有外來和本土語言文化雙重性。不同的翻譯方式翻譯了本土對外來文化的認同程度的不同,根據文化因子的量化數值分類,外來詞中意譯詞和仿譯詞為歸化翻譯,對外來文化認同低,音譯詞和零譯詞就為異化翻譯,對外來文化認同高。
外來詞;外來文化;翻譯;認同
一、外來詞概念
外來詞,在漢語中存在的歷史悠久。國內曾出現過不同的術語,有 “外來語” “借詞” “借語”,國內學者有感于術名的不統一,醞釀修改,于1958年正式確立了“外來詞”一名,現在該術語已得到廣泛認同。 因此,文中采用該術名。
外來詞的概念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問題,爭議的焦點也就是意譯詞是不是外來詞的問題。呂淑湘,高名凱,劉正埮認為意譯詞不能算為外來詞,外來詞只包括語音借入詞,因此意譯詞字形和語音都是本土的,算不上外來詞,只能算外來影響詞。
而葛本儀,羅常培,馬西尼,岑麟祥則從社會文化的廣義視角研究外來詞,認為能反映外來來源的詞就屬于外來詞,不管是語音借入還是語義借入,因為從詞的發(fā)明權來看,該詞是由外民族首先發(fā)明并凝聚了詞的概念,它反映了某一部分外來文化。
文中將采用外來詞的廣義概念,作者認為外來詞的翻譯研究不能只注重語言影響還應該考慮到社會文化等非語言因素。 這樣才能更全面地考察文化接觸對語言發(fā)展的影響 ,才能為外來詞翻譯提供更合理的啟示。
二、外來詞的分類
漢語中的外來詞從來源來看,可以分為英語外來詞、日語外來詞、俄語外來詞等;從運用領域來看,可以分為科技外來詞、文體外來詞、政經外來詞、及日常生活外來詞。文中則從外來詞引進時所采用的翻譯方式,分為五大類:意譯詞、仿譯詞、混合譯詞、音譯詞、零譯詞。
意譯詞就是原來是傳統詞匯中固有的詞,后來從外語詞中吸收新的概念產生新的意義。如“電腦”一詞,詞的構成發(fā)音都是漢語中固有的,只是語義借入了英語的“computer”。
仿譯詞就是根據外語詞語的語素或句法結構而創(chuàng)造的漢語詞語。與意譯詞不同的是,它不僅借入了外來語義,而且還借入了外來的構詞方式。如在“蜜月”(honeymoon)一詞中,“蜜” 對應“honey” , “月”對應 “moon”。
混合譯詞就是外來語言成分與本族語言成分相結合,又可以分為三類:a.半音半意譯,如“motorcycle”譯為“摩托車”;b.音譯加義標,如“DDT”譯為“滴滴涕”;c.音義兼譯,如“vitamin”譯為“維他命”
音譯詞就是詞義和語音都是從外語中借入,詞的構成是散性聚合,字與字之間一般沒有語義聯系,外來特征十分明顯。如“比基尼”(bikini), “迪斯科” (disco)。
“零翻譯”的概念首先由邱懋如提出 (2001),零譯詞就是指直接借入外語詞,詞形,語音,語義都是外來的,借入后只有在語音上有細微的變化。如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CT”(computerized tomography), “DVD”(digital video disk) 。在漢語中,也有許多學者稱之為字母詞。
三、外來詞與文化
(一)外來詞是外來文化的使者
每一種語言都深刻反映了某一社會的文化積淀,外來詞是向目標語文化傳播外來文化的使者。在漢語發(fā)展的歷史中,外來詞大舉進入漢語都是伴隨著中外文化的密切交往。
第一次高潮是出現在東漢時期,持續(xù)到唐宋年間。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大規(guī)模的佛經翻譯帶來了大量的梵語外來詞,據梁曉紅統計,這一時期,漢語吸收了1050個梵語外來詞。
第二次高潮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播西方宗教和科技,其中著名的有羅明堅(1580),利瑪竇(1583),傅泛際(1621)等.他們和中國學者一起,翻譯了大量的宗教和科技譯著,這些著作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帶來了大量的科學術語。
第三次高潮是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列強的入侵喚醒了中國的仁人志士,使他們意識到中國的落后,必須要西學強國,這主要是翻譯軍事和人文科學方面的書籍,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以林紓、蘇曼殊、為代表的文學翻譯也大大發(fā)展。
第四次高潮是改革開放以后,大量的外文書籍、報刊、雜志引進中國,新的外來詞也不斷涌現。王力先生在《現代詞匯史》中粗略估計:拿現在書報上的文章用語和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文章用語相比較,外來的詞語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時代的文章用語比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
作為外來文化的使者,外來詞攜帶著異質文化特征,因此目標語對外來詞的接納過程也就是固有文化對外來文化的認同過程。在該過程中,譯者和目標語文化的制約都不可忽略。
(二)外來詞是語言文化融合的產物
外來詞不僅是外來文化的使者,還是兩種語言文化融合的產物。兩種語言文化在外來詞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史有為先生(2000:129)認為這種融合可以體現在外來詞的兩個方面:一是內容,包括語義內容和語法內容;一是形式,包括語音形式、構成形式和書寫形式。對外來詞所蘊含的兩種語言文化的含量進行模糊量化,清楚地顯示了各類外來詞所含有的不同語言文化的不同程度。他將兩種語言文化各自的最高分值定為10,最低為0,將外來詞分為五個構成因素(詞義、詞音、構成、詞性、字形),并按照形式為主的觀點分別配以一定的分值。分值的分配比例為:詞義2分;詞音6分;構成1分;詞性;字形1分。各種不同類別的外來詞的外來文化和固有文化分值如下:
H319
:A
:1000-9795(2014)011-000123-02
袁愛林(1979-),女,江西都昌人,講師,湖北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李玉英(1964-),女,江西南昌人,教授,江西師范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本文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課題《外來詞翻譯中的文化認同機制》研究成果,課題編號:YY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