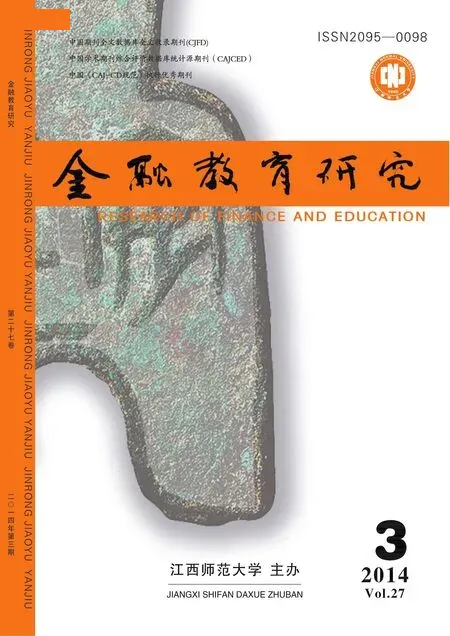經理人治理理論模型:述評與展望
袁春生, 吳麗麗
(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近年來完善公司治理以減少管理層代理成本的研究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一個分支是經理人治理機制的相關研究。經理人的治理作用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1-2]Fama and Jensen(1983),[3]Jensen and Meckling(1976)[4]等經典文獻認為,勞動力市場壓力和職業關注對公司管理層和董事會成員具有約束作用,較好公司業績可以提升CEO或董事會成員未來的職業前景。高管職業關注影響公司投資、盈余操縱、資本結構、戰略管理等諸多方面。[1]本文對經理人激勵、經理人能力的學習、管理才能市場匹配等方面的理論模型進行簡要介紹與評述。
二、經理人激勵模型
(一)報酬激勵模型
高管激勵可分為顯性報酬激勵與隱性聲譽激勵。顯性報酬激勵的基本思想是,企業產出依賴于高管努力程度,采用報酬激勵可刺激高管努力工作。Murphy(1986)[5]構建了二期動態激勵模型用以考察高管工作經歷與報酬之間的關系,模型得出以下結果:當且僅當第一期產出大于均值時,高管第二期報酬大于第一期報酬;高管第二期報酬大于當期期望產出,第一期報酬低于當期期望產出;第二期報酬是第一期產出的嚴格增函數。根據此結論,可以推測:實際產出總是等于期望產出的高管其職業生涯中每年報酬都將相等;意料之外的高產出將使高管以后各期得到高報酬,反之亦然;業績對報酬的影響以及報酬的方差隨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增加;高管初期工資總是低于其生產率,企業支付給高管較低初期報酬所得的額外收益實際上是為未來支付給高管高報酬而進行的融資。
實務中持續較低的高管報酬業績敏感度讓學術界非常困惑,[6]可能原因是即有激勵模型只考慮了道德風險而忽視了逆向選擇問題。為此Chen&Leng(2004)構建了包括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混合模型。[7]在其模型中,委托人目標是最大化預期利潤,同時引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讓高(低)能力的代理人選擇高(低)報酬業績敏感度的報酬合同。Chen&Leng(2004)的混合模型發現:(1)如果市場中經理人是同質的或高能力經理人所占比例足夠大,那么包括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混合模型得出的報酬業績敏感度與純道德風險模型得出的較高報酬業績敏感度是一致的。但是實際上經理人市場并非同質且高能力經理人所占比例相對較低,最優報酬業績敏感度將低于純道德風險模型所得到的結果;(2)報酬業績敏感度與經理人市場中高能力經理人的比例正相關。
(二)聲譽激勵模型
Fama(1980)認為經理人會關注其職業聲譽,來自勞動力市場的隱性激勵可緩和高管道德風險問題。[8]Holmstrom(1982)[9]首次對此原創思想進行了模型化,其得出的結論是:(1)經理人會努力工作以影響市場對其能力的推斷;(2)職業早期經理人努力工作的回報較高,職業后期努力工作以影響產出并不能得到較高回報,努力程度將趨于0;(3)對經理人產出的觀察越準確,聲譽機制越有效。Holmstrom(1982)表明,職業后期經理人努力工作的動機減弱,Zabojnik(2001)[10]認為,此低效率均衡并非是唯一均衡,且模型中經理人期望產出可以為負的假定與現實不符。為此Zabojnik(2001)構建了一個觸發戰略均衡的重復博弈模型:經理人既要努力防止被懲罰,又要努力影響勞動力市場關于其能力的信念。模型結論可歸納為三點:(1)給予風險厭惡型經理人以固定工資比報酬業績合同更有效;(2)低產出的經理人將須更加努力工作,否則將面臨更低的懲罰性報酬;(3)董事職位可充當經理人前期良好業績的報酬及博弈最后階段道德風險的解決辦法。
與Zabojnik(2001)不同的是,Tadelis(2002)從市場聲譽作為可交易資產角度拓展了聲譽模型。[11]Tadelis(2002)認為,聲譽的可交易性能為代理人提供持續激勵,并不會隨職業生涯逐漸減弱。年輕代理人關注當前工作努力程度對未來收入的影響,而年長代理人關注未來出售企業聲譽所能得到的收入,二者面臨著同樣的市場聲譽激勵;好的市場聲譽具有價值,并激勵代理人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保持良好聲譽。Gibbons and Murphy(1992)模型則同時考慮了顯性激勵與隱性激勵。[12]他們發現:在考慮職業關注后,最優報酬合同是隱性激勵與顯性激勵的結合;臨近退休時隱性激勵最弱,因而只有較強的顯性激勵才能對年長者產生激勵效果,對年輕人而言隱性激勵與顯性激勵的搭配恰恰與年長者相反。據此可以推斷:將要退休及沒有晉升機會的員工(如企業頂層的管理者,衰退企業員工)其報酬業績敏感度最強,因為此類員工提拔機會的隱性激勵很弱;CEO越臨近退休,報酬業績敏感度越大;CEO任期越長,報酬業績敏感度越大。
(三)簡要述評
Chen&Leng(2004)的混合激勵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報酬業績敏感度與經理人能力正相關、高管報酬業績業績度持續較低現象。Zabojnik(2001)模型有助于解釋勞動力市場中對經理人較少采用詳盡顯性激勵合同、CEO報酬業績敏感度較低、業績良好的管理者更容易成為董事成員等經濟現象。報酬激勵模型關注報酬特征及其與公司業績的關系,而聲譽模型則主要考察高管職業關注對公司業績、現金報酬等的影響。實踐中高管既關心報酬又關注未來職業前景,因此在理論模型構建時,綜合考察隱性激勵和顯性激勵可能會得出更加合理的經濟預測。另外,激勵強度、勞動力市場競爭壓力、管理者風險厭惡等因素都將影響報酬和聲譽激勵的效果及報酬激勵本身,[12]因此,未來一個研究方向是識別出影響報酬激勵的重要因素,并將此類重要因素納入到理論模型中。
三、學習模型
(一)委托人學習模型
由于管理者才能的信息不對稱,雇主需通過觀察企業業績逐漸了解管理者才能。在Murphy(1986)雇主學習模型中,高管生產率依賴于其管理能力,此能力只能通過一段時間的經營業績而感知,董事會的任務是將管理者與資本適當配置以最大化公司價值。Murphy(1986)發現:隨著工作時間的增加,管理者才能的信息不斷被更新,資本配置更有效率,平均能力的管理者其報酬以遞減的增長率增長,有關管理者能力增量信息的價值逐漸降低;工作經歷與報酬關系的斜率隨著能力的方差增加而增加,這反映出企業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不同管理者獲得相同的初始報酬,而后管理者報酬的橫截面方差將隨時間推移而增加;對于給定的管理者,隨著對其能力的估計趨于準確,其報酬方差趨于減少。與Murphy(1986)的雇主學習模型類似,Milbourn(2003)[13]從資本市場對CEO能力的學習角度,關注基于股價的報酬合同中CEO報酬業績敏感度問題。模型最終發現,基于股價的報酬業績敏感度與作為能力信號的CEO聲譽正相關。
(二)雙邊學習模型
與委托人學習模型不同,Harris and Holmstrom(1982)[14]認為管理者本人也需通過觀察產出才能得推斷自身能力。Harris and Holmstrom(1982)考慮管理者保險需求的學習模型主要結論是:管理者支付保險費以獲得最低保證收入,工資等于平均生產率減去支付的保險費;管理者對自身能力評估的精確度越高,支付的保險費越低,保證收入越高;管理者對其能力估計的準確度隨工作年限的增長而增加,最低保證收入也將增加;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導致合同期內管理者工作年限與收入之間呈非減函數關系;不同管理者之間收入的橫截面方差隨工作經歷及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得到較好工作要約的管理者其實際報酬總是低于邊際產出;年長管理者已經有許多提升其工資的市場機會,而且對自己能力評估更準確和離退休時間更短,他們只需支付較低保險費,因此年長管理者收入較高。Taylor(2010)[15]也認為,管理者能力具有與特定企業相聯系的資產專用性,因此雇主與管理者本人對其管理能力都存在學習過程。Taylor(2010)模型預計:CEO期望薪酬與公司滯后的股票異常回報正相關,因為超常高(低)利潤將導致較高(低)的股票異常回報,也將提升(降低)CEO能力的估計值,并使得下一年CEO薪酬增加(減少);在CEO任期內,公司股票回報的波動程度將逐漸降低。
(三)簡要述評
學習模型的前提假設是,關于高管能力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此假定與現實相符。在資產專用性較強的行業中,甚至高管本人對自身的管理才能也不可知。因此,在管理才能專用性較強的行業及企業中,雙邊學習模型應更有現實經濟解釋力。例如,Harris and Holmstrom(1982)雙邊學習模型能較好解釋如下經濟現象:經驗豐富的管理者其平均收入高于缺乏經驗的管理者,即使前者業績并不高于后者。同時,聲譽激勵的機理是勞動力市場利用高管的當前產出來更新高管能力的信念并且基于能力來確定高管報酬,因此聲譽激勵的效果受到勞動力市場對高管能力學習效率的影響,將市場及高管對高管能力的學習過程納入到激勵模型,也許可以得出更為理想的預測結果。
四、管理才能配置模型
(一)管理才能需求模型
此方面典型模型為Chan(1996)的錦標賽模型。Chan(1996)認為,內部提拔更可能是充當錦標賽式的激勵手段以誘使員工努力工作。[16]該模型發現:企業更愿意使用內部提拔,除非外部候選人能力顯著高于內部競爭者;職工平均能力較弱的企業更不愿意采用外部招聘,此類企業員工報酬通常高于其邊際產出及保留工資,職工更不愿意退休,企業會制訂強制退休政策以控制損失及低能力職工過多;職位層級越高的員工來自內部提拔的可能性越大。與Chan(1996)的錦標賽模型不同,Hermalin(2005)[17]從董事會角度討論公司對CEO的需求及其后果。近年來外聘CEO比例顯著提高,外聘CEO平均任期短于內部提拔CEO。外招聘與內部提拔的主要差異在于董事會對外部候選人能力知之甚少,董事會將努力獲取CEO能力的相關信息,因此Hermalin(2005)從董事會勤勉角度為上述現象尋找經濟解釋。勤勉董事會模型顯示:董事會越勤奮公司越傾向于從外部招聘CEO;董事會勤奮程度的增加使CEO任期縮短;外聘CEO任期低于內部提拔CEO;董事會勤奮工作將提高CEO努力程度,報酬也越高。
與Hermalin(2005)不同,Murphy and Zábojník(2007)[18]的權衡模型則從通用管理才能需求角度來解釋近三十多年來美國公司治理變遷的顯著特征:CEO報酬顯著增長、越來越多的公司從外部市場招聘CEO、越來越多的外聘CEO曾擔任其它公司CEO職位、外聘CEO來自于公司而不是非盈利性組織的可能性越來越高。Murphy and Zábojník(2007)猜測,可能的原因在于環境變化使得CEO通用管理才能對企業經營越來越重要。Murphy and Zábojník(2007)構建的模型發現:通用管理才能相對重要性的增加使企業外聘CEO的比例增加;外部勞動力市場對管理才能的競爭使CEO得到更高工資;企業更傾向于外聘有CEO經歷的管理者擔任CEO;管理者個人傾向于加大通用管理技能的投資;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例趨于增加。
(二)管理才能供給模型
無論是雇主學習模型還是職業關注模型,都假定經理人能力為既定,忽略了經理人能力存在“干中學”效果。實際上,公司高管擔任其它公司董事可以變成更有效率的管理者:有機會將公司戰略與其它公司對比,接觸到不同公司管理風格并擴展CEO視野;方便高管收集信息,使不同企業間管理知識更方便轉移;拓展有價值的社會網絡,學習到商業技巧。不過,外部董事職位占用公司高管的時間,也會對公司業績產生負效應。Conyon&Read(2006)[19]的“干中學”模型對公司高管擔任外部董事的成本與收益進行的分析發現:CEO選擇的外部董事職位數量大于公司愿意讓其擔任的最優外部董事數量;CEO努力程度越高或者能力越強,公司機會成本越大,公司希望CEO擔任較少的外部董事職位;CEO擔任外部董事的數量越大,公司對CEO能力的估值越高。根據Conyon&Read(2006)模型,可得出推論:年輕CEO擔任外部董事的數量低于年長CEO;與外部招聘的CEO相比,內部提拔的CEO將會被允許擔任更多外部董事職位;在不同類(同類)企業中擔任外部董事的CEO其所在企業的董事會規模較小(較大)。
(三)工作匹配模型
工作匹配模型認為,企業通過觀察員工在不同崗位的生產率,可將員工配置到效率更高崗位。工作匹配模型強調工作輪換過程中的學習機制會提升企業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導致高管人力資本配置效率高于底層員工,造成的結果是高管平均生產率更高并取得更高收入。Gabaix and Landier(2008)的管理才能市場競爭模型發展了工作匹配模型用于解釋CEO報酬增長現象。[20]在Gabaix and Landier(2008)的模型中,不同能力的CEO通過競爭方式配置給不同企業。模型發現,高能力CEO往往被規模較大的公司所聘用,CEO報酬依賴于所處公司規模及全部公司規模,較少的CEO能力差異也會導致不同CEO間報酬的較大差異。據此,Gabaix and Landier(2008)認為,公司規模可以解釋CEO報酬方式、以及不同公司之間、不同時間、不同國別之間CEO報酬存在的差異。
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能力和風險厭惡程度不同的管理者被不同企業所雇用。基于此,Edmans,Gabaix(2011)[21]將風險厭惡因素納入到能力匹配模型以考察CEO配置、報酬等特征。模型結論為:(1)在不考慮道德風險時,高能力CEO就職于大規模公司。但代理問題會導致管理才能錯配。(2)CEO承擔較大風險將要求更高風險溢酬,高風險公司不但會雇用能力較低的CEO,同時也將支付給CEO超過其能力的報酬。(3)CEO風險厭惡程度越高或者公司越喜好風險,公司給予CEO的激勵越強。模型還發現:外部工作機會提高CEO報酬,導致企業雇用較低能力的CEO;外部工作機會越多,CEO報酬越高,企業現任CEO平均能力越低。Baranchuk et al.(2011)則在假定經理人市場為管理才能有限供給的競爭性市場基礎上發展出明星模型。[22]模型預測,能力強的管理者付出更多努力并經營更多項目,從而得到更多報酬。模型認為公司規模與CEO報酬內生于管理者能力與努力,較好地解釋CEO報酬大幅增長、大公司CEO報酬業績敏感度較低等經濟現象。
(四)簡要述評
企業不同特征導致對高管的需求存在差異,經理人市場的變化也將影響高管需求方式,進而影響管理者報酬特征。Hermalin(2005)、Murphy and Zábojník(2007)分別通過董事會勤勉程度、通用與專業管理才能重要性的變化,而諸如Gabaix and Landier(2008)等則通過工作匹配模型解釋了美國公司高管相關的顯著變遷特征。這些管理才能配置模型表明高管報酬大幅增長、高管報酬業績敏感度持續變低、公司規模對高管薪酬的解釋程度越來越強可能是在經理人市場變化情況下的內生結果,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委托代理理論認為高管樂于構建公司帝國的觀點,從而為理解CEO報酬變化趨勢、以及CEO報酬與公司規模之間的關系等經濟現象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角。
五、總結與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許多文獻從激勵、學習機制、才能配置等方面構建理論模型對經理人治理相關經濟現象提供了不同經濟解釋。比如,關于經理人報酬業績敏感度較低且下降的趨勢,Zabojnik(2001)模型認為經理人風險厭惡而Chen&Leng(2004)認為管理者逆向選擇行為可以說明此現象。關于CEO報酬快速增長,Murphy and Zábojník(2007)認為是通用管理才能相對重要性增加及經理人市場競爭所致,Bebchuk,et al.,(2002)[23]將此解釋為權力過大 CEO的掘壕自肥行為,而 Gabaix and Landier(2008)和 Baranchuk et al.(2011)則認為是管理才能市場化配置的內生結果。
未來研究可沿以下幾方面繼續探索:一是梳理各理論模型之間的差異并進行經驗檢驗。不同理論具有不同推論。例如激勵理論認為,早期高管報酬與企業業績敏感度較低,而后期敏感度則較高,而學習理論的預測正好相反(Murphy,1986)。此方面一個研究領域是,找出現有主流理論之間的差異并以經驗研究去檢驗各理論對經理人市場相關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二是構建符合我國經理人特征的理論模型并進行經驗檢驗。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不同經濟發展區域、不同性質企業面對的經理人市場存在較大差異,此差異正好為發展和檢驗經理人治理理論對我國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提供了可能。三是關注經理人市場競爭對公司財務與會計政策的影響。經理人市場為有限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不同市場狀態下經理人行為存在差異。在理清經理人市場治理機理基礎上,可研究不同經理人市場狀態下職業關注、學習、高管權力等因素對公司資源配置效率、代理成本、融資和投資等的影響,并可將研究拓展到會計與審計領域。
[1]Fee C.and C.Hadlock.Raids,Rewards,and Reputations in the Market for Managerial Talent[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3,16(4):1315-1357.
[2]Gillan Stuart L.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An Overview[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12(3):381-402.
[3]Fama.E,Jensen M.C.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J].1983,26(2):301-325
[4]Jensen,M.C,W.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5]Murphy K.J.Incentives,Learning,and Compensation: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anagerial Labor Contracts[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86,17(1):59-76.
[6]Jensen,M.C,and K.J.Murphy.Performance Pay and Top Management Incentiv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2):225-264.
[7]Chen Hui,Leng Fei.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in a Heterogeneous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4,16(1):19-33.
[8]Fama,E.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2):288-307.
[9]Holmstrom,B.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s:a dynamic perspective.In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Honor of Lars Wahlbeck.Helsinki:Swedish School of Economics.1982.
[10]Zabojnik J.O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for Managers[J].Economic Theory,2001,18(3):701-710.
[11]Tadelis Steven.The Market for Reputations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110(4):854-882.
[12]Gibbons.R.,and Murphy K.J.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Career Concern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3):468-505.
[13]Milbourn,Todd T.CEO Reputation and Stock-based Compens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2):233-262.
[14]Harris,M.and Holmstrom,B.A Theory of Wage Dyna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2,49(3):315-333.
[15]Taylor,L.CEO Pay and CEO Power:Evidence from a Dynamic Learning Model,Working paper,The Wharton Schoo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2010
[16]Chan W.External Recruitment versus Internal Promotion[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6,14(4):555-570.
[17]Hermalin BE.Trend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5,60(5):2351-2384.
[18]Murphy.K.J.,and J.Zabojnik.Managerial Capital and the Market for CEOs,working paper,http://ssrn.com/abstract=984376.2007.
[19]Conyon Martin J.,Laura E.Read.A Model of the Supply of Executives for Outside Directorship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12(3):645-659.
[20]Gabaix,X.,and A.Landier.Why Has CEO Pay Increased So Mu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1):49-100.
[21]Edmans,A.,and X.Gabaix.The Effect of Risk on the CEO Market[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1,24(8):2822-2863.
[22]Baranchuk.N.,MacDonald.G.Jun Yang.The Economics of Super Managers[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1,24(10):3321-3368.
[23]Bebchuk,Lucian,Jesse Fried,and David Walker.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2,69:75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