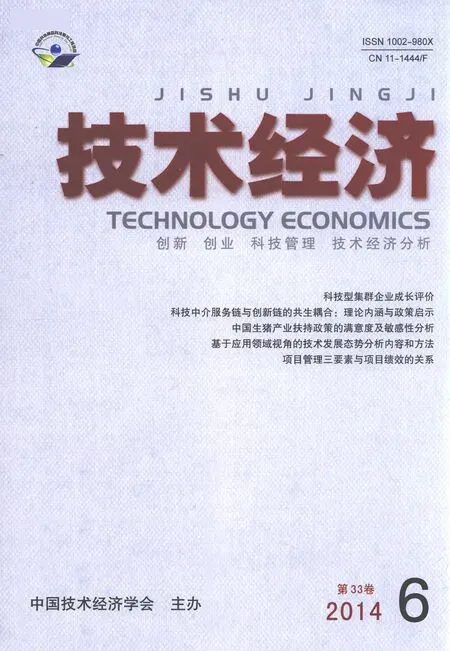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評價方法
孫 艦,任 旭,吳 娜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44)
瞬息萬變的經濟社會環境要求建筑企業具有快速適應變化的能力。早在1991年,美國國防部在日本制造業的市場份額已領先美國的情況下提出了“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和“敏捷制造企業”(ag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的概念[1]。其報告指出:為了奪回美國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必須進行行業戰略變革、提高企業的敏捷能力和靈活性,以滿足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隨后,“敏捷性”(agility)概念開始在美國制造業被廣泛研究和應用,從而實現了美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近年來,部分學者將敏捷性引入建筑業,對建筑企業的敏捷性展開研究[2]。
自美國軟件工程研究所(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ion,SEI)推出軟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以來,各國學者展開了對成熟度模型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外學者逐步將項目管理與成熟度評價模型相結合,構建了許多有價值的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這對于提高企業的項目管理水平和綜合競爭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本文在學習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建筑企業敏捷性與成熟度模型相結合,從企業角度構建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模型,研究其成熟度等級,探索影響建筑企業快速、敏捷發展的因素。
1 文獻綜述
1.1 企業敏捷性
美國戰略咨詢家Rick Dove是企業敏捷性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認為:敏捷性反映了企業應對變化的能力,敏捷能力是企業在變化的環境中獲取競爭優勢、適應未來無法預知的環境并持續贏得競爭的能力[4];敏捷的系統應達到RRS標準,即可重構(reconfigurable)、可重用(reusable)、可擴充(scalable)[1]。Goldman、Nagel和Preiss提出了“合作以競爭”(cooperate to compete)的理念,即合作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速度效應,并指出合作有內部合作和外部合作兩種方式,其中內部合作的主要形式有項目小組(teaming)和向員工授權(empowerment),外部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動態聯盟[5]。英國戰略咨詢家Paul T.Kidd提出了敏捷企業的4個核心因素——人員、組織、技術和關系,即:高技能、知識淵博并具有柔性、理性和響應變化的敏捷人員;非等級化、既支持個體又支持合作以及團隊工作的敏捷組織;先進的計算機基礎技術;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6]。
在企業敏捷性評價方面:Dove提出成本(cost)、時間(time)、魯棒性(robust)和范圍(scope)是企業敏捷性的4項綜合度量指標[7]。Amos和Gibson從組織管理的角度認為CIPME——通訊連通性(communication connectedness)、跨組織參與性(inter-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生產靈活性(production flexibility)、管理流通性(management involvement)和雇員使能性(employee empowerment)——是度量企業敏捷性的指標[8];武振業和馬軍崗[9]以及何漢武、陳新和孫健[10]參考Amos的CIPME評價體系建立了企業評價指標體系結構圖,并利用屬性層次模型(attribute hierarchical model,AHM)、層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法等評價工具和方法確定各因素的權值,然后利用多級模糊綜合評判法進行評判并以雷達圖表示單因素評判結果,在綜合評判后對處于同一敏捷檔次的企業進行排序,并根據企業轉換能力的評價結果來確定企業在敏捷空間中的位置。
1.2 成熟度模型
1987年9月,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軟件工程研究所(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SEI)提出了用于測度軟件工程成熟狀態的能力成熟度模型,為軟件企業的過程能力提供了一個階梯式的改進框架。該框架包括初始級、可重復級、已定義級、已管理級和優化級5個等級,這5個等級共包含18個關鍵過程域(key process area,KPA),每個關鍵過程域按5個關鍵實踐(key practice,KP)加以組織,通過相應的關鍵實踐來實現關鍵過程域的目標,以進行軟件過程評估、軟件過程改進及軟件能力評價[11]。隨后,各國學者對成熟度模型展開了研究,逐步將該模型拓展到項目管理領域。美國著名咨詢顧問和培訓師Harold Kerzner博士參考CMM和項目管理知識體系,將項目管理能力的提升與整個組織管理能力的提升相結合,提出了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Kerzner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K-PMMM)。該模型根據企業的戰略規劃分為5個層級,利用183套測試題評估企業在每一層級的成熟度[12]。組織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OPM3)是美國項目管理協會最新發布的標準。OPM3由一個三維模型組成:第一維是成熟度的4個梯級;第二維是項目管理的9個領域和5個基本過程;第三維是組織項目管理的3個版圖層次[13]。除此之外,Curtis提出了人力資源能力成熟度模型(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PCMM)[14],美國項目管理解決方案公司(Project Management Solution,Inc.)提出了五級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project management solution-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PMS-PMMM)[15],Harigopal和Satyadas提出了識別企業能力成熟度模型(enterpris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ECMM)[16]。中國學者潘吉仁、林知炎和賈廣社提出了建筑企業組織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17],劉波和孫劍平提出了員工勝任力成熟度模型[18],顧霄勇、孫劍平和梁瑞兵提出了組織領導力成熟度模型[19]。
2 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模型構建
基于對企業敏捷性的研究并結合建筑企業自身的特殊性,本文提出如下建筑企業敏捷能力的定義:建筑企業在持續變化和不可預知的環境中密切關注市場技術、客戶需求的變化,快速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根據不同項目及時調整組織管理方式并合理分配企業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高效率地完成項目建設目標,提升其核心能力,豐富客戶聯盟價值的熟練的適應能力。
本文以CMM、K-PMMM和OPM3為指導,對中國學者建立的建筑企業敏捷應變能力成熟度模型[20-21]進行分析,在吸收當前建筑企業敏捷性相關知識的基礎上,提出評價建筑企業敏捷能力的成熟度模型(agi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ACMM-CE),用于評價當前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衡量其所處的成熟度等級,為企業認清自身定位、明確發展的優勢和劣勢提供依據。
2.1 ACMM-CE的結構
2.1.1 研究范疇
本文從3個層面研究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即企業戰略層面、項目運作層面和價值層面。
1)企業戰略層面。建筑企業在戰略層面關注的是:在分析外界環境變化和企業自身條件的基礎上制定切實可行的、能促進和指導企業發展的長期戰略;將長期戰略分解為階段性戰略,針對每一階段戰略制定可操作的行動計劃,并在戰略實施過程中進行動態控制、及時準確糾偏,防止企業發展戰略與實際分離。
2)項目運作層面。建筑企業在項目運作層面關注的是:敏捷地感應客戶日益多變的需求,通過技術改進與創新來滿足建設項目對施工技術的要求,快速、合理、有效地分配企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使建設項目順利完成。
3)價值層面。建筑企業在價值層面關注的是: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通過不斷學習新技術和新知識來緊跟市場變化、提升自身價值,通過組建戰略聯盟來實現優勢互補、提高企業競爭力。
2.1.2 等級及特征
借鑒CMM對軟件成熟度等級[22]的劃分,本文將ACMM-CE成熟度劃分為由低到高的5個等級,每個級別都為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提升到更高等級奠定基礎。各成熟度等級及其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ACMM-CE成熟度等級及其特征
2.1.3 關鍵過程域和關鍵實踐
ACMM-CE成熟度的5個等級的范圍涵蓋建筑企業的戰略層面、項目運作層面和價值層面,除無序過程外,共有18個KPA,具體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ACMM-CE成熟度等級的關鍵過程域
首先,敏捷建筑企業的最典型特征是戰略管理能力突出——這是建筑企業參與敏捷競爭、組建或參與敏捷動態聯盟的必要條件。其次,建筑企業參與市場敏捷競爭,最終是通過項目運作來體現的,所以項目運作的敏捷性是重要的考察內容。最后,價值提升是建筑企業進行敏捷競爭的重要手段,對于建筑企業承攬項目和實施項目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分別從戰略管理、項目運作和價值提升這三個方面劃分不同等級的KPA。
KP是每個KPA特征的表現,每個KPA需要按照KP加以組織,通過相應的KP實現特定的目標。戰略管理層面的KPA共包含22個KP(見表3),分別描述不同發展階段的戰略管理水平;項目運作層面的KPA共包含32個KP①項目運作無序、建筑產品質量、工作質量、建設項目信息反饋及時性、建設項目信息反饋準確性、建設項目信息反饋有力性、質量保證措施、成本保證措施、進度保證措施、安全保證措施、環境保護措施、現場協調措施、人力資源管理、資金分配管理、物質資源管理、組織管理、合同管理、風險管理、技術管理、安全生產管理、客戶需求接受、客戶需求落實、客戶需求增值、生產工藝改進、科技成果轉化、產業結構調整、生產方式轉變、技術新構想、現有技術整合、技術應用、經濟社會效益、全過程管理。,分別描述不同發展階段的項目運作能力;價值提升層面的KPA共包含12個KP②價值提升無序、接受能力、應用能力、知識吸收能力、知識轉換能力、知識創造能力、資源結構組合能力、戰略隔絕能力、組織柔性、關系管理能力、組織學習能力、組織變革能力。,分別描述建筑企業的學習能力和維護良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能力。
2.2 ACMM-CE的評價指標體系
2.2.1 ACMM-CE的結構
本文以戰略管理層面為例,列舉不同KPA涉及的KP,每個相關活動表示實現其對應KP的重要環節,最佳實踐表示每個KP應達到的目標、體現了該環節完成的最佳狀態。若目標實現,則表示該KP達到相應的敏捷能力成熟度等級的要求;若全部KP實現,則表示該KPA已完成。戰略管理層面的具體結構如表3所示。
2.2.2 ACMM-CE的關鍵實踐提問單
在衡量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的過程中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通過向管理層和企業員工發放調查問卷來了解企業在保持自身敏捷性和培養敏捷能力方面的相關情況,對企業是否達到相應KPA內的KP要求進行評定。企業要想達到某個成熟度等級,就必須滿足該等級包含的KPA所規定的要求,即達到每個KPA的標準。
在某一KPA的得分大于等于該域總分的80%,表明企業已達到該KPA的標準。第一等級包含的KPA的得分總和大于等于80%,表明企業已逐步擺脫初始級,正處于由初始級向可重復級過渡的階段;該得分總和小于80%,表明企業處于初始級,各方面管理均處于無序狀態;該得分總和大于等于80%,表明企業處于該等級或向上一等級過渡的階段;該得分總和小于80%,表明企業處于下一等級或由下一等級向該等級過渡的階段。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舉調查問卷。

表3 ACMM-CE的結構描述
3 實證分析
雷達圖法是日本企業界評估綜合實力時廣泛采用的一種綜合評價企業財務狀況的方法[23]。鑒于雷達圖法具有等級化、指標化和直觀化的特點,本文利用該方法評定建筑企業——M公司的敏捷能力成熟度的等級。橫向靜態分析結果可以反映建筑企業在行業內的敏捷能力水平,使得企業可以尋求在行業內的有利地位,并形成戰略聯盟;縱向動態分析結果可以反映建筑企業敏捷能力的變化趨勢及企業工作重點的變化趨勢,使得企業可以及時調整發展方向和發展戰略。
3.1 M公司敏捷能力成熟度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1)建立指標體系。將ACMM-CE的KPA作為M公司敏捷能力雷達圖的指標體系,結合每個KPA對M公司進行問卷調查,進而匯總每個KPA中的KP提問單得分,然后用每個KPA的得分除以該域問題數,從而求得M公司在該域的平均得分,將之作為該域的指標值。具體指標值見表4。

表4 M公司敏捷能力指標測評值
2)指標值定義標準化。結合KP提問單分值的設置情況,設定KPA的定義分值范圍為0~5,最高分值為5/最低分值為0。
3)計算3個同心圓的分值。中間圓的分值為最高分值的80%,為4;最小圓的分值為最高分值的50%,為2.5;最大圓的分值為最高分值,為5。
4)繪制雷達圖。利用最小值、中間值、最大值和指標值即可繪制出M公司敏捷能力雷達圖。圓的中心(即各條軸的交點)的得分為0,表示完全達不到該KPA的要求;最大圓的外沿的得分為5,表示完全達到該KPA的要求。
5)標記指標值。將每個KPA的值標注在坐標軸上,然后連接坐標軸上的所有點,從而形成一個閉合的多邊形。可用不同線型標記每條邊以突出顯示。
6)解釋和使用評價結果。以圖形化的方式顯示得到的雷達圖。
運用雷達圖分析M公司的敏捷能力成熟度等級,結果見圖1。

圖1 M公司敏捷能力雷達圖
3.2 M公司敏捷能力成熟度和綜合敏捷能力分析
首先,由M公司的敏捷能力指標值可得:初始級的無序過程平均得分為4.8(5×80%)>4.0,滿足要求,然后進行可重復級的評價;可重復級的建設項目計劃、計劃反饋與調整、資源配置管理、項目實施措施、建設項目信息反饋、項目質量保證的平均得分為4.28>4.0,滿足其KPA的要求,然后進行已定義級的評價;已定義級包含的KAP的平均得分為3.72<4.0,不滿足其KPA的要求,即可停止評價。上述結果表明,目前M公司的敏捷能力成熟度正處于可重復級或由可重復級向已定義級的過渡階段。
然后,運用雷達圖綜合評價M公司的敏捷能力。通過計算雷達圖中與企業敏捷能力指標值相對應的多邊形面積并與最大圓面積進行對比,可判斷M公司的綜合敏捷能力和競爭能力。具體步驟如下:計算最大圓面積,即S1=πR2=3.14×25=78.5;計算多邊形面積,將多邊形面積轉化為19個三角形面積之和,其中三角形的兩邊長度為相鄰的兩個指標值,兩邊夾角θ=360°/19=18.9°,每個三角形的面積αi=[(lili+1)/2]sinθ,多邊形面積S2=算多邊形面積與最大圓面積的比值,即λ=S2/S1×100%=43.52%,這就是M公司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將評分結果劃分為5個等級,分別用優(A)、良(B)、中(C)、及格(D)和不及格(E)表示①A級,即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達到90%(含90%)以上,表明企業的綜合敏捷能力為優秀、綜合實力強;B級,即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在80%~90%(含80%),表明企業的綜合敏捷能力為良、綜合實力較強;C級,即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在70%~80%(含70%),表明企業的綜合敏捷能力為中、綜合實力一般;D級,即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在60%~70%(含60%),表明企業的綜合敏捷能力為及格、綜合實力較弱;E級,即建筑企業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在60%以下,表明企業綜合的敏捷能力為不及格、綜合實力差。。上述結果表明,M公司的敏捷能力綜合評分為43.52%<60%,因此M公司的綜合敏捷能力不及格、綜合實力差。
雷達圖直接表現了M公司在單個KPA上的優劣,依此可判斷M公司敏捷能力的優劣勢。由M公司的敏捷能力雷達圖可知,M公司在無序過程、計劃反饋與調整、項目質量保證、建設項目信息反饋、資源配置管理、技術改進管理和低級學習能力等KAP上具有優勢,企業在以后發展中應保持這些方面的優勢,并采取措施改進相對較差的KAP。
4 結語
本文基于敏捷制造理論,借鑒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CMM、K-PMMM和OPM3的優點,并結合中國建筑企業的特點,從戰略層面、項目運作層面和企業價值層面分析了影響企業敏捷能力的相關因素,創造性地構建了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模型(ACMM-CE),并用實例說明了建筑企業敏捷能力成熟度等級的評定過程。
[1] Rick Dove.敏捷企業(上,下)[J].張申生,譯.中國工程機械,1996(3/4):22-28.
[2] 章勝平.建筑企業敏捷性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3.
[3] 胡明.多級模糊綜合評估在組織項目管理成熟度中的應用[D].西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2007.
[4] DOVE R.The meaning of life &the meaning of agile[J].Production,1994,106(11):14-15.
[5] GOLDMAN S L,NAGEL R N,PREISS K.Agile Competitors and Virtual Organization[M].New York:Van Nostrs and Reinhold.1995:23-32,158-166.
[6] KIDD P T.Agile Manufacturing:Forging New Frontiers[M].Addison-Wesley Publishers,1994:9-12.
[7] DOVE R.An agile enterprise reference model with a case study of remmele engineering[C].Agility Forum,1996.
[8] AMOS J W,GIBSON D V.An exploratory model of agility:key facilitators and performance metrics[C].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Agility Forum Conference,Atlanta,1995.
[9] 武振業,馬軍崗.企業敏捷性評價模型[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1(8):428-436.
[10] 何漢武,陳新,孫健.基于層次分析和模糊綜合評判法的虛擬企業盟員敏捷性評價研究[J].機床與液壓,2004(8):17-21.
[11] NIAZI M,WILSON D,ZOWGHI D.A maturity mode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an empirical Study[J].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2005(74):155-172.
[12] KERZNER H R.Strategic Planning for Project Management Using A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M].John Wiley &Sons,2002.
[13] FAHRENKROG S,ABRAMS F,HAECK W P,et al.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s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OPM3)[C].Proceedings of PMI North American Congress,Baltimore,2003.
[14] CURTIS B.Making it personal[J].Software Development,1997,5(5):17-24.
[15] 王丹,孫穎,李忠富.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在我國建筑企業的應用[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21):811-814.
[16] HARIGOPAL U,SATYADAS A.Cognizant enterprise maturity model(CEMM)[J].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Part C:Applications and Reviews,2001,31(4):449-459.
[17] 潘吉仁,林知炎,賈廣社.建筑企業組織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研究[J].土木工程學報,2009(12):183-188.
[18] 劉波,孫劍平.員工勝任力成熟度模型及勝任力成熟度空間測度模型[J].技術經濟,2012,31(9):120-126.
[19] 顧霄勇,孫劍平,梁瑞兵.組織領導力成熟度模型及其空間測度模型[J].技術經濟,2013,32(11):119-126.
[20] 魯業紅,李啟明.建筑企業敏捷應變能力成熟度模型及實證研究[J].建筑經濟,2012(9):101-104.
[21] 武振業,馬軍崗.企業敏捷性評價模型[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1(8):428-436.
[22] 傅煒.軟件成熟度模型CMM/CMMI應用研究[D].貴州:貴州大學,2006.
[23] 殷秀清,綦振法,李霞.敏捷企業的敏捷性指標評價體系與方法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03(5):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