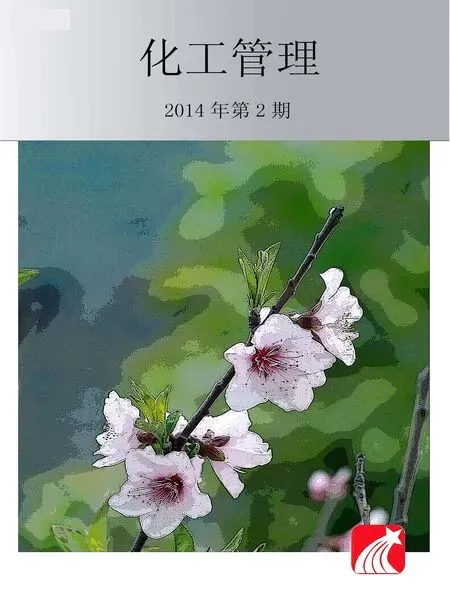碳稅對我國化學工業的影響
文/顧宗勤 韓紅梅
碳稅對我國化學工業的影響
文/顧宗勤韓紅梅

前言 化石能源的利用造成了二氧化碳大量排放。1965年~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計達1萬億噸以上,引發了人們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擔憂。為約束全球二氧化碳持續大幅增長,碳稅應運而生。
碳稅(二氧化碳排放稅的簡稱)是以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目的,對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按照其含碳量或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稅種。截止2012年底,國際上已有18個國家(或地區)開征了碳稅,對抑制該國二氧化碳排放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自2006年開始,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碳減排壓力巨大。2007年,我國政府明確提出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的改革目標。2013年6月,《環境保護稅法》(送審稿)開始征求意見,碳稅納入其中。2013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首批10個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發改辦氣候[2013]2526號),供開展碳排放權交易、建立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制度、完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等相關工作參考使用,預計也是為開征碳稅奠定基礎。
化學工業是消耗化石燃料的大戶,相應地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總量大。碳稅將對全行業帶來怎樣的影響,引起廣泛關注。
全球化石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情況
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中長期占主導地位
據有關資料報道,盡管世界各國在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但直至2011年,全球原油、天然氣、煤炭仍占一次能源消費量的87%,核電、水電、可再生能源僅占一次能源消費量的13%。預計2030年,全球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大概率仍將在70%以上,2050年仍將在50%以上。
不同化石能源對二氧化碳排放的貢獻各不相同
世界多個能源機構通過計算化石能源潛在碳排放系數,給出了不同化石能源“全部燃燒利用后排放出的碳數量”,以單位熱值含碳量表示。盡管計算數值略有差異,但總體上,等熱值燃料燃燒所排放的碳,氣體燃料最少、液體燃料次之、固體燃料最多,即碳排放系數天然氣<原油<煤炭。為減少碳排放,理論上應盡量使用天然氣,少用煤炭。
全球化石能源消費結構趨勢是“三足鼎立”
2011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天然氣、煤炭分別占 38.0%、27.2%、34.8%。預計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總量將增長36%,三者年均消費增速分別為0.8%、2.0%和1.2%。總量結構中石油消費增速逐漸遞減,天然氣消費增速快速上升,煤炭消費增速小幅下降,到2030年消費比例分別為33.6%、32.7%和33.7%,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隨化石能源消費而持續增長
據BP世界能源統計報道,從1965到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從每年117億噸增長到每年340億噸,46年翻了近3倍,年均增長率2.4%。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累計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并不突出。其中美國占24.8%,歐盟占19.7%,中國占12.9%,日本占5.0%。但近十余年來,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呈小幅下降趨勢,而發展中的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仍保持較高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
2011~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1.2%
《BP-2030年世界能源展望(2013)》預測,2030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費將達到136.2億噸(油當量)。結合化石能源消費結構可以計算出,屆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將達到427億噸,2011~2030年年均增長率為1.2%。
我國化石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情況
2000年以來我國化石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長加快
1965~2011年,我國煤炭、石油、天然氣消費年均增速分別為 6.3%、8.5%、10.9%, 2001~2011年分別為9.8% 、7.3%和16.9%。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3》,2011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4.8億噸標煤,相應地二氧化碳排放為82.8億噸。根據《BP能源統計2012》, 2011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7.4億噸標煤,二氧化碳排放量為89.8億噸。二者的差別主要在于煤炭消費量數據相差2.6億噸標煤,由此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相差7億噸。如果采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3》數據,2012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6.2億噸標煤,相應地二氧化碳排放為84.5億噸。
我國能源消費結構逐漸優化
2012年,我國煤炭、石油、天然氣、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分別為66.6%、18.8%、5.2%、9.4%。總體上,我國煤炭消費數量穩步增長,但占比長期近70%。雖然天然氣消費增長較快,但占比仍偏低。受資源條件和進口限制,石油消費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增速放緩。
預計2015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90億噸以上
展望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發展目標是:到2015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0億噸標準煤,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將提高到11.4%。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7.5%,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65%左右。由此可以計算,2015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90.8億噸,2013~2015年能源消費年均增速3.4%,二氧化碳排放預計年均增速2.3%。
工業是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大戶
從統計年鑒數據看,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消費能源占比達70%以上,交通運輸類占比約8%,生活消費類約10%以上。工業消費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生產供應業分別約占8%、81%和11%。制造業中的冶金及加工類占比近42%,石油和化學工業占比約23%。該統計口徑中的石油和化學工業包括了煉焦和核燃料業,與我們通常的化學工業統計口徑并不一致,需要做相應的調整。
我國化學工業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情況
化學工業“原料碳”特性與眾不同
化學工業與其它工業以“燃燒碳”形式消費化石能源情況不同,其他工業消費的化石能源基本都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而化學工業,作為“燃料”的化石能源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作為“原料”的化石能源,一部分轉化為二氧化碳,從系統中排放,而相當大的一部分轉化為化工產品,隨產品帶出系統。在計算化學工業二氧化碳排放時,應該將帶出系統的碳做相應的扣減。
我國化學工業碳總量消耗近7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約11億噸
為理清全行業真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種方法是從微觀角度出發,核算各個化工生產企業、各種化工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再匯總加合,形成全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這種方法需要大量基礎工作支持,由于基礎數據不全,往往得到的結果不能反映全行業的真實情況。
2013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首批10個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發改辦氣候[2013]2526號),利用該《指南》提供的方法,從全行業宏觀角度出發,理清行業流入邊界前端所有含碳原料和流出末端所有含碳產品,做“碳平衡”核算,然后計算碳損失,再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之下,采用這種方法更加反映行業情況。
按第二種方法,化學工業行業邊界前端流入的含碳物質主要包括:原油、燃料油、石腦油、液化石油氣、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等煉廠原料、乙烯原料、燃料類;煤炭、焦炭、蘭炭、焦爐煤氣、煤焦油等煤化工原料、燃料類;石蠟、溶劑油等精細化工原料類;此外還有含碳礦石、電力、熱力,以及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等輔助生產類含碳物質。
末端流出的產品類含碳物質主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燃料油、石油瀝青等油品類和“三烯三苯”類、碳一化工類,精細化工類以及眾多下游化工產品。這些產品相應進入交通、輕工、農業、紡織和民用等多種領域,此外還有數量不大的電力、熱力等輸出。
按上述方法核算,2011和2012年,我國化學工業流入邊界碳總量分別為6.6和6.9億噸。末端“流出碳”中,“產品帶出碳”約為3.7和3.9億噸,“損失碳”約為2.9和3億噸。“損失碳”折二氧化碳約為10.7和11.1億噸,這就是我國化學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
石油化工與煤化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強度截然不同
前端“流入碳”中,原油類、天然氣類、煤炭類占比分別約為72%、6%和19%,含碳礦石約占0.5%,電(折碳)約占2%。末端“流出碳”中,“產品帶出碳”約占56%,“損失碳”約占44%。“產品帶出碳”中,化工類產品含碳占比約92%,煤化工類產品含碳約占8%。“碳損失”中,石油化工類約占80%,煤化工類約占20%。二者相比,石油化工的總量大,含碳量占比高,但碳損失強度相對較小,而煤化工正好相反。
我國煤化工二氧化碳排放量2.2~2.7億噸
采用同樣方法核算煤化工行業的碳平衡。2011和2012年,煤化工前端“流入碳”分別約為0.88和1.05億噸,末端“流出碳”中,“產品帶出碳”約為0.27和0.32億噸,約占31%;“損失碳”約為0.6和0.73億噸,約占69%。“損失碳”折二氧化碳約為2.2和2.7億噸,即煤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數值約占化學工業的21%~24%,約占全國的2.7%~3.2%。可見,煤化工行業的碳排放強度相對較高,但總量占比并不十分“驚人”。
我國化學工業二氧化碳利用量約7000萬噸
一些化工產品的生產過程直接以二氧化碳為原料,傳統的產品主要有尿素、碳銨、純堿等,近幾年,碳酸二甲酯、降解塑料等新型化工產品也利用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根據產品單耗和行業統計產量計算,總體上, 我國化學工業內部使用的二氧化碳量約7000萬~7500萬噸。參考近年我國化學工業發展速度,估計我國化學品使用二氧化碳能力年均增長率約10%。
碳稅對我國化學工業的影響
世界碳稅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歐洲是走在碳稅改革最前端的地區。歐洲碳稅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環境稅-碳稅”改革。芬蘭于1990年首次實施碳稅。截止2012年,歐洲已有15個國家實施了碳稅。美國部分城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也開征了碳稅。目前亞洲還沒有國家實施碳稅,但日本和韓國已有近20年歷史的碳稅研究。
世界各國碳稅稅率沒有統一標準,絕對稅率相差較大,北歐國家碳稅稅率較高。根據能查到的資料看,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是瑞典108歐元/噸CO2;最低的是西班牙0.2歐元/噸CO2,一般在幾十歐元/噸CO2的數量級。各國通常在開征初期采用較低稅率,以后逐步增大。各國征稅對象范圍廣,稅基形式多樣,幾乎包含所有化石燃料。
在稅收優惠方面,各國一般都給予本國支柱產業、高能耗產業以減免優惠,以減少碳稅對本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還通過政策優惠加以導向,例如部分國家對參加自愿減排協議的企業給予減免稅優惠。
我國仍處于工業化發展初級階段,在考慮征收碳稅的時候,應注意選擇好開征時機,借鑒國外經驗,設置合理的稅率和稅收優惠。并應統籌考慮國內外經濟形勢和氣候談判的需要,同時兼顧化石燃料相關稅種的改革進展和結構性減稅的相關安排。
碳稅對化學工業的影響需高度重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送審稿)》 提出,我國碳稅稅率開征初期施行低稅率,按10元/噸作為稅率幅度下限,以后逐漸調整,100元/噸作為上限。
2012年,我國化學工業總產值105597億元,利潤總額3832億元。如果按我們計算的全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11.1億噸、并以不變價格計算,則碳稅10元/噸時,全行業碳稅總額達111億元,占化學工業總產值的0.11%,占化學工業利潤總額的2.9%,影響尚可接受;碳稅100元/噸時,全行業碳稅總額達1110億元,占化學工業總產值的1.1%,占化學工業利潤總額的29%,影響相當可觀。
對于剛剛興起的現代煤化工,碳稅的影響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對于煤制天然氣、煤制油、煤制烯烴、煤制甲醇、煤制合成氨項目,碳稅對煤化工項目的影響是很大的。按照國家示范項目規劃要求的能效值來計算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由此計算碳稅,再將碳稅與產品價格相比較。譬如:煤制天然氣出廠價格為2500元/千立方米,則碳稅占天然氣出廠價的0.2%~2%。按煤制油(柴油)價格7500元/噸、煤制烯烴(按乙烯計)價格8500元/噸、煤制甲醇價格2500元/噸、煤制合成氨價格3000元/噸計算,則碳稅占產品價格的比例區間大致為0.1%~1%。通過對煤化工項目內部收益率(IRR)指標影響的測算,大約為0.2~2個百分點之間。上述測算是分別對應碳稅10~100元/噸進行的。總體上,碳稅10元/噸時,煤化工項目尚可承受。如果碳稅達到100元/噸,則恐怕煤化工項目很難承受。
鑒于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狀況長期存在,石油需求不斷增長,油價長期高位運行原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應對大氣污染的重任十分艱巨,我國對煤化工,尤其是剛剛起步的現代煤化工行業,應慎征碳稅。建議參考國外碳稅經驗,給予煤化工行業一定的免征期、優惠期。當國內能源消費結構更趨合理、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價格理順后,再適時開征碳稅。
碳減排措施展望
目前國內外二氧化碳利用途徑主要有四條,即化工生產利用、二氧化碳捕集與封存(CCS)、二氧化碳驅油、二氧化碳生產藻類。
國外可借鑒的有三個成功的CO2封存項目的實例:
1.挪威大型石油天然氣公司國家石油公司Sleipner項目,是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的項目,將CO2封存于海上咸水層之下,CO2處理能力100萬噸/年;
2.美國Weyburn-Midale項目,將薩斯徹溫省一座廢棄油田的煤炭氣化廠產生的CO2進行填埋;
3.英國石油公司經營的阿爾及利亞薩拉油田項目(InSalah項目),把從當地天然氣生產中提取的CO2輸入地下,CO2處理能力100萬噸/年。
在CO2驅油方面,目前世界上也已成為一項比較成熟的技術,美國是該領域的領跑者。2000年,美國大平原廠建成了一條328公里(205英里)的CO2管道送加拿大油田,每年輸送140萬噸CO2。2010年,美國共實施了112個CO2驅油項目,其CO2驅年產油量達到1250萬噸。每年用于石油開采的CO2約占其CO2總消費量的11%左右。
加拿大從1990年起至今共實施了43個注CO2提高原油采收率項目,2010年,加拿大共實施7個CO2混相驅油項目,其日產油量達到45萬噸。丹麥、阿根廷、特立尼達、土耳其、巴西等國也相繼開展了CO2驅油及封存提高原油采出率的研究與應用。
對于我國來說,總體上,化工生產途徑可利用的二氧化碳量有限;CCS需要著力降低碳捕集和輸運成本,需要有適宜的地質封存條件;二氧化碳驅油也需要特定的油田地質條件;而二氧化碳生產藻類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森林碳匯應是目前最適宜的途徑,應鼓勵加快發展。對于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二氧化碳驅油、二氧化碳生產藻類等途徑,現階段應加緊進行示范工程建設,待技術取得工程上突破后,再大范圍推廣。大型煤化工項目建設通常集中在煤礦坑口附近,開展二氧化碳驅油和枯竭煤層儲存二氧化碳的研究具有地質條件和經濟優勢,可以參考國外成功的做法,加快相關工程技術研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