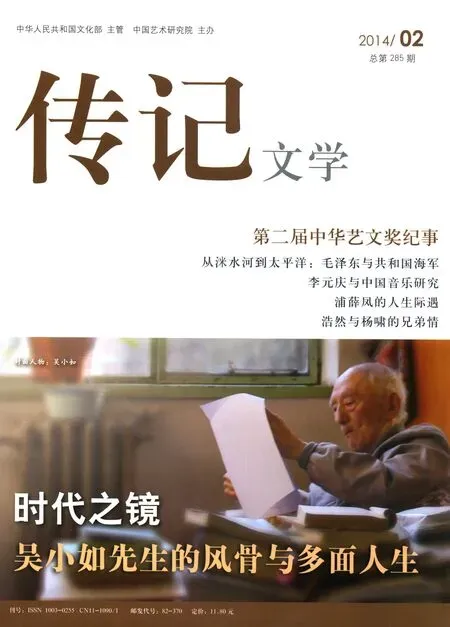用苦難鑄成文字
——馮積岐評傳(二)
鄭金俠
用苦難鑄成文字——馮積岐評傳(二)
鄭金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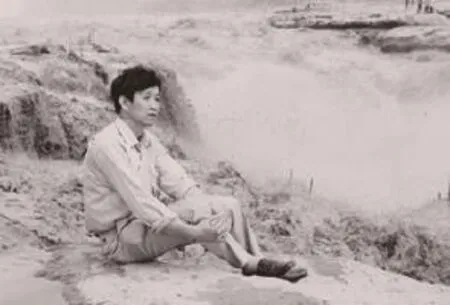
第二章 遭遇“社教”
1
1963年的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研究制定指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毛澤東在會上說,我們在農村中十年沒有搞階級斗爭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有些地方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有些地方是社會主義革命尚未成功,地主階級根本沒有打倒的個別地方是重新革命的問題。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決定》也叫“前十條”。決定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會議結束以后,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在全國相繼拉開了序幕。
這場運動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開始,以至發展到亂搞斗爭,亂打亂殺,使農民人心惶惶,個個緊張不安,一時間,共和國的天空陰云密布,階級斗爭的雷聲滾滾。
有人提出,西北民主革命不徹底,陜西成為重災區,長安縣是“社教”的試點。資料顯示,長安縣的一個農村只有25戶農民,有15戶被補定為地主、富農。
1964年的秋天,社教工作組駐進了岐山縣北郭公社陵頭村。
少年馮積岐根本不知道,一場災難像狼一樣就蹲在他們一家人的身后。
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個秋雨死死纏住的秋天,不懷好意的秋雨天天下,街道霉了,房屋霉了,樹木霉了,吸進肺腑里的是一股嗆人的霉氣。街道上泥濘難行,每天去學校的時候都要趟著爛泥臟水。家里沒有柴火燒,母親將面條下到鍋里燒不開,只得不得把炕席下的麥草抓出來燒了鍋。日子本來就像滾上了一身泥,不堪入目了。就連這樣艱難的日子也沒法過了。
秋雨住了沒幾天,一天清晨,馮積岐還沒有去學校,村里的貧下中農涌進了四合院。一家三代八口人和同住一個院子的叔父家的七口人全被貧下中農趕到了前院里。在沒有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貧下中農開始抄家了。他們翻箱倒柜,樓上樓下的去尋找,折騰了大半天,卻沒有找出一塊銀元或者一件值錢的東西,只有一些舊衣服和舊鞋襪,塞在柜子里,連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全家人不敢上前詢問,更不敢阻止,全都噤若寒蟬。馮積岐畢竟只有11歲,他和年幼的弟妹們根本不明白眼前展現的這一幕是怎么回事,驚恐不安地睜大了雙眼。父親和叔父一臉的憤怒,卻不敢出聲,唯獨祖母鎮靜自若,她老人家拄著拐棍,站在院子里,不卑不怒,并不畏懼這些滿臉階級斗爭的貧下中農,冷眼看著那些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出出進進。在馮積岐眼里,平日里村子里的那些叔叔、伯伯、爺爺們的笑臉這時候變得十分冷漠、冷酷甚至猙獰。他們在自己的家里橫沖直撞,舉動粗暴野蠻,毫無人情,少年的他很難理解那些大人們何以變得這樣可怕。馮積岐除了害怕還是害怕,比第一次見到狼還害怕,比跌到井里去還害怕。他不知道這些人要把他們一家怎么樣。看著這些臉色鐵青的莊稼人,他的眼淚撲簌簌地流下來了。

1979年初夏,在岐山縣陵頭村鄰居院內,馮積岐與其母(前右懷抱馮積岐兒子)、其妹(前左)等合影
馮積岐不知道,更大的災難還在后邊,抄家之后沒幾天,就是第二次“割韭菜”,就是所謂的“分浮財”。家里的桌椅板凳箱柜全部被搜羅一空,更慘的是,前院的三間半廳房(廳房:其建筑風格和樓房相仿,只是比樓房低四五尺、只有一層,一般建在剛進門的前院)和后院的三間半木面樓房被分走了,他們一家八口人只剩下三間廈房,叔父家也只留下了三間廈房,少年的他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了。1994年,馮積岐發表的短篇小說《沒有屋頂的房子》記錄的就是自己對“社教”的記憶。在他的記憶中,家里前院的三間半廳房被生產隊做了保管室,后院的三間半樓房被全部拆走,屋頂上的大梁、木椽、屋瓦被揭去以后,剩下的四面墻壁還沒有被推倒,土炕還在。深秋時節,馮積岐和他的堂弟就睡在沒有屋頂的房子里,這無異于睡在寥闊天地里,睜開眼就可以望見高遠而深邃的天空和滿天的繁星。秋風嗚咽,兄弟倆用被子蒙住頭。墻上的浮土被風刮下來撲在被子上,第二天早上,被子和炕上全是灰土與冷霜。有一天晚上,兄弟倆睡著了,半夜里下起了雨,他們醒來時才發覺,身上的被子早就濕透了,精身子像泡在水里一樣,只得趕緊從那個炕上爬起來,他們沒有叫醒大人。小小年紀,馮積岐就知道,父母親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即是父母親起來,他們還是沒有地方睡覺。兄弟倆就那樣抱著濕透了的被子,站在廈房的房檐臺上,看著雨夜,看著黑暗。秋雨不知疲倦地下著,靜夜里,叮當叮當的房檐水像惡毒的蚊子一樣在他們的身上叮。兄弟倆凍得瑟瑟發抖。漆黑的夜沉重地壓在兄弟倆身上,他們背靠著墻坐在房檐臺上,抱著濕被子,竟然睡著了。在沒有屋頂的房子里,兄弟倆從仲秋睡到了初冬。那些凄涼寒冷的夜晚木楔一般楔入了馮積岐的腦海之中,他牢牢地記住了在沒有屋頂的房子里棲息的日子。作為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年,最起碼也應該住進能遮風擋雨的房子里,可是,馮積岐卻不能。這是為什么?馮積岐還不能進行那么深入的思考。時隔30年,他之所以寫出了《沒有屋頂的房子》,不只是一種成長記憶,“沒有屋頂”顯然有其暗示和隱喻,暗示著少年馮積岐的人生從一開初就沒有最基本的庇護,隱喻了政治災難對人的摧殘。
在這次“割韭菜”的前幾天,村里的社教工作組就把父親和叔父喊去訓話。工作組的魏組長義正詞嚴地給馮積岐的父親和叔父說,給你們每家留下三間廈房,廳房和樓房要分掉。父親和叔父一聽,愣住了。這是他們沒有料到的事。兄弟倆先是抗爭,后是哀求。魏組長臉色一變,指住兄弟倆罵道:“狗東西!真是不識好歹。共產黨沒有把你們掃地出門就不錯了,你們是還想翻天?!啊?!滾出去!”父親和叔父哭喪著臉回到了家,把這件事告訴了祖母。
幾十年后,馮積岐寫過一篇叫作《銀元》的散文。在這篇散文里,他記錄了木面樓房未被貧下中農分走之前一件聞所未聞的事情。
一天晚上,馮積岐半夜里醒來,他一看,睡在他旁邊的祖母不見了,一陣說不清的細微的聲響傳進了他的耳膜。他爬起來,穿上衣服下了炕,走出木面樓房的套間,他一看,祖母端著一盞煤油燈站在房檐臺上,山墻上搭著一架木梯,父親站在木梯上用镢鋤在山墻上挖,叔父站在木梯旁邊朝上看。院子里的氣氛緊張而肅穆。祖母用左手遮著煤油燈的燈火,唯恐被風吹滅。馮積岐一聲不吭,只是站在遠處看。不一會兒,山墻上挖出了一個洞。父親很小心地從洞中端出來了一個瓦罐,叔父接過瓦罐,放在房檐臺上,然后,叔父把打成幾截子的土坯遞給了父親,父親將土坯塞進洞中。叔父將和好的泥巴給父親用鐵锨遞上去,父親給土坯上抹上了一層泥皮,泥皮抹得和原來一樣平整。然后,父親才下了木梯。父親和叔父的舉動和做賊沒有什么兩樣。幾十年后,馮積岐記住的不只是那緊張的一幕,他記住的是父親和叔父那緊張不安和微微抖動的雙手。
瓦罐是祖母端進樓房里的房間的。馮積岐跟在他們后面。瓦罐口用顏色發灰的枸紙包裹了好幾層,再用納鞋底的繩子扎住。祖母神情嚴肅地解開繩子,取掉枸紙,她將瓦罐雙手一舉,瓦罐口朝下,向炕席上一倒,一堆白花花的銀元堆在了炕席上,馮積岐第一次見識了銀元,他對銀元只是感到好奇。祖母將那一罐子銀元平分給了父親和叔父。
幾年以后,馮積岐用“銀元”做題目,又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在這篇小說里,馮積岐傳達了對銀元的憎惡。
祖母活著的時候,不止一次地在馮積岐跟前罵過祖父:你爺爺那個細死鬼,一輩子不吃不喝,攢錢買地蓋房,到頭來,啥也不頂,卻把你們害苦了,他那老東西現在后悔也來不及了。祖母告訴他的長孫:祖父在土改前夕把好多銀元埋在了地下,埋在了房子里的土墻中,他給誰也沒交代過。他一個人偷著埋,生怕誰看見。樓房山墻中的那罐銀元是祖父半夜里埋進去的,第二天用泥巴泥墻時被祖母撞見了,不然,這罐銀元父親和叔父是得不到的。
2
馮積岐的長篇小說《大樹底下》是寫“社教”的,短篇小說《目睹了或未了卻的事情》也是寫“社教”的。這些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有原型的,小說中的生活是馮積岐深刻體驗了的生活。《目睹了或未了卻的事情》中所寫的那個新補定的地主就是村子里被馮積岐尊為“叔叔”的一個不到30歲的農民。斗爭新定地主的場面馮積岐是目睹了的:工作組那個姓魏的組長個子不高,胖胖的,肥頭大耳,戴一副眼鏡。他的手指頭一戳一戳,幾乎戳進了這個新定地主的眼睛中,他破口大罵這個年輕的地主:狗東西!你不交代罪行,還想與貧下中農對抗到底?他罵著罵著,就用腳在這個新定地主的腿上猛踢了一下。這個新定地主疼得呲了一下牙,耷拉著腦袋,一聲不吭。在社教工作隊,有一個女孩兒,她的皮膚白皙光亮,圓臉,大眼睛,20歲左右,是很漂亮的。馮積岐曾經目睹過她和生產隊里的貧下中農青年在一塊打撲克的情景,也聽見過這個女人月光一般純潔的笑聲。可是,在斗爭會上,她變得氣勢洶洶,一臉惡相,她也像魏組長一樣揚臂動腿,對地主分子拳腳相加。好多年以后,馮積岐一旦回憶起那個女孩兒,眼前頭即刻浮現出她的一臉的兇相和可怕。階級斗爭把一個本該溫爾文雅的女孩兒改變成了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這確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1981年初夏,馮積岐與妻子董喜秀攝于岐山縣陵村麥地
在《大樹底下》這部小說里,社教工作組的組長和他的女組員在田地里野合,被地主出身的少年撞見了。工作組長對少年說,你什么也沒看見。少年說,他什么也沒看見。工作組長說,你是個瞎子。少年回家后,眼睛果然瞎了。工作組長命令你瞎,你的眼睛就必須瞎!可以說,這個情節寫出了馮積岐在1964年的社教中的全部體驗。這次社教是后來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演練和前奏曲。
社教工作組要給這個青年農民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這無異要將一個年輕人隨意毀掉。這個年輕人自我作踐了20多天后,喝毒藥自殺了。自殺前,這個年輕人到了馮積岐的家里,絕望中,他大概想和馮積岐的父親談談心。馮積岐記得,這位叔叔進了房子門,身子靠住他家的舊木柜蹴在腳地,臉色蠟黃,神情呆滯,眼神縹緲,好像全身的骨頭已經被敲碎了,如果不靠緊身后的木柜就會如一攤泥癱在地上。他眼簾下垂,一聲不吭。父親勸了他幾句,他還是不說一句話,臨走時,只是長長地長長地唉嘆了一聲。
沒幾天,這個新補定的地主自殺了。接著,村里開始鬧鬼。天還沒有黑盡,家家戶戶關上了院門,一個村莊寂然無聲,街道上空無一人,一股森然的鬼氣充斥于村街上。有人聽見, 這個年輕人在村子東邊的田地里半夜里嚎哭,哭聲非常真切;飼養室里的飼養員說,放在炕欄上的煤油燈在無人挪動的情況下滾落在地上卻不熄滅。村里人都認為,是年輕人的冤魂不散。那個年輕人的母親過幾天就趴在兒子的新墳上去慟哭一場,白發在秋風中飄動的悲悲切切的樣子深深地印在少年馮積岐的記憶里。
幸福的家庭有相似的幸福,災難的家庭有不同的災難。
1964年,不足1000人的陵頭村補定了十戶地主富農。每個地主富農家庭都陷入了深重不一的苦難之中。
苦難的日子陰云一般籠罩在馮積岐的家里。家里的大人,特別是父親和祖母的臉龐上再也不見一絲笑容,沉悶和死寂石頭一樣壓在每個人的心頭,這是比貧窮更可怕的苦難。馮積岐性格上的自卑和憂郁可以說從那時候起就萌芽了。就是在學校里,同學們不喊他地主,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種”,是屬于哪一類人的后代。同學們鄙視的眼神就是他的鏡子,他能從鏡子中看出自己的畏怯、懦弱和孤立無援的處境。
少年人心上的創傷久久難以彌合。
(待續)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