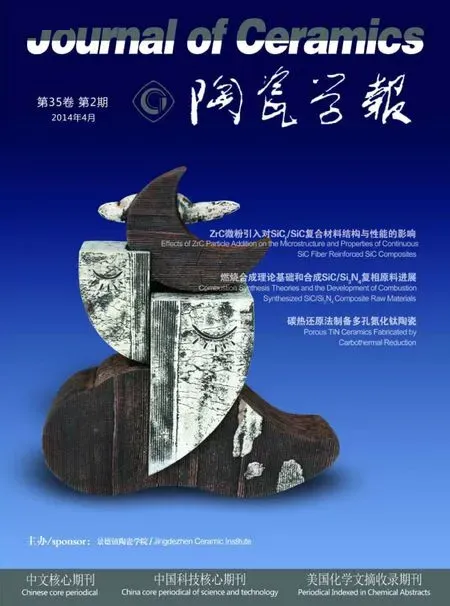謝赫“六法”生態淺析
吳也凡
(景德鎮陶瓷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000)
謝赫“六法”生態淺析
吳也凡
(景德鎮陶瓷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000)
歷代都對“六法”多有闡發,“六法” 之新解也隨時代不同而出現新的內涵。畫家創作時的激情、情操和美感等象“鏡像”關系一樣,傳移模寫到畫面中去。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往往不是“定態”,而是對應于一種高能量的“過渡態”。筆者通過創作實踐的感悟,將上古的結繩與人的手部的骨桿和骨結等與骨法用筆相關聯,提出了骨結與骨結密度的觀念,將骨架、骨氣(骨勢)、骨質、骨力、骨肉、骨韻和骨結視為骨法用筆的具體內容。以“六法”為綱,提出陶瓷美術理論體系涵蓋的內容主要為陶瓷繪畫美學、陶瓷繪畫材料學及工藝學、陶瓷繪畫形象學、筆法學、色彩學、構圖學、創作心理學、品鑒學等以及相關的交叉科學,強調所構建的陶瓷美術理論體系不僅是涵蓋相關陶瓷美術知識的科學理論體系,而且是關于陶瓷美術的智慧層面的科學理論體系。
謝赫;六法;陶瓷美術;陶瓷繪畫
謝赫生活在南北混戰及文化融合的南朝齊、梁時代,在謝赫之前就有名振千古的文藝理論家、書家、文學家、畫家,如劉勰、陸機、曹丕、曹植、顧愷之、宗炳、王微等人,他們的文論、詩論、畫論、書論、樂論等必然深刻影響著謝赫的繪畫觀念。在現存的典籍記載中,“六法”最早出現在謝赫的《古畫品錄》的《序》中:“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1,2]在謝赫的文體表達上,其中的“是也”顯然受到當時佛學中講經的影響。從“雖畫有‘六法’”可知,是謝赫將“六法”保存、流傳了下來。宋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對“六法”給與了高度評價:“‘六法’精論,萬古不移。”在中國畫論中,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當屬“六法”。歷代都對“六法”多有闡發,“六法” 之新解也隨時代不同而出現新的內涵,直至今日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即便是在對“六法”的文言文的斷句上,也引發了不少爭議。董欣賓和鄭奇合著的《中國繪畫六法生態論》[3]對古代諸多文獻進行了梳理,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對“六法”進行了廣泛的論述。徐悲鴻[3]、錢鐘書[4]、李澤厚[5]等紛紛登臺演釋,各抒己見。在現當代這種爭論仍在繼續,而且還將延續下去。
一、氣韻生動之生態新解
“氣”是一玄虛的抽象概念,是秦漢哲學中最重要的二個概念之一,幾近與“道”相提并論。秦漢哲學還揣測“氣”是構成人體生命的基本物質,并以氣的運動變化(氣機、氣化)來說明生命活動。人體之氣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指人體內流動著的具有營養作用的精微物質,例如水谷之氣、呼吸之氣等;二是指臟腑組織的功能活動。人體之氣還可細分為元氣、衛氣、營氣等,它們各司其職。
事實上,科學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玄虛之“氣”的物質性存在。近代科學家發現人受到宇宙氣場的制約,通過射電天文望遠鏡可測定宇宙在創生時期宇宙發生過程的信息。在有生命及無生命的物體周圍,都有一個由十分微小的粒子組成的微輕粒子場,并可用特殊的照相方法將人及固體物質周圍的微輕物資記錄下來。人體的生物能場可分為三層:近皮膚的0.635厘米為暗色層,0.635至5.08厘米為淡色層(紋理垂直于體表),5.08至15.24厘米為模糊層(輪廓不清)。1911年基爾納用“色隔板過濾色器”照相法和上世紀三十年代柯里爾用高頻電場照相法把環繞人體的輝光拍攝下來,人體輝光的明亮部分竟然與中醫的七百四十一個穴位相吻合,當人處在極度興奮時,其輝光呈紅色,與中醫理論的心經之氣呈紅色大致相同。人體被三層薄霧狀生物能場籠罩著,生物能場與身體的健康狀態有關,更受思想情緒的支配。現代科學研究也表明:氣是一種具有能量的信息及載體。人通過與外在環境進行物質與能量交換而達到協調平衡,通過修為(修行),可強化人體之氣,增進人對宇宙之氣的感知與交流等。“韻”可理解為創作過程中主體與客體所呈現出的優美節律,具有詩意和音樂之美。
在魏晉時期盛行人物品藻,“氣韻”被廣泛用于當時的相面術。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強調體悟的重要性,特別強調由里及外、由近及遠的認知過程。在創作過程中,畫家的氣機、氣化等運動狀態與作品休戚與共、息息相關。
古代很多畫論對“六法”的闡述往往有所偏向,可以在畫論中影響較大的汪珂玉、鄒一桂等人的論述為例。明代汪珂玉主要從作畫的過程強調氣韻生動,汪在《跋“六法”英華冊》中寫道:“謝赫論畫有‘六法’,而首貴氣韻生動。蓋骨法用筆,非氣韻不靈;應物象形,非氣韻不宣;隨類賦彩,非氣韻不妙;經營位置,非氣韻不真;傳移模寫,非氣韻不化。所謂氣韻者,乃天地間之英華也。”[6]清代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引用明代謝肈淛對“六法”的解釋:“愚謂即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為第一,用筆次之,賦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在畫成后得之。一舉筆即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為第一者,乃鑒賞家言,非作家言也。”[7]鄒、謝等人主要從鑒賞畫面效果的角度推崇氣韻生動。表面看來汪、鄒等人各執一理,其實氣分陰陽,他們只不過從不同的側面對氣韻生動進行了闡發。其中的“陰”更多地對應于能量結構狀態,“陽” 更多地對應于具象實態。
在量子力學中,微觀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描述微觀粒子運動狀態的薛定格方程以偏微分方程形式將其 “波”“粒”二象性進行整合,可對物態與物象運算求解,進行定量分析及圖像化,其符號表現形式最為簡潔、優美。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表明:所描述的狀態圖像越清晰,其能量狀態就越模糊,反之亦然。自然科學的晶核與藝術是相通的。筆者曾經在《瓷畫論》中對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進行了詩化的描述:空濛靈透、似象非象。其中有直觀感相的模寫,有生機的萌動,情景交融,沖然而澹,翛然而遠,澄觀一心而騰踔萬象;畫面里還蘊含著醒態和醉態:醒者映著天光云影,尖山碎石。醉者超塵脫俗,變化迷離。溫情和智慧交輝,時醒時醉。色塊、筆觸、節奏、旋律、虛實相間,蒼茫躊躇,生生不窮;畫面的宇宙時空不僅是詩化了的時空,還是節奏化了音樂化了的時空。在散點透視中,強勁的筆觸和激情的墨色構成節奏化的空間:星球的碰撞、驚濤拍岸、風卷碎石、石縫蟲鳴......,天地所有的聲響匯聚成鋪天蓋地而來的交響曲,其雄渾的動勢與壯觀是難以言狀的;畫面充滿著一陰一陽、一虛一實的生命節奏,虛靈的時空,流蕩的氣韻。虛空納萬象,萬象萌生機。畫家的行文題跋以及對作品的解讀,要有詩意,要有跳躍,可激發人們無窮的感受,讓作品與讀者相互間產生互動。例如李白的“……低頭思故鄉”的著名詩篇,如果用“望月思鄉”將其簡化之,就失去了詩味。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好比種子,人們無窮的感受與想象好比土壤,種子在土壤的生發過程,是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之生命的延續。
筆者認為: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往往不是“定態”,而是對應于一種“過渡態”,是與人的感覺中的具象與氛圍等相對應的一種顫顫動的運動狀態。顫顫動的運動狀態可與活動電影所造成的視知覺中的“擬動現象”相比擬。電影拷貝中的圖像原本是靜止的,當拷貝中的兩條先后出現的線條投射到屏幕上時,如果時間間隔大于1/5秒時,我們只能看到先后出現的兩條靜止的線條。但當它們先后出現的時間接近1/15秒時,我們就可明顯看到“擬動現象”(即原本靜止的線條在視覺中運動起來)。如果當它們先后出現的時間接近1/30秒時,我們卻只能看到兩條靜止的線條同時出現。根據人的視覺運動原理,筆者發現在繪畫藝術中也同樣存在著與活動電影相似的“擬動現象”,在整體的畫面中,當一定大小的色塊與色差的強弱變化或線條的曲直變化及力度變化定格在人的視覺運動的“擬動現象”范圍內時,畫面就會呈現出顫顫動的運動狀態(見圖1、圖2)。這種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狀態應該是“氣韻生動”的繪畫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據筆者的繪畫實踐,不同的顫顫動的畫面對視覺的沖擊效果,可調整觀者的情緒和食欲(例如增食或節食)等,并可用于醫學治療。在各畫種中,用火煉就的陶瓷藝術作品最適合表現這種顫顫動狀態。對于畫面整體在視覺前呈現出的“動像”的研究,將開辟陶瓷美術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

圖1 陶瓷美術作品神龍系列之一(84×84cm)Fig.1 One of Wu Yefan’s magic dragon series

圖2 陶瓷美術作品意象山水系列之一(84×84cm)Fig.2 One of Wu Yefan’s imaginary landscape series
二、骨法用筆之生態新解
魏晉時期盛行相面術,認為人的“骨法”、“骨相”可反映其性格、命運及精神狀態。魏晉時期,人物畫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六法”中的“骨法”一詞與“氣韻”一樣,雖源于魏晉時期盛行的相面術,但其本意除含有用筆墨刻畫骨相之意外,更強調的是繪畫的筆法。六朝繪畫以人物畫見長。據筆者考證:魏晉時期的一些著名人物畫不是用動物毛發制成的毛筆畫成的,而是用竹筆(將竹筆的尖端削成絲狀)畫成的,陰氣較重。書畫同源。關于骨法用筆,漢代《筆陣圖》說:“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8]關于骨法用筆,散見于古代的書論、文論及畫論中,廣涉骨架、骨氣(骨勢)、骨質、骨力和骨肉等內容。五代時期的荊浩通過對前人的經驗的總結,并結合自己的作畫體驗,提出以“筋、肉、骨、氣”為用筆四勢:“筆絕而(不)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7,8]運筆重中鋒筆法,通過運氣、運力,勁力徑直而下,筆分陰陽,如包裹在肉中的強勁的筋骨一樣,力透紙背,起伏成實,飛走流動,充分顯示了用筆的自律之美。
關于骨法用筆,除了骨架、骨氣(骨勢)、骨質、骨力和骨肉之外,筆者認為還應加上骨韻和骨節。筆者認為:骨韻系筆痕在運行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優美的能量狀態,是整個畫面氣韻生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生物界,植物的枝干和動物的肢體是抽象的筆痕所對應的實體。死體與活體的根本差別就在于能量狀態的不同,死體處在不斷的消解過程中,最后回歸于泥土。而活體則靠吸取來自泥土的養分與光合作用的能量,通過新陳代謝來維持活體這一自組織系統。活體會向周圍散發出微妙的氣息作用于人的視覺,使其表現出生機盎然的感覺,而死體則不會。活體的輪廓邊緣有極輕微的模糊感,即便是從感光照片或數碼照片也可隱約看出。筆者在幾十年的繪畫生涯中,特別注意在作品中表達這種感受,這樣有助于刻畫畫面中充滿能量的活體狀態(見圖3)。在用線造型的視覺藝術中,對應于活體的能量狀態的骨韻是極為重要的。

圖3 陶瓷美術作品佛像系列之一(84×84cm)Fig.3 One of Wu Yefan’s buddha series
以六法為綱,筆者認為《八大山人作品局部經典(動物二)》[9]書中第四面的“魚圖頁”(見圖4)的筆力較弱,魚翅和魚尾的墨暈有些收不住,眼部的筆墨力道較弱、不活,有些甜俗氣。其線缺乏內斂力,是小心翼翼、心虛地做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尤其是“山”字,象刷油漆似的,過于規整,雖有陰勁,但很不自然,書寫性不夠。八大畫眼的筆法絕不是平涂,而是用陰勁扣進去,挖出來,極富變化。運筆如壯士運劍,如果從畫的背面對光觀看,其豐富的筆墨變化將看得更加真切。更深一些的判斷應從整個畫面的氣場的角度去判斷,該畫氣場較弱,與八大的功力相去甚遠。
李澤厚從《易傳》中的“上古結繩而治”及大量史料推斷認為:作為符號系統的漢字“并不是口頭聲音(語言)的記錄或復寫,而是來源于和繼承了結繩和記事符號系統。承續著結繩大事大結、小事小結,有各種花樣不同的結來表現各種不同事件的傳統,以各種橫豎彎曲的刻畫以及各種圖畫符號(“象形”)等視覺形象而非記音形式(拼音)來記憶事實、規范生活、保存經驗、進行交流。”[10]這表明結繩和文字具有溝通天地鬼神的巫術等功能,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文字的發明者原本就是掌握神權的巫者這一類人物,時至今日還有道士使用漢字式的符篆做法事的舊習,顯示了漢字在人們心理上還具有神圣的律令性能。在遠古文化中,線中的“結”是具有巫術功能的一個抽象符號。以人的味覺和觸覺作為最基本的感知方式的中國傳統文化重體悟,中國書法和繪畫都是以手執筆,靠心與手的協調來進行抒寫,所以草芥中的草桿及桿與桿相連接的結,以及人的手部的骨桿和骨結的美感必然會在書法和繪畫中表現出來。對草本植物而言,草結的密度越高,就越顯現出茁壯老道的生機和美感特征。傳統的中國文化具有很多仿生學的特征,例如猴拳、鶴拳、五禽戲、柳葉描等等。在筆者長期的碑、帖摹寫等實踐中,骨結及骨結密度的美學概念如出水芙蓉,油然而生。例如王羲之的真、行、草書在行筆中全部具有明顯的骨結特征,而且骨結密度高。懷素中年時好酒,書法名噪朝野,經常騎著高頭大馬到王公貴族家寫字,時年四十一歲時的《自述貼》中,雖骨桿如鐵筋,但骨結少。素師晚年內心平靜如鏡,數十年的出家修行已將世俗名利及浮噪心態掃蕩無存,時年六十三歲時的《小草千字文》全無狂怪怒張之習,字字用意、平淡天成、蒼勁靜穆,字字具有明顯的骨結特征,而且具有很高的骨結密度。爐火純青的中國傳統繪畫及書法作品中的點線均具有類似的骨結特征。

圖4 魚圖頁Fig.4 Fish picture
綜上所述,可將骨架、骨氣(骨勢)、骨質、骨力、骨肉、骨韻和骨結視為骨法用筆的具體內容。
三、 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之淺析
以味覺和觸覺作為主要感知方式的中國文化與感知對象之間有著一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于是產生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藝術表現上具有強烈的來自內部的寫意傾向,在散見的中國文論和畫論里,以味、觸為原型的味字和品字是最頻繁出現的字眼。素為白色,玄為黑色(參太極圖),北極(天頂)為玄色(神圣的顏色),而其它色彩卻僅僅是起到眩耀眼目的作用,屬非本質的表象,于是水墨的顏色便與宇宙的本質緊密相連,水墨畫便成了載道的藝術。張彥遠(唐)在《歷代名畫記》中說:“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而以視覺和聽覺作為主要感知方式的西方傳統文化與感知對象之間是一種外在的斷裂關系,于是導致了西方藝術傾向于外部的寫實。
應物象形以物求象,以象求心,以形表情,以情達理。應物中的物,是由近求遠而來,其結果是意象應物,神形兼備,重神輕形。
隨類賦彩是指畫家氣韻生動、順其性情地對類相加以色相的描繪,將心態、類相、色相等融為一體,不分彼此。
經營位置雖含有主體構圖之意,但由于中國繪畫的抒寫性,使其更具有下筆隨情生境,隨機成趣之意,還有細心收拾、補綴等過程。
“傳移模寫”是一個完整的范疇,但為方便解,可暫時將其拆分為“傳移”與“模寫”。 傳移是指繪畫創作中的應物象形過程,通過傳移模寫的移行變貌對自然本相進行再造,使之包含了更多自然本相的類相。通過信息的傳遞和儲存,畫家將“萬趣融其神思” (宗炳《畫山水序》)[2]。“傳”與“移”含有傳統、傳形與傳神、移情、移動變化等諸多含意。“模寫”中的模字含有楷模、模仿、模式等含意。由于中國書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書法美學體系的早成,再加上中國古代畫工地位的低下及書家地位的顯赫以及中國繪畫所使用的工具和書法工具相同等原因,從觀念和實踐上導致傳統的中國繪畫始終未能脫離主要用毛筆和墨以“寫”的方式作為表現手法的特征。中國書法中的線條和墨韻及章法本身就是一種極抽象的寫意繪畫,是一種極特殊的繪畫表現。篆書最主要的造字原則是“依類象形”,近于寫實性的繪畫。最富形象的篆書最接近繪畫,隸書和真書的結構形式接近于建筑藝術,富有節奏和動律感的行書和草書具有音樂的旋律美。中國的文人畫起源于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作畫者均善書,主要為不得志而忘形于山水林泉之間的隱士這一特殊階層。文人畫的始創有兩大基礎:一是源自書法(主要是行草、狂草)的水墨抽象藝術;一是師法老莊之道和禪宗的以畫道戲墨。善書的文人畫作者群都強調作畫過程中的“寫”字,以“畫”為俗,以“寫”為雅。寫雖有契刻、刻畫之意,但更強調:寫者瀉也,情感之宣泄也。把注重筆墨看得高于模仿對象,應物象形只是表象,繪畫的目的不僅有形式表現上的裝飾性,且更是抒寫逸氣、解脫性靈,進而進入一個“道”的世界。由于水墨借助于毛筆在宣紙上的渲染所產生的特有的美感,非人力可控的水墨在宣紙上渲染的自由性,作為一個重要成分被注入到繪畫藝術,這種自由性和隨意性所達到的象征意味正好與莊禪暗合。老莊所追求的是認知生存的真正本意,是人的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由老莊再向上一關,就是禪機。莊禪尋求將變幻無窮的宇宙萬物加以擬人化、有情化。萬物都在虛空中,但禪境中的大智慧虛空卻幾近于不能畫。禪宗所關注的人生修為是一個從欲界到色界,進而到覺界的過程。禪偈(佛經中的唱詞)是謎,水墨畫也往往是謎。通過這樣的類比,禪宗藝術家把水墨繪畫當做是色界向覺界過渡、尋求精神解脫的一種形式。在審美意識和表現技法上革新中國寫意水墨畫的基本上都是禪宗大師。“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心源是禪宗的說法)是以我心為萬象立法的主體自我意識,表現了一種樂生隨緣的自然精神。這是中國繪畫傳統中最具主觀表現性和代表性的一大畫派,其所追求的是以主體意識把握和重塑繪畫對象的自由精神,是一種主體表達的境界。以畫載道,是繪畫作品的最高境界,還可把觀者帶到遠離塵世的精神世界里去,從而起到凈化人們的心靈的作用。“六法”中的“氣”和“寫”是其“晶核”,就像人體之氣血在其經絡與血管中運行一樣,是活體的最本質特征,從古至今的文人畫對之推崇備至。在中國古代歷來就有以畫為業者賤,以畫為娛者貴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但過于強調文人畫的雅興,似乎拉開了文人畫與職業畫的距離,抹殺了中國繪畫文化生態的多樣性。
四、六法與陶瓷美術
健康的活體生命具有氣韻生動的個體特征,優秀的美術作品象生命個體一樣,不僅具有原創性,而且由于其高品位和高質量而具有難以復制的特征。如果名人的陶瓷美術作品不難仿制或經仿制后,仿制品的藝術水準高于原作,那么該原作就不是藝術水準高的作品,該名人也就不是因藝成名者。春雨過后的地皮菇雖一夜之間就爬滿了背陽的山坡,但過不了幾天就會枯萎。八大山人的很多作品雖只寥寥幾筆,卻獨步古今,天下能亂其真者又有幾人?
現代流行的有些水墨青花作品,雖具有一些形式美感,但由于缺乏以骨立像,于是便顯得有些松散。在某些意向山水或顏色釉的陶瓷美術作品中,其肌理效果雖有一些形式美感,但看起來卻像一塊大花布。在追求新的表現形式與風格的創作過程中,如果能加深對“六法”的理解,將有助于創作出妙成天趣的陶瓷美術作品。在繪畫與書法學習中,最大的敵人就是不斷重復自己的錯誤,提升個人繪畫能力的最簡捷的方法就是下苦功夫向優秀的傳統學習。
在中國畫論中,六法可視為一個生態系統,一千五百多年來圍繞六法的討論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畫論。由于謝赫六法具有模糊性,缺少對繪畫體系內部各要素進行具體的分析與整合,已不能完全滿足當代對學科建設的需求。自古以來,中華傳統文化中就以精滿、氣足、神旺來描述一個人的健康狀態。但現代人在體檢時,絕不會同意讓一個方士坐在醫院門口,用這種模糊的方式來代替體檢指標。例如有些高血壓患者面部發紅、“神采奕奕”,但收縮壓和舒張壓都極高,其實已處在一種垂危狀態。要形成中國陶瓷美術理論體系,需要從陶瓷繪畫美學、陶瓷繪畫材料學及工藝學,從陶瓷繪畫的形象學、筆法學、色彩學(含古彩、粉彩、新彩、青花、釉里紅、斗彩等以及顏色釉繪畫表現方式)、構圖學、創作心理學、品鑒學等,以及相關的交叉科學來進行構建,形成一個智慧的知識科學理論體系。在中國陶瓷美術理論的構建過程中,可以六法為綱,綱舉目張。與以紙、絹為載體的中國畫不同的是,陶瓷美術是以具有玉質感的瓷器作為繪畫的載體。陶瓷美術不僅具有中國繪畫的技藝與美學等特征,而且還具有玉文化的全部內涵。陶瓷美術家除了具備傳統畫家具備的學養外,還必須掌握坯、釉、料及燒制的火候、氣氛等工藝過程,他們必須首先是掌握陶瓷技藝的體力勞動者,然后才可能成為陶瓷美術家。特殊的窯火氣氛,例如窯變,仿佛有神力相助,還可使陶瓷美術作品成為千窯一寶,個中妙趣,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但其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前功盡棄。與其它任何一個傳統的畫種相比,陶瓷美術在創作過程中擁有更多的變數,具有更豐富的表現力。陶瓷美術應該與中國畫和油畫等傳統畫種并列于人類藝術之林。在世界范圍內,陶瓷美術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陶瓷美術理論體系應是一個將陶瓷材料科學、工藝與美術理論相融合的智慧與知識的體系。例如陶瓷美術品的壽命評價的科學根據是什么?古陶瓷為什么會呈現出迷人的古色古香?如何將其引入現代作品中?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是什么?這些重要的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在學術領域幾乎是空白。陶瓷釉面屬玻璃體(暫且不論硅氧鍵的水解),玻璃體不穩定,有析晶傾向。在緩慢的析晶過程中,會將部分具有“火氣”的反射光變為“柔和”的散射光。當析晶到一定程度時,陶瓷釉面就不透明了,隨著陶瓷美術品的美感的退化、消失,輪廓雖在,但已成為混沌體了。筆者認為可將其作為美術陶瓷壽命評價的參考,進一步的工作還要針對不同材質并對其析晶活化能進行測定、建立析晶動力學方程等;景德鎮傳統的水槌工藝是顆粒級配的最佳方式,但卻缺少對其規律性的科學認識。陶瓷美術作品為什么有很強的地域特征?這很可能與原料中的某些微晶相有關?但這微晶相是什么?含量多大?這牽涉到能否突破陶瓷美術的地域性問題。如何從陶瓷顆粒的均勻、穩定分散的科學研究入手,消除陶瓷成型的應力等問題?這些在美術陶瓷工藝領域也是一個空白。筆者在研發色料的過程中,通過量子力學分析發現現有色料理論中用晶體場分裂來解析發色的機理是牽強附會的,錯誤的機理分析將把對色料的研究引向歧途。由于國內學術審查機構的人才知識結構不偏重于陶瓷美術工藝,即便有極為公正的評審流程,也很難對陶瓷美術工藝課題作出界定。筆者呼吁:在瓷都景德鎮建立一個沒有學院“圍墻”的陶瓷美術科學研究院,以對研究人員進行流動、淘汰的方式,深入、系統的開展陶瓷美術的工藝與理論研究。民間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陶瓷的許多工藝經驗性極強,現代科學技術還不能完全概括。今日景德鎮的陶瓷美術領域,藏龍臥虎,從業者之多、樣式之廣、水平之高,堪比春秋戰國時期之百家爭鳴,是英杰輩出的時期。
與中國傳統繪畫的頂峰期宋元遙相呼應,筆者認為:在元代,景德鎮的青花瓷例如“蕭何月下追韓信”、“鬼谷子下山圖”等繪畫水準,以“六法”衡量,絕不低于宋元時期的繪畫精品。再加上器型之飽滿、大氣,釉面之溫潤、典雅,用手觸摸時使人產生的那種妙不可言的親和感等等,這些美學特征與氣韻生動的歷史典故繪畫融為一體,不就是《易經》所稱頌的龍馬絕配嗎!元代這些陶瓷美術作品是人類美術史中的絕品,很值得認真學習與研究。
當今中國社會已進入信息與網絡時代,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交融的不斷深化,必然會導致陶瓷美術家和欣賞群體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觀念產生相應的變化。在具有千年陶瓷文化與藝術沉淀的瓷都景德鎮,來自海內外的藝術家與本土藝術家正在形成合流,以空前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及思想的深刻性將陶瓷美術推向歷史最高潮。一個以六法為綱的陶瓷美術理論體系正在構建過程中。
[1] 王宏建, 袁寶林. 美術概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2] 潘運告編著. 漢魏六朝書畫論[M]. 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 1997.
[3] 董欣賓, 鄭奇. 中國繪畫六法生態論[M]. 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 1990.
[4] 錢鐘書. 管錐編[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9.
[5] 李澤厚, 劉綱紀. 中國美學史[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6] 楊大年. 中國歷代畫論采英[M].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7] 俞劍華. 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0.
[8] 熊秉明.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M]. 北京: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2.
[9] 王一飛, 郭曉芳. 八大山人作品局部經典動物[M] (二). 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 2005.
[10] 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 北京: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Implications of Xie He’s “Six Principles in Painting”
WU Yefan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000, Jiangxi, China)
Xie He’s “Six Principles in Painting” were explicated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new explicat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time. Passions, sentiments and aesthetic emotions of an artist are mirrored in his paintings. Vivid paintings are usually not stationary but dynamic with flowing energ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connections of the brush stroke use with the ancient knot-tying practice for record keeping and the bone structure of a hand. It proposes on the basis of the personal art experience two concepts in painting: bone joints and their arrangement density. It regards the structure, energy, quality, strength, fesh, rhythm, and joining of bones a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 brush strok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eramic painting theory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e’s “Six Principles in Painting”is interdisciplinary, spanning aesthetics, ceramic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onography, painting, calligraphy, chromatology, painting composition, art psychology, art appreciation and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only knowledgedependent , but also wisdom-dependent.
Xie He; Six Principles in Painting; ceramic art; ceramic painting
TQ174.74
A
1000-2278(2014)02-0198-07
2013-10-02
2013-12-15
吳也凡(1953-),男,博士,教授。
Received date: 2013-10-02 Revised date: 2013-12-15
Correspondent author:WU Yefan (1953-), male, Ph. D., Professor.
E-mail:wyf46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