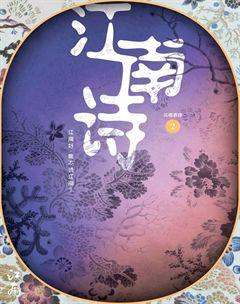生·欲·死
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是20世紀英美詩壇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其非凡的詩藝掀開了英美詩歌史上新的篇章。他的詩圍繞生、欲、死三大主題,詩風粗獷而熱烈,音韻充滿活力而不失嚴謹;其肆意設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擊、相互制約,表現自然的生長力和人性的律動。他前期的許多作品晦澀難懂,后期的作品更清晰明快,盡管某些細節仍然令人疑惑不解;然而,他作品的晦澀與不解并非由于結構的松散與模糊,而是因其內涵過于濃縮所致。他的詩篇感性而堅實,絕少流于概念或抽象;他的詩歌很少涉及精神壓力、懷疑、自我分裂、反諷等現代詩常見的主題。他的詩樸實純粹,自成一體,普通的一片落葉、一滴露水、一次性愛過程均可化為無窮的詩意;他從感性出發,通過具體可感的物象,觸及內在的本質,最終達到某種永恒的境界。他那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詩歌藝術令人贊嘆,令人翹首仰望。
狄蘭·托馬斯,1914年10月27日生于英國南威爾士斯旺西(Swansea),1925年9月入斯旺西文法中學學習,并開始詩歌創作。他那本著名的《筆記本詩抄》[1](1930-1934),記錄他早期的大量習作。研究者發現,他后來正式發表的大量作品在《筆記本詩抄》中多能找到雛形,有些就是略作修改或部分刪節修訂而成。研究者在1928-1929年斯旺西文法中學校刊上還發現詩人更早的一些作品。據說詩人最早的一首詩寫于1925年,即年僅11歲時。2003年美國新方向出版社修訂出版的《狄蘭·托馬斯詩歌》[2]收錄了包括詩人的《筆記本詩抄》及早期作品在內的共計192首詩歌,更多詩歌殘片現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館。1931年8月,詩人從中學畢業,出任當地《南威爾士每日郵報》記者。1933年,他在倫敦《新英格蘭周刊》首次發表詩作,1934年獲“詩人之角”圖書獎,同年12月出版第一部詩集《詩十八首》,1936年9月出版《詩二十五首》,1939年8月出版《愛的地圖》。1943年3月,他出任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1946年2月出版詩集《死亡與入口》,1950年2月20日-5月31日他開始首次赴美詩歌朗誦之旅。1952年1月20日-5月16日他攜夫人凱特琳開始第二次赴美詩歌朗誦之旅,1952年2月出版詩集《夢中的鄉村》,同年11月詩人親自從以往出版的詩集中選定意欲留世的90首詩作推出《詩歌合集》(1934-1952)。1953年10月19日詩人開始第四次赴美詩歌朗誦之旅,11月5日不幸發生,他因酒精中毒陷入昏迷。1953年11月9日詩人在美國紐約去世,享年39歲。
狄蘭·托馬斯的一生就是一個傳奇,他熱情好客,交際甚廣,詩人曾在“進入她躺下的頭顱”一詩中寫道:“一葉草融入草坪才能長存,/ 一粒石禁閉在云雀的山崗會迷失自己”。但是,他無所節制的生活卻暗藏不幸的種子。要是他少一點交際,多一點孤獨,少一點放縱,多一點節制,他也許活得更久些,寫出更多更美的詩篇。當然,那他就不再是詩人狄蘭·托馬斯。他的童年是在威爾士度過的,但他學習英語,不說也不懂威爾士語;他不喜歡威爾士民族主義,也反對各種民族主義;他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對威爾士中產階級嚴格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一種反叛。盡管威爾士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個家鄉的概念,但他詩句的樂感、元音輔音相互纏結的效果、奔放華麗的詞匯以及奇特智慧的修辭均無可置疑地體現威爾士游吟詩人的風格。他那色彩斑斕、聯想獨特、節奏分明的詩歌,配上詩人深沉渾厚、抑揚頓挫的音色極富魅力,令他赴美的四次詩歌朗誦巡演獲得空前的成功。
1951年,狄蘭·托馬斯在應威爾士某一大學生的訪談寫下的一篇“詩藝筆記”[3]里談道,“我寫詩最早的起因源自于對詞語的偏愛。我記得最早的一首詩是童謠,在能閱讀這些童謠之前,我喜歡的只是童謠的詞語。至于詞語代表什么、象征什么或意味著什么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聽到詞語的聲音,從遙遠的、不甚了解卻生活在我的世界里的大人嘴唇上發出的聲音。詞語,對我而言,仿佛就像鐘聲的音符、樂器的聲響、風聲、雨聲、海浪聲、送奶車發出的嘎嘎聲、鵝卵石上傳來的馬蹄聲、枝條敲打窗欞聲,或許就像天生的聾子奇跡般地找到了聽覺。我不關心詞語說些什么,也不關心詞語對杰克與吉爾意味著什么。我關心詞語命名或描述行動時在我的耳朵里構成的聲音形態;我關心詞語投射到我雙眼時的音色”。
詩人一生創造性地運用韻腳、節奏、構詞造字法,像一位詩歌手藝人在詩行間的詞語上煞費苦心,樂此不疲,盡管有時效果并不如意。他傾其所能利用各種手段——雙關語、混成詞、悖論、矛盾修辭法、引喻或譬喻的誤用、俚語、輔音韻腳、斷韻以及詞語的扭曲、回旋、捏造與創新——往往以超現實主義的方式翻新詞語花樣,力求他的詩歌創作朝著理想的王國前行。
20世紀30年代,英國詩壇及知識界陶醉于艾略特和奧登的理性世界。狄蘭·托馬斯一反英國現代詩那種苛刻的理性色彩而著力表現普通人潛在的人性感受,他的詩富有強烈的節奏和密集的意象,甚至于超常規的意象排列方式,沖擊著慣于分析思維的英國詩歌傳統。事實上,狄蘭·托馬斯超現實主義的詩風與20年代風靡歐洲的超現實主義運動一脈相承。他認為那些藝術家既不滿足于現實主義筆下描述的真實世界,也不滿意印象主義畫筆下想象的真實世界。超現實主義者想要跳入潛意識的大海中,不借助邏輯或理性來挖掘意識表面下的意象,而是將非邏輯或非理性化為筆下的色彩與文字。超現實主義者確信四分之三的意識為潛意識,藝術家的職責就在于從潛意識中收集創作的材料,而非僅局限于潛意識海洋露出的冰山一角。超現實主義詩人常用的一大手法就是并置那些不存在理性關聯的詞語或意象,希望從中獲得一種潛意識、夢境或詩歌,這往往比意識中的現實或想象的理性世界更為真實。然而,狄蘭·托馬斯盡管從主體上接受了超現實主義的詩歌理念,但并不完全同意,他曾經說:“我不在乎一首詩的意象從何處撈來:如果你喜歡,你可以從隱蔽的自我的大海最深處打撈它們;但是在抵達稿子之前,它們必須經過非凡才智的所有理性加工;另一方面,超現實主義者卻把從混沌中浮現出來的詞句原封不動地記錄到稿子上;它們并未塑造這些詞語或按一定的秩序加以整理,在他們看來,混沌即形式和秩序。這對我而言似乎太過自以為是,超現實主義者想象從潛意識自我中隨便撈出什么,就以顏料或文字記錄下來,本質上就存在一定的趣味或一定的價值。我否定這一點。詩人的一大技藝在于讓人理解潛意識中浮現的東西并加以清晰地表達;才智非凡的詩人的一大重要作用就在于從潛意識紛繁的無形意象中選擇那些將最符合想象目標的東西,繼而寫出最好的詩篇”[4]。
綜合分析狄蘭·托馬斯超現實主義的詩風的成因,一定繞不過弗洛伊德思想。當時這一思想席卷西方文學、藝術、文化各大領域,對作為詩人的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有關潛意識、性欲與夢的思想成為他詩歌的背景或題材。正如研究者發現,“狄蘭·托馬斯許多詩就是描述夢境,或根據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來構思,通過濃縮、轉移、象征等手法來創作”[5],就像基督教的神學啟示構成詩人創作的素材一樣。例如,他的詩歌會不時出現“諾亞”、“摩西”、“雅各”、“大衛”、“所羅門”、“約伯”等《圣經》人物,因為《新約》的故事打從小時候起就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詩人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基督教的神學啟示只是詩人深入思考宇宙萬物的開始;他既感知到無所不能的上帝和愛的力量所在,也看到了比之更可怕的死亡的力量。狄蘭·托馬斯對生命與死亡的思考構成他的詩歌最華美的樂章。詩人將生、欲、死看成一個循環的整體,生孕育著死,欲創造生命,死又重歸新生。
[3]:Dylan Thomas, “Notes on the Art of poetry”, Preface,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3,p15.
[4]:ibid, p.21.
[5]:William York Tindall, “Introduction”, A Readers Guide to Dylan Thoma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