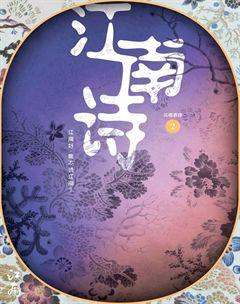民刊與環境
主持人語:
民刊與官刊的并存,是當下詩歌出版與傳播的一個現實,也是詩歌生態的一個縮影。民刊的平臺大多是以作者為核心,而官刊大多是以編輯為核心。與數十年前的嚴重分野有所不同,今天,民刊和官刊的界限已被逐漸打破,關鍵是誰在辦、怎么辦的問題。桑克的思考是一種突破邊界的思考,涉及到了“環境”的嚴峻一面,而思考的落腳點又回到了具體的寫作者,回到了“把詩歌的外部環境置換為詩歌內部的寫作問題”。(沈葦)
民刊的發行量大多數是比較少的,或者說它們之中的大多數并不追求發行量。
這不是說追求發行量的官方刊物的發行量就一定是大的。應該和實際之間總是有那么一丁點兒的距離,或者說總是有那么一丁點兒的臺灣海峽一樣的距離的。
我這里說的民刊,主要是指詩歌刊物,它們和官方刊物的區別本來是非常明顯的,但是現在這種區別卻有一種模糊的傾向,在我們的眼前呈現出來。我不知道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實際上我是知道為什么的,但是我又不愿意為這個浪費更多的口舌。
不管什么刊物,它們至少都是一個平臺,或者一間火車站的候車室,不同的只是進出的人是有限制的。有的候車室,表面上似乎什么人都可以進來,但有的候車室就僅限于同道或者幾個人,有點兒類似私人會所的意思。
這就關系到自由度的問題。民刊的自由度應該大一些,否則辦它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也看到自我限制的設立,有的甚至比官方刊物的限制還多,還強硬。這種情況大多數還不是基于真正的認識,而是由于對官方刊物的真正限制并不了解。這就有點兒可悲了。我面對這個問題,經常忍不住挖苦編輯:你不看《人民日報》啊,你不看新華社電稿啊。
民刊的平臺大多是以作者為核心的,而官方刊物大多是以編輯為核心。這個區別有些大了。寫什么本來是無所謂的,詩人在意的只是怎么寫,但是現在寫什么確實成為了一個問題。對于一個沒有什么野心的詩人來說,通常采取的一個聰明的或者狡猾的辦法是,寫什么還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寫,但是發表什么,還是盡量挑選一些所謂的“不惹麻煩”的東西吧,不管是把作品交給民刊,還是交給官方刊物。
這些都是實際的情況。我想任何人,即使是歷史本尊,也是會諒解這些所謂的妥協的。
那么民刊的存在究竟有什么獨特的意義呢?
同代人或者同類人相互刺激寫作。同仁刊物的作用大體就是這樣,因為這些刺激是新鮮的,與經典的外來的刺激是不同的。還有一個就是建立寫作機制的問題,這就是民刊的真正的建設性所在。與其他的大規模的或者綜合性的民刊,追求權威性或者包容性,還是有一些區別的。目前來看,同仁刊物的發展更激烈一些,而綜合民刊則面對著深入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從編輯的角度看詩,與從作者的角度看詩是不同的。而我們這些寫詩的人,現在更愿意選擇作者的角度。但是同時,我們也別忘了理解那些從編輯角度看待詩的內在心象的善意。
一個詩歌編輯怎么看待、葆有、促進作者的個性可能是一種真正的日常功課,尤其是尊重那些與自己的美學觀念,甚至是自己的寫作能力完全不同的作者的個性。這些說起來容易,但是施行起來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藝術如果尖端到了一定程度,就達成了非此即彼的唯一性,而很難再說包容這種所謂的正確性的堅持之辭了。
我們都知道文學團體與文學流派是不同的,而文學團體的年齡段,地域性,傾向性,目前都是比較明顯的被張揚出來的幾個元素。而文學團體大多數則依附于民刊的物質表現,當然也有依附于社會活動或者其他文學活動的。
比如《讀詩》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詩人的根據地,但它同時保持著前后銜接的視野,前面是五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出生的詩人,后面則是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詩人。地理方面,它是跨地域性的。而不少民刊則強調地域性,比如海南的民刊《海拔》。還有的則強調美學觀的同與不同,這些可能都是基于詩歌本體建設的動機。
以目前這樣的陣容傳播,且不說它的自然限制,主觀限制也是比較明顯的,所以強調這種社會傳播的必要性,可能也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而且我認為也沒必要把這個當作一種刊物的追求。小雜志(有一份嚴肅的民刊就叫這個名字)或者民刊,追求的只是一種小范圍的有效交流,它不是面對讀者的,而更像一個行業工會的內部刊物,僅限于工會會員之間進行交流。這個定位可能更為明晰一些,為的只是自我促進。而更廣泛的傳播,似乎應該交給報紙和網絡(電視極少涉及詩歌,暫且忽略不計)。官方刊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不具備傳播的廣泛性。而書籍的傳播主要依賴于詩人個人的影響力,當然也和出版機構的權威性與商業影響力有關。這些其實只是某些詩歌編輯關心的問題,大多數詩人和少數詩歌編輯可能沒必要關心這個。
換句俗話說,把鐵匠的活兒交給鐵匠,把木匠的活兒交給木匠。那么詩人從民刊中能夠獲得什么呢?一個發表的地方,一個閱讀同行作品的地方,這樣也就可以了。其實達到這個目的的民刊,就是傳說中的真正的絕招和真正的捷徑。
而環境對人肯定是有影響的。
對詩人們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現在詩人們的喜怒哀樂大多是和環境有關的,而構成環境的元素就多了,什么政治啦,社會啦,制度啦,我們每天不厭其煩地討論的環境問題,大多與這些元素密切相關。單純的環境問題當然是有的,但是孤立地談論它們好像也談不出什么來。而且個人的真正問題有時反而被環境問題遮蔽掉了。
當然把個人問題當作是環境問題的深遠影響也是可以的。
一個人或者一個詩人是渺小的或者說就應該是渺小的。它在社會或者環境之中可以選擇,或者說沒什么好選擇的,無非就是那么兩條路,適應環境或者改變環境。或者說這樣的兩條路可以同時存在于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甚至說它存在著而這個人并不知情。
所以無非是適應環境或者糾結于環境,改變環境或者改革環境。否則你又能怎么樣呢?個人力量之有限,在具體的寫詩行為之中的表現都是非常明顯的,何況更為明顯的是不能由個人把握的致命環境問題,且不說個人權利與個人權力的較量與掙扎的困境。
人人皆知而不能深談的問題其實就是環境問題。這就是問題嚴峻的一面。
而適應與改革之間的具體行為,至少包括日常社會行為,微博,報紙什么的。這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或者說目前體會比較深的三種方式。
報紙的反應是迅猛而敏感的,而“微博”或者“推特”,從某種程度上說已經是人心的或者環境的晴雨表,在上面你能清晰地看見環境是怎么在一秒鐘一秒鐘地跳動著變化的。
而對于詩人的外部環境,則可能包括詩人的小社會或者小江湖什么的研究,對這個問題我覺得現在完全沒有必要深談。還有就是關于寫什么的環境制約問題,雖然寫什么本來也不是什么值得一說的問題。
所以在一般情況下,我更愿意把詩歌外部的環境問題置換為詩歌內部的寫作問題來講述,即環境作為詩歌寫作對象的問題。這樣一來,不僅順利地繞過了寫什么的難題,而且直接把環境本身變成了寫作對象。平時我們總是聽一些詩人說,我們寫詩就是要寫我們的生活,那么現在就來寫寫我們細膩的環境吧,甭管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或者詩人創造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象征的或者符號化的環境。
那么怎么來寫“環境”呢?我更關心這種技術問題。這仍然就是怎么寫的問題。
首先是描述環境,不管是概括性的,還是對某一局部的細節進行深入的研究。達到真實的,精確的效果,這個也是說起來太容易了,但是做起來則需要十分嚴格的技術保障。就是說你不能把寫真實的態度當作寫真實的能力,更不能把你閱讀的鑒賞能力,當作真正的寫作能力。這種技術的東西在不少相關的書里有過一些記載,或者在一些關于修辭術的書里。但是更多的時候,它只是一種個人的秘而不傳的經驗,是包含在許許多多寫作者的作品之中和之外的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而它們之間共同的東西則太過于基礎性了,容易讓人覺得不值一提,但是更高的技術又容易被一些簡單的人將之與靈魂什么的對立起來。而它實際上根本不是一個對立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在更高的技術之中是包含著靈魂問題的。我希望讀者不要把這個當作物理事實來理解,而是當作一種思考的角度或者思考的方法來理解。
單純的技術也是有靈魂的力量的,何況那些復雜的技術呢。一首詩需要單純的技術還是復雜的技術完全要看這首詩表達效果的需要。所謂簡樸或者素樸是不該成為唯一的美學風格的,而只是一種實際的寫作需要。這在環境的表現中是非常明顯的,比如說卡夫卡對夢境的描述其實就是現實環境的藝術顯示。你用所謂的簡樸這一點是概括不了卡夫卡的。
在這種技術中,同時應該注意環境里所包含的新聞或者信息。我非常喜歡在詩里讀到相關的信息,這些都是帶有明顯的環境因素的,實際上也是在當代生活經驗之中包括了更多的歷史因素。這種能夠以文字顯示的東西確實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我們當然知道環境書寫的復雜性與綜合性,所以我們說環境的書寫確實不是那么單純的,如果把它當作一個講述的或者思考的線索,也是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問題串聯到這里來一起講的。這也就意味著事實的真相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關聯的,但是我們談論的時候,又可以暫時將它們當作獨立的對象看待。這只是易于表達而已,正如我們可以把環境故意地從主題的地位降低到素材的位置上來,或者故意地把環境的影響問題置換為怎么書寫環境的問題。而后者可能更利于我們寫詩,而不是把有限的精力花在怎么看待外部問題上。
我們今天似乎應該有這樣一種智慧:既能從一個人的角度看待問題,也能從一個詩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它們之間存在交叉,但是它們之間還是有那么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