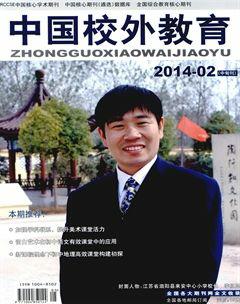從金融市場看語言發展的主流傾向
羅植琳
《金融煉金術》是金融投資類經典著作,該書闡述的原理可以與語言學原理緊密結合,二者有相似之處。通過闡述證偽主義和反身性兩大哲學原理,分析出金融市場研究語言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主流傾向。反身性原理金融市場語言發展喬治索羅斯是具有傳奇色彩的金融投資大師,1997年他旗下的投資基金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拋售泰銖,直接導致了東南亞經濟危機。《金融煉金術》是索羅斯的投資日記,他從歷時的角度分析個股,把握市場的偏向和轉機,并及時調整對策,這種精彩手段的背后則是他獨樹一幟的哲學理論——反身性原理。正是這本書,卻為筆者在語言哲學方面的思索打開了一扇門。
一、索羅斯的哲學理論
喬治索羅斯繼承了他導師、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其著名的論述是“科學陳述不能被證實而只可能被證偽”,這得到了愛因斯坦等眾多自然科學家的肯定。在語言中,陳述的真假同樣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當我們闡述一句話、一個命題的時候,證實必須同時滿足充分和必要條件,而一句話的充分性往往歸納并不完全,因此證實不具有科學的剛性特征。證偽主義哲學揭示了人類認知活動并不完備的本質,人們只能在不斷批判的過程中接近真理,而這一過程中的一切判斷都只是暫時有效的,并都屬于證偽的對象。
除了證偽主義哲學,索羅斯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反身性原理。所謂反身性(Reflexivity),表示參與者的思想和所參與的事態都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二者相互雙向多次作用,且不存在任何對稱。他認為,在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參與者的思想成為所要認識的事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事態的發展并不具有相對于思想的獨立性。反身性是一種不確定原理,即參與者的決策建立在對事物固有的不完備的認識之上。反身性也屬于辯證法的非決定論,究竟語言創造了人類社會還是人類社會創造了語言,他認為兩者相互決定互為因果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單向直線運動。
在索羅斯獨樹一幟的反身性理論背后,將他的理論追根溯源,有非決定論、非理性主義、解構主義和反本質的影子,但這是將他的理論極端化才出現的問題,不能輕視的是他對于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精辟的區分,對人類意識、認知局限的深刻認識。正是他這一闡述給了筆者啟發。
二、索羅斯哲學對于語言學的啟發
認知語言和語言本身并不等價,人類認知所涉及的不是事實,而是人類的認知情境,因此不能看成事實。人類用語言研究語言現象,用思維研究思維產物,這種研究方法注定會受到認知干擾。在語用學中,語言和人類的反身性關系最為密切。比如“飯我吃了。”這話最初可能只是偶然的語序交換,但是語用學家分析為強調的是飯,即“飯被我吃了”。于是再出現“錢我交了”這一句子,便約定俗成為強調的是錢,“錢被我交了”。這種分析在中文這個局部范疇是有效的,放眼其他語言就并非有效。這就是典型的研究行為干擾了研究對象的例子。基于認知的研究只是短時期、局部有效,盡可能避開意識的局限而走向理性十分重要。
語言的生成和發展并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卻受集體意識的合力影響,集體意識并不是無意識。意識的合力即意識形態是一種認知,認知是不完備且不一定合理的。集體意識的趨勢影響著語言發展的進程,變化的語言又反過來影響著集體意識的趨向。語言的發展趨向不是與人類的意識趨向相符合,而是未來語言的發展進程由目前的集體意識所塑造。在這種反身性中,語言的研究不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追求絕對化和理想化,否則會嚴重失真。我們唯一能做的是不斷在張力中,在動態、真實的語言世界中無限接近真理,追尋均衡。
如果把我們認識語言的行為稱為“認識函數”,把人類集體意識對語言的影響稱為“參與函數”,認識函數中對語言的認知基于語言,參與函數中語言受集體認知的影響。兩個函數從相反的方向發揮其功能。認識函數的自變量是語言,而參與函數的自變量是參與者的思維。兩個函數同時發揮作用并相互干擾。在數學中可體現為一對遞歸函數:
y=f(x)認識函數
x=Φ(y)參與函數
相互代入即:
y=f[Φ(y)]
x=Φ[f(x)]
兩個遞歸函數不會均衡,只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變化的過程不是一組事件直接、單一導向下一組事件,而是像復利的計算,利上加利不斷向前發展。
由此聯想到,喬姆斯基在句法中建構一個管約理論,也許就是句法“不管不行”的因果關系。目前這個想法暫時歸為三點:從認識到行動(管制)是人類的自然傾向;憑借不完備的理解和認識從事句法管理活動,大量的語料終究會產生意料之外的例子;出現例外后更加需要管約理論彌補上一次的缺陷。
三、金融市場和語言發展的相似
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跟語言發展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屬于社會現象,都受到人類意識較大的影響。語言變化源于集體大眾的意識,而集體的意識又反過來受制于語言的發展變化,即“我們說語言,同時語言也在說我們”。這種反身性體現在金融市場中則是買賣決策依據對將來價格的預期,而將來的價格又反過來受制于當前的買賣決策。
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是研究反身性現象的最佳切入點:一個中央市場,同質的產品,便捷的通訊平臺,足夠數量的參與者以保證沒有人能夠在日常的交易過程中左右市場價格。語言也具備同樣特征:從屬同一普遍語法框架,同質而形態不同的各種語言,快速而方便的社會交流平臺,足夠數量的說話人以保證沒有人能夠以個人的意識左右語言發展的趨向。任何人不享有話語的壟斷權。
語言的發展進程是開放的。語言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集體意識的傾向,這個傾向不是變化的唯一方向,因為語言自身還有普遍語法在主導,但社會意識確實是外在驅動的獨有力量。
語言是先驗的,在語言研究中我們先生成一個假設,然后用演繹的方法推論,最后得出結論并建立一個普遍的概括。同樣在投資活動中,做出投資決策就像系統做出一個科學假設并將它付諸實踐,最后讓它在市場中檢驗假設。只是兩者的目標不一樣,一個為了無限逼近真理,一個為了盈利。
在語言系統中,形而上的層面(大言)系統自足,形而下的層面(小言)語言不完美,系統不自足。同樣,金融市場在抽象的層面上是自足的,例如,宏觀經濟學“從較長一段時期看,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個就是理想狀態下的自足。可是,在實際層面誰也不知道“較長一段時間”是多長時間,以及每個波段周期是多久,每天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價就沒有一天消停過,震蕩的厲害。價格變動都有周期和主旋律,語言的發展變化也有主旋律,語言的變化體現在小言上,小言受集體意識(即流行趨勢、社會風俗)影響而圍繞大言(普遍句法)周期性波動,形散而神不散。
語言的研究和投資的決策都是對情境不完備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者的思維應包含于這些狀態之中還是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這些狀態就無法適用科學觀察,因為觀察到的只是參與者的思維效應而不是過程本身;如果排除認知只承認它的事實作為證據,就會破壞科學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為過程是不斷遞歸的,語言是動態的,共時研究語言的同時,語言正隨著集體意識而歷時的變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