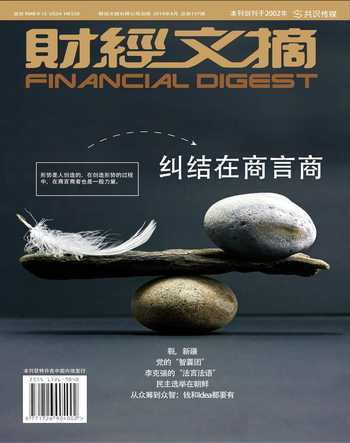張口閉口之間
楊帥


“我國自昔賤商,商人除株守故業、計較錙銖外,無他思想。”1910年,梁啟超先生在《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一文中寫下這樣的話。
古有“士、農、工、商”的階層四分,商為最末,而政治生活長期為士人階層所把持。于是,在商言商,不問政事,便成為大多數中國商人的行為準則。從商人抗禮諸侯的戰國時代以降,到清末救亡圖存之前,兩千余年,不曾更改。
革命中的保守派
西方的槍炮轟開國門,西方的思想也為中國人看世界與思考問題的角度開辟新境,兩相交擊,“在商言商”的傳統信條逐漸被突破。
庚子國變之后,清廷推行“新政”,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鼓勵組織商會團體。各地渙散不整、互相隔閡的商人們逐漸聚攏,其獨立意識與權利意識日益提升。正逢國家風云變色之際,商人議政之舉亦日多。收回路權運動、收回礦權運動,商人階層既需要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也常常會從國家大局出發考慮問題。他們一方面認識到專制統治的局限性,推動地方自治,請愿速開國會;一方面又偏向保守,力避社會動亂,因此在初期對辛亥革命抱持否定態度。
當然,全國商會并非鐵板一塊,他們的各自主張與政治動向不盡相同。但整體上,商人與地方政府和諧多于不合作,與中央政府則是頻頻請愿卻不得回應。面對“離不開,靠不住”的晚清政府,他們最終放棄了依附。連張謇這種與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有密切聯系、直到革命槍響之后仍力主鎮壓的商人,最后也轉而支持共和。
爾后大概是商人參政議政最為積極的一個時期,甚至在1923年7月,上海總商會成立民治委員會,自行草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嘗試建立“商人政府”。當是時,初入中共領導核心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上海《向導》周刊上發表《北京政變與商人》文章,稱贊民治委員會是“商人干預政治的第一聲”。“我們從這次上海商人對于政變的舉動看來,知道他們業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丟掉和平主義,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進步得非常之快。”
商人政府終成虛話,民族資產階級后來也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希望所在,商人階層的聲音又一次慢慢微弱下去。回顧這段歷史,商人初期認為革命“妨害商務,殊屬不智”,因此大都投身立憲派。辛亥革命之勢不可逆轉后,他們又竭力維護社會秩序,謀求“和平光復”。有人說商人比其他任何階層都希望穩定,此言不虛。
改革中的先鋒官
轉眼至八十年代初,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從小作坊逐步壯大為百余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有人向上級反映其雇工問題,于是“資本家復辟”“剝削”等說法傳播開來。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并寫下一份報告上報中央。1984年10月,鄧小平做出批示:“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1984年3月,國營石家莊造紙廠因連年虧損難以為繼,業務科長馬勝利主動要求承包經營,僅用時一月便實現盈利。由于馬勝利等人的試驗,促使當時的中央政府下定決心,將發端于農村的承包制引入國企改革,是為“包”字進城。
同是1984年,在全國尚未實施廠長負責制之時,杭州第二中藥廠廠長馮根生向舊體制發出挑戰,率先試行干部聘任制,全廠員工實行勞動合同制。隨后的1991年,面對名目繁多的國有企業廠長考試,馮根生率先“罷考”,引發軒然大波。在《人民日報》等強勢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全國掀起了一股“為企業領導人松綁”的大討論。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時期的中國商人,并沒有特意言政,然而他們率先認識到舊有平衡不復存在,悄然間突破了固有體制的邊界,引領著全國關于改革的討論與進程。
其中頗多冒險與失敗,商人階層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膽魄。雖然他們并無最后的話語決定權,其中許多人更是終成改革“炮灰”。但辟路先行,勇吃螃蟹的壯舉,澤被后世,也堪為后輩企業家之楷模。
時勢
時而張口,時而閉口;時而奮起,時而沉潛;時而阻浩蕩之勢,時而領風氣之先,為什么商人的姿態時常扭轉?
梁任公在百年之前的文章里已說得清清楚楚:“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強有力之法治國之下乃能生存,中國則不知法治為何物也。……股份有限公司,必責任心強固之國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國人則不知有對于公眾之責任者也。……茍非取此不相容者排而去之,則中國實業永無能興之期。”
一無所有之時,當然不怕輸;有產而不得保障之時,自然頗多顧忌——商人所希望的,無非是爭取一點適宜的營商環境而已。達成此點之后,才有可能進一步談家國之事。百家爭鳴之時,商家也愿共鳴,一聲獨大之時,商人只好附和。無論是張口還是閉口,都是時代之下的被迫選擇。
八九十年代的企業家,大都沒什么可輸的,中央政府給幾分支持,他們便敢言敢做。新世紀以來國進民退,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便沒有了說話的底氣。此次關于“在商言商”的討論,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其實都掩身人群之中,并沒有站在太靠前或靠后的位置。
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希望商人“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希望商界領袖,也能成為思想界的領袖,公共話題的領袖。但實際上,商人的勇氣從來都是時代所給予的,而不是由商人去給予這個時代勇氣。歸根結底,我們不能站在遠處,催促他們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