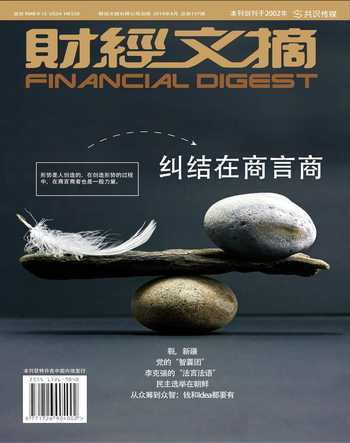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香蕉人”令中國尷尬
劉伯川

在駱家輝結束美國駐中國大使的任期之際,中國的官方媒體發表社論對他進行譴責。文章稱駱家輝為“導盲犬”,并稱駱帶來了一股“歪風邪氣”,更糟的是他被稱為“香蕉人”。
香蕉的外部是黃色的,而內部是白色的,因此被用來詆毀駱家輝,這就和用來詆毀非裔美國人的“奧利奧”以及詆毀拉丁裔美國人的“椰果”一樣。這些詞匯是人們對本種族中族群特征不明顯的一類人的詆毀。
以此推斷,“香蕉人”旨在說明駱家輝雖然有中國血統,但卻不夠中國范兒。他不會講中文,并且不僅不配合中國領導人的命令,反而去西藏訪問,接見持不同政見的人權活動人士,單方面公布北京的霧霾指數,而這些行為都體現出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毫無疑問,駱家輝是地道的美國人,而這確實讓中國的一些時事評論者感到如鯁在喉。
許多中國人反對這樣的稱謂,認為這是一件令人十分難堪的事情。事件本身表明,盡管中國的現代化速度飛快,財富迅速增長,但中國在身份認同方面上仍然是脆弱的,或許是二者的增長造成了這個結果。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篇社論發表于官方媒體。由于政府控制媒體,社論往往只是用來表達高層領導的觀點。這篇文章有可能只是作者的個人觀點,但是在缺乏新聞自由的情況下,誰能肯定呢?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香蕉論”用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將國籍和種族混為一談。在中國,漢族占人口絕大多數,漢族的民族優越感形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架構,同時也滋養了中國與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間領土爭端背后的民族主義情緒。
“香蕉論”的前提是,只要你擁有中國血統,那么無論你身處何處,心中必須認定自己是中國人,并且始終忠于中華民族。
當然,這是美國白人為證明歧視中國移民的合法性而常用的一種想法,而這些中國移民被視為“永久的異族”,無論是19世紀晚期的排華時代還是這個世紀對李文和的迫害都是如此。
但是,這個觀念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錯誤的。即使駱家輝本人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飽覽了中國經典名著甚至能寫一手漂亮的中國書法,但他這個從小住在美國廉價公屋,參加過童子軍,后來成為公訴人、州議員、州長、內閣秘書以及外交官的人,卻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最后,“香蕉論”提醒我們,盡管美國面臨著明顯的挫折以及持續緊張的種族問題,但它在促進新一輪世界人口融合的過程中仍然發揮著無人能及的力量。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在經濟問題沖擊和地緣政治地位相對下降的情況下,與像中國這樣崛起中的大國相比,仍保持著競爭優勢的原因。
簡而言之,美國能產生華裔美國人,但是中國不會也不希望產生美裔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