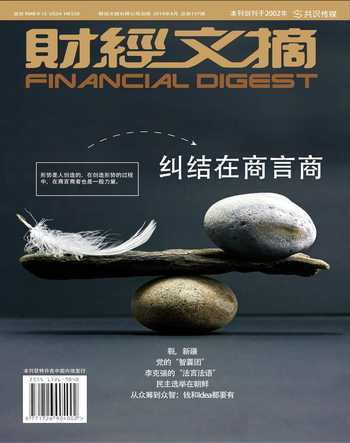剛性兌付不再

2014年注定是中國金融市場不尋常的一年。開年之時中誠信托旗下“誠至金開1號”30億兌付風波有驚無險,隨后吉林信托“松花江77號”又現逾期未兌,一再將信貸違約風險問題推至風口浪尖。
3月4日晚間,*ST超日董事會發布公告稱,“11超日債”第二期利息將無法于原定付息日2014年3月7日按期全額支付,僅能夠按期支付共計人民幣400萬元。這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債券市場出現的第一例實質性違約事件,宣告了中國債券市場“剛性兌付”和“零違約”神話的破滅。
打破剛性兌付
剛性兌付現象是中國近幾年非銀行融資體系(即所謂“影子銀行”)蓬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非正常“中國特色”。一方面,投資者在信托和理財產品上獲得了遠高于銀行存款的收益,而另一方面并未承擔相對應的投資風險。即使在個別產品已經出現事實違約的情況下,銀行、信托公司的托底擔保,地方政府的介入以及神秘第三方的出現,使得投資者至今沒有出現本金損失。
金融改革致力于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融資體系,打破銀行一家獨大的局面,同時為利率自由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是非銀行融資體系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但是,剛性兌付導致了市場的扭曲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道德風險。盡管監管者屢屢發出風險警示,但信托和理財產品仍然在2013年持續大幅增長。
“無論是市場參與者還是政策制定者,對于信貸違約都存在非常糾結的心理。”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說道,“一方面,他們希望盡早打破剛性兌付的怪圈,建立真正市場化意義上的風險定價機制。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一旦第一起信貸違約事件發生,可能導致市場信心的扭轉,大量資金流出信托和理財市場而造成流動性危機。”
債務違約本來是正常不過的經濟現象,政府太多“父愛”和參與者心懷僥幸,才使問題顯得分外可怕。然而,剛性兌付的游戲不可能一直進行下去,拖得越久,傷害越大。首次真正的債券違約還是來了。
“去年11月份,股東大會上,公司高管還拍胸脯說不會打破剛兌。”一位超日債權人表示,當天公司高管一直強調正在著手利息問題,并站在投資人的角度認為,公募債違規影響較大,公司不會成為首例。
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事實上在債券終止上市之前,發行人連續大額虧損、生產線停產、大量借款逾期、涉及訴訟賬戶被查封等嚴重償債風險就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內外部流動性已經枯竭,違約的概率極高,超日公司2013年度債券利率的支付很可能已是依賴外力解決。為什么投資者視信用風險如無物?因為投資此類債券,從未失過手,從未吃過虧。
超日債違約已成事實,接下來的問題是,眾多民企以及產能過剩行業會不會成為違約風險的集中爆發領域——它是第一起,恐怕不會是最后一起。李克強總理在回答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提問時也說道:“你問我是不是愿意看到一些金融產品違約的情況,我怎么能愿意看到呢?但是確實個別情況難以避免,我們必須加強監測,及時處置,確保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讓誰違約?
債券違約意味著什么?有人說,超日債的確打破了剛兌,但并不具有普遍意義。“這起違約案只反映出一個特定行業中一個特定公司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不會導致更多信貸違約的連鎖反應。”
有人說,“超日太陽違約事件是中國債務問題日益加劇的信號”,預示著中國公司債市場上即將出現的一連串違約。
也有人說,讓剛性兌付神話破滅,與其說是為了警示債市,不如說顯示了中國政府加速“去產能”的決心。“對那些陷入困境、靠‘輸血度日,或者依靠借新還舊延續生命的僵尸企業中止救助,以便激發中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
但無論如何,市場的普遍認識是,中國政府會區別對待經營不善的民企和國企。例如,太陽能電池制造商天威保變在連續兩年報出虧損之后,該公司發行的債券上周被暫停公開交易。但與超日太陽能不同的是,天威的控股方是國家。去年超日太陽能被停牌時,其債券已被降級兩次,只比垃圾評級高了三檔。而天威盡管被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其政府背景卻令其債券保住AA評級,比頂級的AAA級只低兩檔。某固定收益產品交易員表示:“評級反映了天威的政治地位,而非財務狀況。這仍是觀察中國各種情況的準確方式。”
中金公司也持相同的觀點:“如果說發生了什么變化,那就是認為帶政府背景的企業風險較低的觀點得到了強化。”
過去幾年內企業債與信托市場的急劇擴張,已經導致相關產品平均質量的下降,恐怕超日違約不會成為孤立案例,而是2014年中國企業債與信托產品一系列違約的開始。同時,中央與地方政府會嚴格管控,以防企業債市場爆發系統性風險。畢竟在超日之前諸多瀕臨違約的案例,最終都因為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的介入而最終兌付。相關監管部門只需制造一些違約事件,一面向參與者提示風險,一面把違約沖擊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而選擇哪些公司債違約,左右掂量,還是超日這樣無擔保的中小型民企最為合適。
吳桐根據《金融時報》《每日經濟新聞》等綜合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