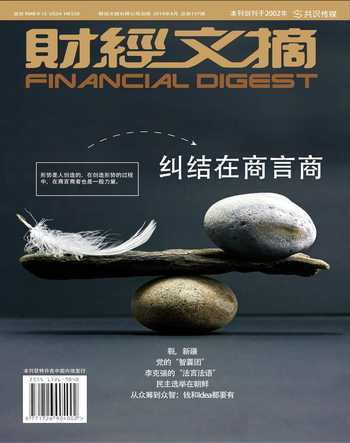別讓反思變成了洗白
張白燁


昆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立即引起強烈震動。很多人都在聲色俱厲地譴責恐怖分子,并表達詩一般的哀悼。然而,卻也有一批自由派傾向的媒體人和公共知識分子不識時務地提醒大眾,要反思新疆問題的根源,并有意無意地將矛頭指向中央的民族政策。
輿論的兩種反應激烈碰撞,前者被指責“嘴皮子上占領道德高地”“讓情緒凌駕于智商之上”,后者則被批評為“假裝深刻”“替犯罪分子洗白”,唇槍舌劍,唾沫橫飛。
如果這是一場戰斗的話,勝利顯然屬于前者,一向能言善辯的媒體人、知識分子被群眾的憤怒湮沒,他們在微博上的發言被截圖、拖出來展覽,仿佛對暴力事件的反思成為了人人喊打的可恥行為。
事實上,這并非孤例,在近年來的很多起暴力事件中,輿論都呈現出類似的裂紋——自由知識分子自以為冷靜、理性的反思,在普通人看來只是為施暴者洗白,他們假裝圣父圣母,將人性固有之惡抹除,轉而對公權力進行鞭撻。這種長久以來的習慣性動作,引發了反彈,很多人即便無意為公權力站臺和辯護,也開始朝“公知”吐口水。
反思是如何變成洗白的呢?不妨跳過這起恐怖襲擊,從更常見的平民暴力事件看起。
去年8月,四川成都和河南安陽分別發生兩起公交車持刀行兇案。“僅僅數分鐘,15人倒在那血泊之中,其中4人殞命刀下,傷者年齡最小的僅為10歲”,“搶奪公交車方向盤不成,便持刀傷人,造成3死15傷,最小的死者剛滿10個月”。兩起事件極端暴力、場面慘不忍睹。
然而,無論社交媒體還是紙媒對事件的評論卻都呈現出用體制及社會原罪論為這些罪犯辯護的傾向。“為何‘便民公交淪為‘奪命公交,何以讓一名普通平常之人突變為極端暴力的兇手,將罪惡的屠刀伸向了無辜的、素不相識的路人?……在利益多元化、訴求多樣化、問題復雜化的今天,合理需求受不到公平保證、合情訴求得不到有效表達、合法權益得不到公正保護,導致社會心態發生改變,以至于歪風又起,邪氣不斷,戾氣郁結,是造成很多類似悲劇的深層次原因。”
引自某主流媒體網站的這段時評,正是許多媒體人和知識分子的典型思路——社會戾氣和體制弊端更應該為暴行負責。我們在幼兒園殺童案、重慶女童摔嬰案等許多暴力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評論,這些紙上文章,避實就虛,看似深刻,實則賣弄,更重要的是忽略了慘案受害者的脆弱心理,甚至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在另外一些帶有“反抗公權壓迫”性質的暴力案件中,這種“反思”更加泛濫。如夏俊峰殺城管案、陳水總廈門BRT公交爆炸案,以及多年前的楊佳殺警案,媒體跟風報道施暴者人生經歷和家庭生活,肆意延伸,將他們刻畫成被體制和社會碾壓的弱者。本該受到譴責和嚴懲的濫殺無辜,反倒成了民不畏死的壯舉。
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反過來,可恨之人也總能找到值得同情的地方,但這可憐之處并不能構成報復社會的理由。在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事件中,反向推導的因果鏈比一般的犯罪行為更為模糊。我們應該承認一個無奈的現實:性善論并不能套用到所有人頭上,總會有極個別人因為先天基因或后天環境,犯下反人類的暴行。將“壓迫”作為統一格式的既定解釋,既無助于減輕“壓迫”,更可能激勵無差別的暴行。
反思被解讀為洗白,以監督公權為己任的媒體人和知識分子們自然覺得委屈。一方面,面對政黨利益,他們的發言是危險的;另一方面,面對公眾的詰難,他們又成為虛偽的作秀者、裝逼犯,可謂兩頭不討好。
簡單地將輿論的反彈理解為民粹化的表現既不會讓自己顯得高人一等,也無益于彌合不同群體間的矛盾。媒體和讀書人需要反省自己的思維定勢,社會心理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理念層面刻舟求劍,就意味著在現實中的一敗涂地。
對于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沿襲舊套路的反思理當摒棄。但這是因為那種反思相當輕率和懶惰,而不是說知識分子和媒體人可以放棄反思、放棄思考,讓以暴易暴的情緒充斥社會。針對類似事件,目前急需改善的是提高言論的專業性,把握更深層的事實,增加多元性,避免主題先行,并切忌將反思變成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