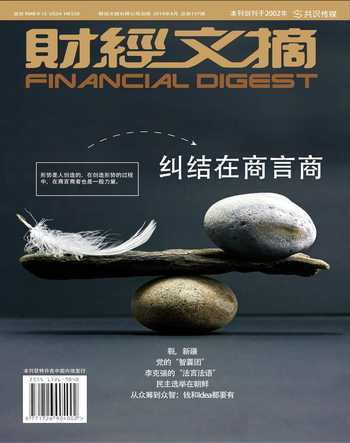校園團契的“脫敏”能否發生?
曹小強
校園團契這幾年在高校發展迅速,就筆者采訪的南昌高校來看,每所高校(內部或附近)都有兩到三個團契,每個團契的人數多則20以上,少的也有10個左右。一般來說,校園團契都會有牧師或傳道人帶領,這部分人中有的是高校教師有的則是一些大的教會差派而來的,像筆者采寫的《南昌的校園團契》一文中提到的章老師以及高牧師就是代表。
如果把校園團契當作一個常態組織來看,那這個組織的凝聚力與發展程度,和帶領者有著直接的關系。帶領者的個人魅力與講道水平會影響到大學生的去留,進一步影響大學生能否成為信徒。在采訪時,高牧師告訴筆者,很多學生是跟著同學一起來的,他們只是看看,覺得有意思下次就還會來,沒意思的話就不會再來了。所以要留住學生,講的東西得吸引他們。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看他們自己愿不愿意跳出意識形態教育的束縛,相信有上帝。
外界對校園團契普遍有種妖魔化印象,大部分是因為團契的傳道方式,以及團契生活的不公開,這也說出了校園團契的尷尬處境。校園團契一般都在居民住宅里進行,而且地點常常不固定,每次活動為十幾人到幾十人,低調隱蔽、小型分散、因陋就簡、不重形式。校園團契不具備合法身份,長期處于“地下狀態”,這是校園團契面臨的最大難題。按照政府的現行政策規定,沒有三自教會的認可與推薦,任何一個新設立的教會都無法在地方政府管理部門登記注冊。校園團契嚴格意義上屬于家庭教會的一部分,因而,這就使校園團契客觀上處于與政府的宗教管理體制對立的狀態,成為一種事實上存在但卻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的組織。
在筆者采訪章老師時,章老師就表達了他最大的擔心。校園團契常常會受到學校統戰部與學校所轄片區派出所的干擾,像筆者采訪的團契中的學生與教師就曾被學校統戰部約談,或者被派出所以非法集會的理由帶走。在周日的敬拜上,高牧師通知大家下周敬拜換地方,也是因為收到了警告。
學者劉澎長期研究中國家庭教會,在他看來,走出“地下”,接受場所備案,實現“陽光化”,對家庭教會來說是一場巨大的轉變,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思考、觀察,反復激烈的內部討論,才有可能接受。不過筆者在采訪中深深地體會到,要想走出“地下”,首先當去除外界對校園團契的妖魔化印象,抱著理解的心態去看待學生基督徒的信仰緣由與團契生活,這將是校園團契“脫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