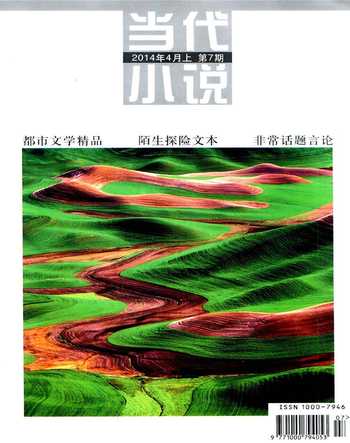半生
尹群
高中畢業二十多年之后,多年難得一見的老同學,見面的機會一下子多了起來。到了這個年齡段,不是你家的孩子升學,就是他家的孩子結婚,各種“升學宴”、“結婚宴”接二連三。于是,天各一方的老同學,借喝酒的引子,大老遠地湊到一起,見見面,敘敘舊,跟女同學半真半假地開開玩笑——念書的時候可是連句話也不敢說呀,感嘆一番“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似極快意。可是呢,左一次喝酒,右一次聚會,卻從沒見到過陳萬喜。
我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姓廉,廉老師,教我們語文。如今已經快七十歲了,銀發如雪,見了我們這些二十多年以前的學生,親熱得不得了,拉住手不松開,打聽這個怎么樣,打聽那個怎么樣。打聽最多的正是陳萬喜。別人,我們還能給廉老師提供點訊息,可是關于陳萬喜,我們卻誰也說不上他的近況如何。連當時跟陳萬喜住一個大隊,倆人時常在一塊兒走路的同學趙亮,跟大家聯系得比較多,都以為他會知道些啥,可是一問陳萬喜現在怎么樣,他也是直抓光頭,說不出個子丑寅卯。對于大家來說,我們的老同學陳萬喜可謂是銷聲匿跡下落不明。
看得出廉老師的失望。酒桌上滿懷希望地瞅著我們,端著酒杯的手哆嗦得很明顯,挨個囑咐,樣子竟像是懇求,誰有了陳萬喜的消息,知道陳萬喜的電話,應該馬上告訴他。臨別再一次拍著各位的肩膀鄭重地叮囑一番。看著大家露出的疑惑,有一次喝得有幾分酒意的廉老師,終于告訴我們,他想當面向陳萬喜道個歉。他當年做過一件對不起陳萬喜的事。廉老師重重地嘆息一聲。
陳萬喜跟我們在一起念書的時候,我們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少年。陳萬喜似乎還要比我們大上一點。長得比誰都結實,掰手腕子,沒人能掰得過他,全是他的手下敗將。為此陳萬喜有點沾沾自喜。在家里,什么農活都幫大人干。上學來,身上還帶著勞動的泥土。陳萬喜的父親身體不大好,有肺病,咳嗽,常年吃藥,干不了重活,家中日子過得緊巴。那時候本來同學們的穿戴都很差,可陳萬喜的穿戴更是比誰都差。陳萬喜不愛說話,寡言少語。也不淘氣。下雨天,操場上沒法玩,就在屋里,變著法地玩。誰想出個怪主意,在黑板上用粉筆畫個不大的圓圈,然后站到教室的后面,從鞋底兒上摳下泥,摶成蛋兒,往那白白的圓圈里投,像投標,像打靶,看誰準。男生幾乎都參加進來。不一會兒,黑板上就粘滿了密密麻麻的黑泥球。惟獨陳萬喜站在一邊看,頂多跟著呲牙樂一樂。一樂,露一口白牙。陳萬喜的牙居然很白。陳萬喜居然天天刷牙。而那時的我們,還沒有天天刷牙的習慣。也許是陳萬喜面相長得黑的關系,牙就顯得格外白。所以,班級里,論臉長得最黑的,數陳萬喜,論牙長得最白的,也數陳萬喜。好像是,陳萬喜特別愛自己的牙,也愛樂。一樂,露一口白牙。兜里揣個飯碗底兒那么小的一個小圓鏡子,沒人的時候偷著拿出來照照,摩挲摩挲頭發。這是誰都想不到的。因為只有女生兜里喜歡揣那玩意兒。有一回鏡子被同桌無意中掏落到地上。同桌是掏爆米花吃,卻掏出個圓圓的小鏡子。小鏡子像車轱轆似的滾出老遠,陳萬喜的臉登時羞得通紅。陳萬喜害怕女生。面對女生的時候,總是羞答答的,溫順得像個小貓,說話的聲音也小得像個貓,誰都聽不見,聲音含在嗓子眼里,跟人掰腕子的那股兇狠勁兒一點也沒有了。不像趙亮那樣,愿意往女生跟前湊,越有女生越是興奮,越能嘚瑟,咋咋呼呼。趙亮個高,精神,籃球打得好,穿戴也好,有嘚瑟的資本。陳萬喜相反。陳萬喜是見著女生就躲。自卑也好,害羞也罷,反正不敢往前湊,而是往后躲。當然,學習方面嘛也算不上刻苦。書本放在桌子上,翻開,看意思也想學,可是呢,拿起書本就犯困,就不由自主,沒瞧上兩行,眼皮打起架來,一個勁磕頭。便用雙手托住下巴。眼皮勉強睜著,卻半天也不見翻一篇兒。多數時候,就那么睡著了。有時候,同桌會拔根頭發絲,伸進他的耳朵眼里,陳萬喜耳朵一癢,醒了。老師同學都說陳萬喜是個“大覺迷”。書包挺大,卻是癟癟的。開學之初作業本還樣樣齊全,沒多久,就缺胳膊少腿,被他爹撕去卷煙了。用老師的話說,學習目的不明確。不光是陳萬喜,那時候,大家的學習目的都不明確。念完書干啥呢?還不是回鄉務農。書念得好壞,全憑個人愛好和興趣。在遵守紀律,響應學校號召方面,沒說的,陳萬喜絕對是個好學生。學校有什么勞動,揀糧揀柴,抹平房,鏟操場,掏廁所,或者農忙季節上生產隊去“支農”,班主任廉老師對陳萬喜的評語是“熱愛勞動,助人為樂”。回回都能當上“勞模”,上“光榮榜”。
陳萬喜出事那年,是個夏天。應該是暑假開學后不久,同學當中偷偷流傳一種說法,說陳萬喜……說陳萬喜偷看女生上廁所。乍一聽,我們都嚇出一身的雞皮疙瘩,不相信是真的。我們學校的廁所,在教室的后面,是學生們自己就地挖土,再拌上麥秸,不用脫坯,直接挑水和泥,用洋鍤一鍤一鍤插起來的。很簡陋,既無門,也沒頂,只有那么個一人多高的土墻圍成的四框。里邊挖溜深溝,便是糞池子。糞池上面,順著,擔著兩根方木頭,木頭上再橫著釘了一塊一塊的寬木板。一長溜廁所,中間被一道土墻隔開,一面是男廁所,一面是女廁所。年頭一久,風吹雨打,墻頭越來越矮。過去真的不止一次發生過有人扒墻頭看女生上廁所的事。把女生嚇得,怎么說呢,不顧一切,拎著褲子跑出來。你想,人家正蹲在那里解手,猛然發現身后的墻頭上趴著一張臉,呼哧呼哧的,不嚇死才怪呢!有的女生不只是嚇得尖利的哭叫那么簡單。有的女生甚至有種沒臉見人的感覺,從此再不肯來上學。輟學了。人們當然要罵那個扒墻頭的人,是流氓什么的。陳萬喜,那么厚道的人,能干這種事?不可能吧。觀察陳萬喜,也跟平常沒啥兩樣。雖然半信半疑,但大家看陳萬喜的眼光里就多少含著些鄙夷。陳萬喜似乎也覺察到了大家眼神的異樣,心里明白他偷看女生上廁所的事大概是被人知道了,所以見了誰目光都是躲躲閃閃,也不說話,把頭低下來匆匆走路。因為臉黑,看不出臉紅不紅。本來就不怎么合群的他,這下就更是獨來獨往了。曠課的情況也越來越多。大家都以為陳萬喜要念不下去了。其實在陳萬喜偷看女生上廁所這件事情上,我們男生更感興趣的,是陳萬喜究竟看到了什么,那個被陳萬喜偷看的倒霉女生又是誰。陳萬喜看到了什么,除了他本人,別人無從知曉。這將永遠是個謎。而那個被這小子偷看的女生,她到底是誰呢?被人看了之后,會是個什么樣子?都很焦急。一面悄悄打聽,一面胡亂地猜疑。七嘴八舌,猜這個,猜那個,基本都往長得好看的女生身上猜。卻始終確定不了是誰。于是大家便把希望寄托在班主任廉老師身上,以為班主任老師肯定要在班級說這件事。班主任在前面一說,大家就會看到那個趴在桌子上不敢抬頭的女生,肯定就是被陳萬喜偷看的人無疑。可是班主任廉老師一直也沒有說。就好像廉老師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似的。我們像熱鍋上的螞蟻,廉老師卻若無其事。說實在的,當時我們每個男生的心情都差不多,都十分迫切地想揭開這個天大的謎底。甚至,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樣子,比比看,到底誰的眼光厲害,能最先把這個謎底揭開,把那個被陳萬喜偷看的女生給發掘出來。結果呢,看誰都像是被陳萬喜偷看過。女生們見我們男生用幸災樂禍的眼神,賊溜溜地盯著她們不放,立刻就不自在起來,連走路也一順邊了。全用白眼仁翻楞我們,嘴里嘟噥著什么,看口型是“缺德”兩個字,把脖子狠勁扭一邊去。
沒幾天,被陳萬喜偷看的女生終于有了眉目,不過不是我們的發現,是傳言又出來了。說是黃云香。黃云香跟陳萬喜是一個大隊的,平時接觸的機會比別人多一些。據說,那天,黃云香上學,走在莊稼茂密的田間小路上。由于莊稼的遮擋,黃云香沒有注意身后不遠還走著陳萬喜。黃云香可能當時有點內急,就拐進旁邊的苞米地去解手。關鍵是黃云香沒有往苞米地里多走幾步。一個呢,可能是黃云香以為跟前沒人,一個呢也可能是黃云香有點害怕,結果黃云香還沒有起來,還蹲在苞米地里,陳萬喜就走過來了。誰也說不上陳萬喜知不知道黃云香是進地里去解手的。陳萬喜一過來,黃云香就慌慌地提褲子。結果越慌亂,越是不能順利地把褲子提到位。提上了,卻系不上褲帶。褲帶半天摸不到。陳萬喜呢,就那么傻傻地看著,也不把頭轉一邊去。等黃云香前面拎著書包跑了,陳萬喜才回過神來。還有個說法,說的不是早晨迎著朝陽上學,而是晚上放學,是黃昏時分,剛下過一陣雨,晚霞穿透云朵,普照大地。樹木,莊稼,草地,村莊,還有村莊上空飄著的裊裊炊煙,還有天上的燕子,地上的牛羊,統統籠罩在橘紅色的霞光里。莊稼葉子上,樹葉上,草葉上,都還掛著亮晶晶的雨滴,晚霞一照,映射出萬道霞光。遠處有片葵花,更是黃澄澄的鮮亮無比,葵花們擁擁擠擠,爭著把一張張嫵媚的笑臉獻給迷人的晚霞。這種景象,往往會令人情緒陡然高漲,詩情畫意涌上心頭。可惜陳萬喜不會寫詩,也不會作畫。陳萬喜當時是個啥心情,激沒激動,不得而知。陳萬喜一直慢慢跟在黃云香的后面,不遠不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說是跟蹤、尾隨也行,說是保護也行。黃云香走著走著就拐進了旁邊的苞米地。黃云香啥時不見的,陳萬喜沒注意。陳萬喜被遠處耀眼的葵花吸引了。葵花向陽,葵花真美。陳萬喜大概就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陳萬喜唱著唱著就不走了,站下,站在那兒,可能是納悶黃云香怎么不見了呢?正納悶呢,聽見里面有聲音,陳萬喜忽然蹲下,把頭歪得很低,從苞米葉子的下面,往里看。
不管是哪一個說法,反正黃云香解手被陳萬喜偷看的事很快傳開了。我們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才知道廉老師當時是知道這件事的。而且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我們當時就猜,是誰把這件事說出來的呢?是黃云香自己嗎?那樣的話,黃云香是不是有點傻?自己的屁股被人看,也不算什么光彩事,還天 著臉告訴別人?可是,不是黃云香自己把這事說出來,還能有第三個人知道這件事?陳萬喜自己絕不會說。后來人們就推斷,陳萬喜看黃云香解手的時候,在他的身后,還有別的學生,正好把這一幕看在眼里。那么,這個親眼目睹了偷看事件的第三個人又是誰呢?
廉老師怎么知道的,是聽誰說的,只有廉老師自己知道。廉老師雖然表面上沒有什么反應,但心里其實是很生氣的。對陳萬喜的印象一下子改變了。無論陳萬喜再怎么能干,再也沒有當上過“勞模”。那一年的期末鑒定,廉老師給他作的也不好,把“品行不端”這樣的話干脆寫進了鑒定里。這是廉老師在二十多年后,一次喝酒的時候跟我們說的。廉老師在二十多年后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內心充滿了悔恨。廉老師說他當時不應該感情用事。
我們畢業之后全班四十幾個同學就都作鳥獸散了。記得當時全班同學騎著自行車,跑了三四十里地,上鄰縣縣城照了張畢業相,因為我們公社中學所在地距離鄰縣縣城比本縣縣城近一半還多。許多年以后,我才偶然發現,那張畢業照上,沒有陳萬喜。
廉老師說,他當時的那個所謂“實事求是”的鑒定,給陳萬喜后來的人生道路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什么樣不利的影響呢?我們只有通過與陳萬喜住一個屯子的同學趙亮了解。關于陳萬喜畢業之后的情況,趙亮知道的應該比我們多一些。陳萬喜畢業之后先是要當兵,身體檢查完全合格,家庭成分是貧農,社會關系也好,歷史也清白,這樣,政審完全沒有問題。可弄來弄去,后來卻沒當上。過兩年,大慶油田來招工,比陳萬喜條件差的都招上了,到最后,弄來弄去,惟獨把陳萬喜給刷下來了。人們都被這樣的結果搞得莫名其妙。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會是廉老師的那份期末鑒定壞了事。當時,部隊的人,招工的人,都上陳萬喜上學的學校了解過情況,連陳萬喜上小學的學校都去過了。翻出了有關陳萬喜的檔案材料,看到“品行不端”這樣的鑒定,事情就徹底涼快了。陳萬喜什么也沒當成,把陳萬喜有病的父親氣得病情更加嚴重了,咳嗽個不停,翻著白眼珠罵陳萬喜,罵一陣還要停下來喘上一會兒,吐一陣痰。按著陳萬喜他爹的脾氣,若是早先,陳萬喜這頓打早挨到身上了,可如今陳萬喜他爹已經沒了打人的力氣,打不動了。陳萬喜他爹罵得最多的就是,陳萬喜丟了老陳家的臉!你個沒出息的雜種!你叫我這張老臉往哪兒擱啊?陳萬喜他爹打不動陳萬喜,就倉房里翻出根麻繩,哆嗦著要去上吊。陳萬喜的母親唉聲嘆氣的,抹著眼淚在身后罵,你個老不死的!家里出了一個丟人現眼的還不夠,你也去丟人現眼嗎?
趙亮他爹是大隊支書,當了一輩子,老了得了中風,半面身子麻,趙亮接了班。趙亮根紅苗正,一當也當了十幾年。或許是當領導當得年頭多了,歷練出來了,早不像念書時咋咋呼呼的樣子,變得沉穩,自信。肥頭大耳,滿面紅光,偏又喜歡剃個光頭,看著,像個和尚。塊頭大,往那兒一坐,能壓住陣角,顯得很有魄力。只是,也是當領導當得年頭多了,尤其是農村的基層領導,說話句句都帶個啷當,不罵人不說話。一罵,好像威嚴哪,魄力呀,就都有了。
據趙亮講,陳萬喜在當地說不上媳婦。沒有人家愿意把姑娘嫁給他。一個呢是因為他家窮,一個呢是因為,陳萬喜的名聲臭。再后來,趙亮也不知道陳萬喜上哪兒去了。起初陳萬喜的父母健在的時候,每年還能見陳萬喜回來兩回。問他也不說在啥地方,也不說干啥,也不說咋樣,什么也不說。等陳萬喜的父母沒了,陳萬喜再沒回來過。說起陳萬喜,趙亮似乎頗有些感慨,說想起小時候的事,怪好笑的。嘴上說“怪好笑的”,臉上卻又笑不出來。表情復雜,語調滯重。便掏出煙來,狠狠地吸上一口,再徐徐地吹出,吹出一線淡淡的白煙。
陳萬喜出事之后,廉老師背后找陳萬喜問過,廉老師說他是出于關心學生的目的。他得讓他的學生走正路,他不能眼看他的學生走上犯罪的道路。廉老師說,陳萬喜臉紫得像豬肝,低著頭,摳手指蓋,不說話,就是不說話,到最后啥也沒說。廉老師由此認定傳言不虛了。其實,即使陳萬喜真的看見黃云香在苞米地里解手了,到底是故意看的,還是無意中看見的,我們并沒有弄清楚啊。廉老師這樣說,是后悔當時聽信了那個傳言,并且很武斷地給陳萬喜作了“品行不端”那樣的鑒定,白紙黑字寫在了紙上。
廉老師一再吩咐我們大家,誰有了陳萬喜的消息,一定告訴他。廉老師把他的手機號留給大家。
說說黃云香吧。黃云香呢也是一次都沒有參加過我們這些同學的各種酒宴。大家在說到黃云香的時候,忽然就把音調壓低下來,就像當年人們說“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一樣”,神神秘秘的。關于黃云香后來的情況,大體是根據趙亮所述,真實與否,有待考證。黃云香畢業之后,在當地嫁不出去,都知道她在苞米地解手被人偷看的事。其實,這本來并不是多大的事,不就是解個手被人看見了嗎?但屯子人不這么想。屯子人在男女關系方面,具有更濃厚的興趣,更豐富的經驗,更浪漫的想象力。可不能小看了那些婦女,閑來無事,走東家,串西家,嘴里呸呸地飛著瓜子皮兒,說,那么大片苞米地呀,就他兩個人,你想啊,能是光看看的事嗎?誰信哪?說死也不信哪!末了用鼻子哼一聲,這個小喜子,蔫了吧嘰的,想不到還有這么大膽子!你說說!不知是夸陳萬喜膽子大呢還是羨慕陳萬喜有艷福。拋開屯子人怎么想不說,單說這個事,屯子人怎么也知道了呢?有一段時間,吃過晚飯沒啥事,屁股往炕沿邊上一坐,腦袋挨著腦袋,嘰嘰喳喳,嘰嘰喳喳,不說別的,全說老陳家的小喜子跟老黃家的小香子怎么怎么。什么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就是。屯子人稱呼誰,不習慣稱呼人的大名,習慣叫小名,即乳名。看見黃云香,管黃云香叫“老黃家的小香子”,無論老爺們還是老娘們,都用那樣一種特殊的眼神,賊亮賊亮,肆無忌憚地盯著黃云香看。黃云香遠遠過來的時候,他們盯著人家前面看,等黃云香慌慌地走過去了,他們還要盯著人家的后面看,一直看出老遠,看不清了,看不見了。看什么呢?前面吧看黃云香的肚子大沒大,后面吧看黃云香的腰粗沒粗,就是想看出黃云香還是不是個閨女。黃云香后來遠嫁內蒙古,具體地點好像是大雁煤礦,丈夫是個煤礦工人,是不是下井挖煤不知道。因為遠,黃云香回家的次數也少。連她的家里人都不知道黃云香在那邊的日子究竟過得怎么樣。
廉老師有一天忽然接到趙亮的電話,趙亮告訴他,說他有了陳萬喜的下落啦。廉老師一聽很激動。能不激動嗎?趙亮說,是他老婆打聽到的。趙亮是替他老婆邀功的口氣。趙亮的老婆跟黃云香的妹妹關系挺好,春節回家,趙亮的老婆去看她,閑說話說到黃云香,黃云香的妹妹說,開始的時候,黃云香的丈夫不下礦井,工作挺清閑,但掙得沒有下井多。后來就主動要求下井。沒幾年就出了事故,在一次塌方中,同組的工人砸死兩個,黃云香的丈夫揀了一條命,只是砸斷了腿。屬于工傷,從此在家呆著,礦上照樣給開工資。這樣一來,家里外頭,就全靠黃云香了。要不是有陳萬喜,黃云香的日子不知道有多難呢。黃云香的妹妹無意中說出了陳萬喜。趙亮的老婆就問哪個陳萬喜?黃云香的妹妹說還能有哪個陳萬喜?陳萬喜當初打聽到黃云香嫁到大雁煤礦之后,便只身一人千里迢迢來到大雁煤礦,下井挖煤。趙亮的老婆問黃云香的妹妹,陳萬喜肯定是撲奔黃云香去的。黃云香的妹妹不置可否,說陳萬喜去大雁煤礦,開始她姐姐黃云香不知道,后來才知道的。趙亮的老婆就疑惑了,說那陳萬喜為什么上那么遠的大雁煤礦去挖煤?趙亮的老婆心里明鏡似的,陳萬喜就是奔黃云香去的。黃云香不在大雁煤礦,陳萬喜怎么會上那去?那么遠?千里迢迢的。黃云香的妹妹恨恨的,說他那個人,有毛病!黃云香的妹妹說陳萬喜的腦子有毛病,其實是有點恨陳萬喜。不是因為陳萬喜,她姐姐也不能嫁到那么遠。趙亮的老婆心里就有幾分感觸,鼻子發酸,眼圈一下子紅了。不過嘴上卻說,陳萬喜這個人,賊心不死,心里一直惦記著你姐姐黃云香呢!
陳萬喜在大雁煤礦屬于盲流身份。因為肯吃苦,干得好,再加上黃云香找了丈夫的親戚幫忙,后來回家把戶口起去落在了大雁煤礦。黃云香的丈夫出事之后,家里有啥事,黃云香都去找陳萬喜。在別人眼里,黃云香跟陳萬喜是黑龍江老鄉,關系比一般人近是很正常的。黃云香的妹妹則透露說,陳萬喜從小就黏糊她姐姐。念書的時候,學校干個啥活,揀糧揀柴,陳萬喜每回都偷偷幫黃云香揀,幫黃云香扛。黃云香呢,從不吭聲,也不說謝,也不拒絕。
陳萬喜打光棍打了十幾年,一直到三十大幾了,在黃云香的撮合下,才娶了個當地的年輕寡婦。煤礦寡婦多。黃云香早就有意幫陳萬喜成個家,陳萬喜始終不同意。黃云香知道陳萬喜的心思。對陳萬喜說,你這是何苦呢!好歹有個家,回家吃口熱乎飯,晚上有人暖被窩,不比一個人強?眼瞅半輩子就這么過去啦!陳萬喜每天工作在黑暗的礦井下,臉更黑,牙更白。陳萬喜大膽地看著黃云香。看著黃云香頭上的幾根白頭發在陽光里一閃一閃,咧咧嘴。嘴唇嚅動著,似有千言萬語,最后只憋出一個字:姐……
廉老師良久無語。廉老師問趙亮知道陳萬喜的電話不,趙亮說不知道。廉老師說趕緊,讓你媳婦再問問。廉老師說,這輩子如果不親口跟陳萬喜說句對不起,就是死了這眼睛也閉不上啊!
不過趙亮并沒有把他老婆打聽到的事全部說出來。趙亮的老婆通過黃云香的妹妹,還知道了趙亮當年也看上了黃云香,但黃云香看不上趙亮。無論趙亮怎么像靠近組織那樣靠近黃云香,黃云香始終對趙亮不理不睬。黃云香每天是走著去上學,所以比誰都走得早。路上常常只有黃云香一個人。趙亮騎自行車,從后面趕上來,要帶黃云香。黃云香不干。趙亮在路中間挨著黃云香騎,黃云香就靠到路邊去走。趙亮上路邊上再挨著黃云香騎,黃云香就上路中間去走。趙亮再上路中間騎,黃云香就再靠到路邊去走。趙亮干脆下來,推著自行車跟著黃云香走。黃云香就往地里走。地里有壟溝,有莊稼,自行車沒法推。趙亮看見過陳萬喜幫黃云香拿過東西。趙亮也想學陳萬喜的樣子靠近黃云香,要用自己的自行車幫黃云香帶柴火,帶糧食,帶糞,干什么黃云香都一概拒絕。趙亮就有那么點悲哀。傷心地想,我還不如陳萬喜嗎?那么窮,那么黑,一杠子壓不出個屁!不就是牙白點嗎?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