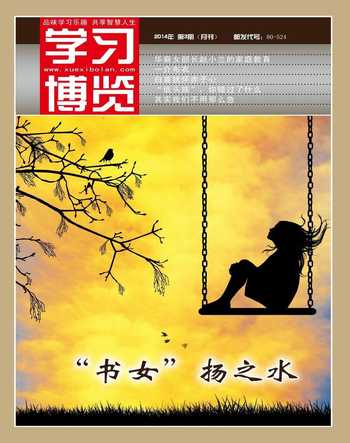觀點
中國的年輕一代有膽量關心政治嗎?
亞歷克·阿什
在中國,二十幾歲的這一群體被共同稱為80后、90后。表面上看,這些年輕人對政治普遍冷漠,就連國家領導人換屆選舉也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與我們無關”。這種冷漠的背后有四個理由:
第一,政治無聊。媒體總是單調乏味地報道政治的結果,而非其過程。每個學齡兒童都要接受大量的思想政治必修課教育,枯燥乏味的課程內容讓學生一輩子都不想碰政治。
第二,政治很危險。在一個由專制權力來決定是非對錯的體系里,人會自然發展出一種內在的晴雨表,以告訴自己什么可說可做,什么不能說不能做。當然,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但是,這一代的父母經歷過政治風雨,他們會設法教導孩子——最好遠離政治。
第三,政治沒有優先性。有太多的競爭——學校,工作和配偶。有太多的經濟壓力——買房,買車,贍養父母。還有太多的分心之事——性愛,娛樂,毒品,以及魔獸世界。
最后,政治無望。既然知道自己無可奈何,為什么還要自討苦吃?你不是無意于此,也不是沒有膽量——你只是正視現實罷了。
但是個體卻與政治息息相關。年輕人的權利意識更強,期望更高,承擔的風險也更少了,因此他們有更大地勇氣去伸張。
(亞歷克·阿什,自由作家,居住北京,《洛杉磯時報書評》記者。譯言網)
社會的“心態緊張”消磨中國的改革能力
郭于華
80年代改革有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相伴。那時候有比較開闊的胸襟,開放的心態,開明的思想,使社會活力充分釋放出來。一次改革,實際上要釋放社會的活力,帶動整個經濟社會文化的改變,帶來一種生機,一種發展。但是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這些,神經比較緊繃。
80年代改革開放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各個階層普遍都有奔頭,覺得只要努力,只要付出了,就有相應的收獲,可能會改變處境,改善生活,提升社會地位。
但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經濟結構變了,而且走得很快,但是政治結構跟不上,已經有點尾大不掉了。
重建社會或許是唯一出路。社會建設至少應包括或可始于以下基本面向:首先需要制約權力,法律至上,真正落實依法治國,權力不能比法律大。
建設社會,首先是把社會領域內的事辦好,如大力發展科教文衛等社會事業,改善社會管理和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等。作為獨立于國家和市場之外的主體,社會建設即培育一個獨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體性社會。另外政府要信息透明,有暢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實現公民的知情權——了解真相的權利;有真相才有信任,信任了才有信心,不至于有絕望、無安全感、猜謎等心態。完善利益表達,承認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社會建設的應有之義。公民需要通過社會參與來實現和保護個人權利;常規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也必不可少。一個健全的體制應該容納各種合法的表達方式,包括信訪、上訪和通過各類媒體的意見、質疑和批評的發表,也包括集會、游行、請愿、對話等法律框架內的抗爭表達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嚴防死守、草木皆兵,壓制社會訴求。
(《南風窗》)
校長脫“官帽”為何難推行?
線教平
蘇州推行校長職級制,成為教育圈一大熱門話題。此前已有上海、廣東中山、山東濰坊、安徽馬鞍山等多地先后為中小學校長摘了“官帽”。然而該項制度并未在全國推行。
校長職級制落實往往涉及三個問題:門檻,評價,評價后的職級待遇。實現真正的去行政化,評價的主體要十分清晰——到底誰說了算?校長是為公共教育服務的公職人員,其選拔或考核的主動權理應交給學生、家長與公眾。但目前,校長的選拔、培養、使用、評價等環節,仍牢牢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門手中。
理順政校關系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放權;二是監管,建立科學、高效、全面的評價體系。新加坡實施校長評價由校長的直屬上司“校群領導”負責,以“360度”評估法中的自我評價為核心,評價者是與校長親密接觸的人員,如上司、同行、學生及其家長、社區負責人、職員、教師(中層干部)等;而美國校長評價由縣教育行政長官組織教育中介或行業協會進行,如權威的校長評價機構全美校長聯合會。
陶行知先生在《整個的校長》一文中談到:“國家把整個的學校交給你,要你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校長職級制”并非以等級看其優劣,根本上還是以此力量鞭策、鼓勵校長更好地治校和前行,倘若“四級六等”級別異化為新的行政職級的追逐,很可能背離制度改革的初衷。
(人民網教育頻道)
污染與治理:發達國家前車之鑒
梅雪芹
環境污染發生質的變化并演變成一種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危機,始于18世紀末興起的工業革命。首先是英國,而后是歐洲其他國家、美國及日本,伴隨重工業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推進,出現了煙霧騰騰的城鎮,河流等水體也嚴重受害。此后,隨著汽車工業和石油與有機化工的發展,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們消耗大量資源和原料,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廢棄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氣之中,最終造成環境污染的大爆發,環境污染公害事件層出不窮,成為西方國家重大社會問題。
西方國家在環境污染發生初期,采取過一些限制性措施,治理污染源,減少排污量,給工廠企業補助資金,建立凈化設施,征收排污費或者“誰污染,誰治理”,并頒布了一些環境保護法規。但是,僅這些被動措施未能阻止環境污染蔓延的勢頭。
污染公害事件對于經濟和人身健康的影響,使公眾從痛苦中覺醒。在學者們和廣大公眾的強烈要求下,在各國輿論的壓力下,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力圖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西方國家相繼成立環境保護專門機構,開始了對環境的認真治理,工作重點是制定經濟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長期政策。這樣,到80年代,西方國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較好地解決了國內的環境問題。
1992年,183個國家的首腦、各界人士和環境工作者聚集里約熱內盧,舉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正式否定了工業革命以來的那種“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這是人類環境價值觀由不科學到科學的轉變。
(《社會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