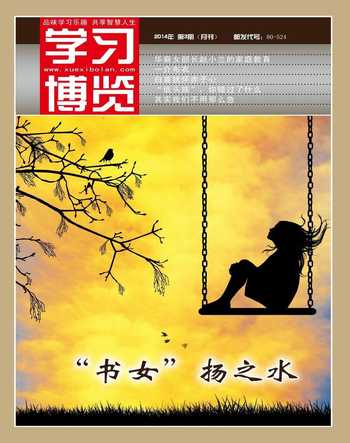《南下北上求學記》:一次現身說法的“中國教育調查”
萬佳歡
“我兒子厭學,我們沒有責任,責任在于社會、學校、老師。”
11月30日,作家春桃在自己新書《南下北上求學記》的讀者交流會上說。她情緒有些激動。
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合寫過著名報告文學作品《中國農民調查》《小崗村的故事》,相比于那些宏大的主題,他們的新書卻是整理自春桃的個人日記,主角是他們的兒子。
《南下北上求學記》講述了兒子小明在江西省萍鄉市(書中化名萍城)上小學期間,六年內三次擇校、三次搬家,最后逐漸在市重點學校里變得厭學的全過程,看似瑣碎而個人化,但仍然延續了陳桂棣和春桃關注現實、批判現實的路子,指涉當下種種教育問題和一個地級市的怪異教育生態。
從南下到北上
2005年,由于寫作《中國農民調查》得罪了一些本省官員,春桃不得不帶著5歲半的兒子從安徽合肥風塵仆仆地趕到江西萍鄉,準備讓他在這里上小學。
萍鄉是春桃的娘家。按照她的描述,這里的城市氣質與中國大多數地級市雷同:老百姓不看書不看報,打麻將成風;經濟不夠發達,但講究吃喝。作為一個曾發生過路礦工人大罷工、又策動過秋收起義的礦工城市,萍鄉人講義氣、重團結,講人情、重關系。“動不動就靠拳頭說話”,在春桃眼中,這樣的傳統以一個奇怪的方式延續到了今天。
兒子剛入學,就接二連三地被同學欺負。而為了跟老師搞好關系,春桃的妹妹請老師到家中吃飯。春桃在書里這樣描述兒子第一所小學的班主任,“打扮得很時髦”,“匆匆吃了飯,就和其他老師們一道退到里屋去打麻將了”。
不久,由于作業太多、負擔太重,春桃和丈夫陳桂棣把小明從東門小學轉入北門小學,又因不滿意后者的硬件和體育設施、更因為對重點學校的向往,春桃又托關系,把兒子轉入了重點學校南門小學。他們沒想到,兒子竟然在這所重點小學中產生了嚴重的厭學情緒。
一天,小明突然哭著對父母說,他要回北門小學,說班主任周小萍老師(化名)喜歡罵人,并當眾將小明的作業本摔在地上,罵他的作業格式錯誤,譏諷這是“天下第一格式”。剛轉學過來的小明并不清楚格式要求,嚇得不敢哭出聲。“這件事對兒子產生了極大刺激,”陳桂棣回憶。
后來,類似的事漸漸多了起來。“開始一兩年我一直忍氣吞聲。教師節我送給她奧運紀念車票,兒子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時又署上她是輔導老師,都沒用。”周老師笑嘻嘻地收下奧運紀念車票的兩個月后,因為小明跟同學在奔跑中相撞,她把他拉到走廊,連扇了五六巴掌。
春桃得知后十分憤怒,卻很快從別的家長處打聽到,“周老師的一個親戚是市里某部門的頭頭,后臺很硬”。
“我不可能永遠這樣忍氣吞聲。”春桃說。她嘗試聯合幾個家長,想換掉班主任。但家長們顧慮重重,計劃最終胎死腹中。“當時有個家長甚至說‘我的孩子太皮了,老師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放開手弄他。” 春桃回憶。陳桂棣又打電話找到一位副校長,卻被告知周老師是一位“優秀老師”。
小明與班主任的沖突愈演愈烈。春桃一次發現小明的課桌因為有廢紙而被班長強行搬走——周老師賦予了班干部們懲罰同學的權力。還有一次,因為小明跟同學發生沖突,周老師當著全班對那個同學說:“你不要理他(小明)就是,不要把他當人,就當他是畜牲。”
小明的成績開始下降,周老師把他的座位安排在了“差生”的靠墻位置。被貼上這一標簽后,小明的厭學情緒達到頂點,更開始與同樣的“差生”混在一起。
無奈之下,春桃夫婦只好為兒子另謀出路。他們花幾十萬在天津買房,為小明辦了個“藍印戶口”,又聯系了一所北京的民辦中學。2011年,他們帶著小學畢業的小明再次逃離,北上求學。
“我生孩子到底是為了什么?”
2011年小明到北京后,學習壓力驟減,春桃夫婦竟然又有些不適應了:這個學校也太松了點,作業怎么那么少?
他們為兒子挑選的是一所民辦學校,校長是臺灣人。教職工里天主教徒比較多,“絕不會出現老師打孩子的情況”。另外,每個班只有20人左右,兒子“好歹不會成為被放棄的對象”。
他們很快看到了兒子的變化。初一那年,小明在春桃的鼓勵下第一次報名參加了運動會的200米和1000米比賽——之前在江西讀書時,運動會都是由老師指定專人參加,小明從來沒有得到過機會。1000米跑到最后,小明被別人領先了足有一圈,但在全場的加油聲中,他堅持跑完。從那以后,他經常去健身房跑步。
除了運動會,小明還踴躍參加學校的辯論、表演及義賣活動,漸漸開朗起來。“以前他沒有個性、沒有自我,現在敢于嘗試很多東西,性格一下就變了。”陳桂棣說。
最讓春桃感到意外的是,這個學校讓家長成立了“家委會”,便于與校方溝通。小明一開始的班主任也不大理想,經家長反映,很快就換掉了。想起自己在江西為了換班主任費的九牛二虎之力,春桃感慨:“跟‘下面反差太大了!”
對于春桃和陳桂棣來說,做出“北上”的決定并不容易。用春桃的話形容,自己“經過了幾年的思想斗爭”。
對于“北上”,春桃夫婦有最大的擔心:沒有戶口,孩子無法參加中考和高考。他們雖然在天津買下了“藍印戶口”,但小明死活不愿意去——后來他們才發現,天津重點高中對藍印戶口學生的安置數量有限制,只有一成孩子才能通過考試入學。最奇怪的是,這個考試不考語文,只考數理化和英語,因為語文拉不大分數差距。
“要是以前我就逼著他去了。一個可以參加中考的地方,不去太浪費。”春桃說。但后來她慢慢想通了一個問題,“我生孩子到底是為了什么?最開始就是因為我特別喜歡孩子,并不是為了讓他光宗耀祖。”
兒子上小學后,她開始不自覺地“被應試教育牽著鼻子走”,“我現在要回到他上小學之前我對他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把學習的興趣找回來,以后能自食其力,做一個善良、感恩的人。”她說。
幾個月前,當春桃提筆開始寫作《南下北上求學記》頭幾章時,小明跟在后面看,邊看邊哭。在萍城的六年讓春桃夫婦學會了一件事:不要替孩子做決定,凡事尊重他的選擇。
小明喜歡畫畫、并且畫得不錯,宣稱“對應試教育已經絕望”的春桃夫婦決定依他的意思,放棄中考。明年,小明初中畢業后將直接報考美術學校。
(摘編自《中國新聞周刊》,有較大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