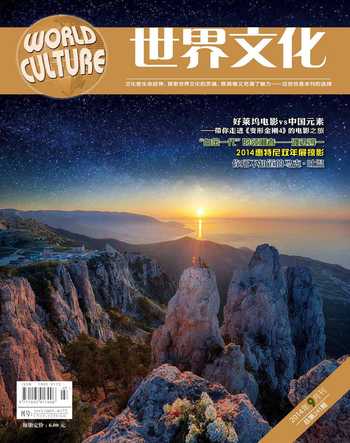格雷厄姆?格林后期政治小說解讀
夏宗霞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的創(chuàng)作生涯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一直延續(xù)到風云變幻的戰(zhàn)后歲月。在20世紀小說界各種“主義”與試驗形式層出不窮的背景下,格林始終將懸念和驚險作為情節(jié)的助推器,將人性和道德沖突作為故事背后的敘事動力。就故事性和道德關(guān)懷而言,他的小說更接近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就類型而言,他的許多小說可以劃為間諜小說、犯罪小說或驚險小說;就題材而言,格林既使用以天主教信仰為主的宗教題材,也關(guān)注冷戰(zhàn)時代的國際政治問題;就其題材范圍而言,他的小說覆蓋越南戰(zhàn)爭、海地獨裁、南非種族隔離、拉美的貧困和壓迫、共產(chǎn)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等。作為小說家,他的小說既可以作為通俗讀物以吸引最廣大的普通讀者,也可以作為嚴肅小說而進入文學批評家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視野。
對格林的最初印象是“天主教作家”,因為他創(chuàng)作了“宗教四部曲”,特別是《權(quán)力與榮耀》和《問題的核心》已成為現(xiàn)代小說史的經(jīng)典;但簡單地運用這個標簽會掩蓋格林豐富而復(fù)雜的創(chuàng)作特色。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在《現(xiàn)代英國小說》一書中指出:“批評家和英國傳統(tǒng)認為格林是當代英國作家中最難對付的,因為他的作品從不是單一的特點或形式。”還有的評論家認為格林是評論家的絕望,因為格林的評論實在是太多了。他的作品分為三類:天主教、間諜和政治小說。從50年代中期開始,格林的創(chuàng)作興趣轉(zhuǎn)向國際政治題材:對宗教的興趣減弱,政治成為主題。
格林認為:“和天主教作家相比,我更是一個政治作家,但我更愿意被稱作碰巧是天主教徒的小說家。”“我害怕被標簽為政治作家,就像我害怕成為天主教作家那樣,因為我不認為我的寫作方式或我對寫作的態(tài)度由事件決定,事件只偶爾影響對主題的選擇。我認為當我處理政治主題時, 我被稱作政治作家; 但政治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像上帝的隱現(xiàn)一樣。”
按照格林的觀點,世界的沖突是由共產(chǎn)黨和天主教構(gòu)成的,所以格林的一生是共產(chǎn)主義和天主教互相糾纏的一生。他早期迷戀共產(chǎn)主義,曾加入共產(chǎn)黨6周;之所以入黨,也就是因為那種有朝一日掌權(quán)的不著邊際的想法,另外入了黨也許可免費去一次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早期成名作《斯坦布爾列車》中,刻畫了一位受理想主義壓迫的“左派”人士;《這是戰(zhàn)場》是格林的第一部政治小說。中期創(chuàng)作以宗教小說為主,探討罪與救贖等問題,1938年的《布萊頓硬糖》是格林的第一部宗教小說。后期又回歸政治主題,一般認為,格林轉(zhuǎn)向后期政治小說的創(chuàng)作以格林在越南的經(jīng)歷為界,《沉靜的美國人》被公認為格林作品中最好的政治小說。
格林后期政治小說是指1955年以后出版的,以冷戰(zhàn)和第三世界革命為主題的小說。“二戰(zhàn)”的槍聲還沒寂靜,冷戰(zhàn)就開始了。冷戰(zhàn)是相對于二戰(zhàn)那樣的“熱戰(zhàn)”而言,是對戰(zhàn)后美蘇為首的兩級對立與對抗的態(tài)勢的形容和概括。到50年代早期,冷戰(zhàn)中的對抗已極其緊張。冷戰(zhàn)主要的事件包括:杜魯門主義(1947)、柏林封鎖(1948—1949)、東德成為獨立的國家(1949)、蘇聯(lián)實驗原子彈(1949)、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1950)、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1956)、美國參與越南戰(zhàn)爭(1955)。這段黑暗的歷史時期反映在格林的小說里。格林小說的背景都放在英國以外的國家,如《沉靜的美國人》《哈瓦那特派員》《喜劇演員》《名譽領(lǐng)事》的故事分別發(fā)生在越南、古巴、海地、巴拉圭和阿根廷邊界小城。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及為什么把小說的背景放置在英國本土以外的這些國家,格林的回答是:這些國家的政治不是政黨的更替,而是事關(guān)生死的事情。
一、《沉靜的美國人》:冷戰(zhàn)時期的越南
從1951年到1955年,格林在越南度過了四個冬天,正是胡志明領(lǐng)導(dǎo)越南人民抵抗法國入侵的時候。這段經(jīng)歷的結(jié)果是《沉靜的美國人》的出版。小說出版后,引起政治爭論。在美國,對該小說的接受是非常負面的,因為對派爾的刻畫折射出格林的反美情緒。該小說也預(yù)言了美國插手越南的災(zāi)難性后果。
《沉靜的美國人》的小說背景是50年代越南人驅(qū)逐法國殖民主義者的戰(zhàn)爭。小說的題目是誤導(dǎo)的:主人公不是沉靜的美國人派爾,而是福勒。福勒以一名英國記者的身份來觀察派爾的一言一行。他一向尊奉的生活信條是“不干涉他人”“不牽涉其中”。作為記者,他關(guān)心的只是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實,而不是去干預(yù)事情發(fā)生的過程。他在越南采訪時,遇見了美國對越經(jīng)濟援助使團的派爾。兩人態(tài)度常常是對立的。福勒人到中年,久經(jīng)世故,在某種意義上是格林的化身。派爾年紀32歲,從哈佛大學畢業(yè),表面上很天真,滿腦子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人很熱情,但是他的思想往往帶有危險性。他外表上是個“沉靜的美國人”,在越南宣傳民主、自由,但實際上在經(jīng)濟援助的幌子下干著罪惡的秘密活動。他組成一支“第三勢力”,既排擠法國殖民勢力,又反對越南人民的解放斗爭。這個“第三勢力”多次制造爆炸事件,使許多無辜的越南人喪失性命。派爾的罪惡活動終于使福勒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使他終于認識到事情“并非與己無關(guān)”。于是他同意了越南進步組織地下工作者的要求,配合他們行動,借邀請派爾吃飯的機會將他除掉。福勒心中又為此感到不安,希望能找到一個人說一聲對不起。格林生動地描繪了“天真”要付出的可怕代價,而美國式的天真背后隱藏著無意識的傲慢和自以為是。
這是小說的主線,還有一條副線是福勒、鳳和派爾的三角關(guān)系,他們?nèi)擞滞瑫r代表舊殖民主義的歐洲、風雨飄搖的越南人民和新殖民主義勢力。鳳是福勒在西貢苦苦追尋才到手的情人,鳳每晚為他鋪床和點燃鴉片。但這一切隨著派爾的到來而被打破,派爾從福勒的手中奪走了鳳,因為他更年輕,并許諾:娶鳳為妻并帶鳳到美國。這三個人的掙扎和糾結(jié)是外在斗爭的投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福勒殺死派爾,是為了殺死他的情敵。
格林完全反對美國插手越南的事情。越南沖突的解決只能是美國軍隊完全、無條件的撤離,外國軍隊的出現(xiàn)阻止了北越和南越的談判。
二、《哈瓦那特派員》:哈瓦那的情報戰(zhàn)
格林的小說是其時代的產(chǎn)物,反映了核武器的威脅。《哈瓦那特派員》的故事背景轉(zhuǎn)到了革命以前的古巴,小說描寫在巴蒂斯塔獨裁統(tǒng)治下的間諜活動。英國商人詹姆斯在古巴推銷吸塵器,他的妻子同別人私奔了,他獨自將女兒撫養(yǎng)成人。為了滿足女兒的奢侈要求,他身負重債,一籌莫展,最后因優(yōu)厚報酬的吸引而充當了英國政府的間諜。但是他不會搞間諜活動,于是他就捏造假情報,謊稱自己發(fā)展了若干名間諜,其實這些人的名字都是他從電話簿里抄錄下來的。這些無辜的人莫名其妙地受到了英國間諜網(wǎng)和古巴警方的監(jiān)視,而詹姆斯本人也受到了警方的調(diào)查。間諜組織發(fā)現(xiàn)了他的詭計,打算處決他。他僥幸逃脫了,但是他的一位朋友卻被誤殺。詹姆斯自己也殺死了一名間諜。事情越鬧越大,他為自己的欺騙行為造成的惡果感到驚恐,于是只好回到倫敦去坦白請罪。
選擇哈瓦那對于格林而言并非偶然:作為一位左翼傾向的作家,他一直關(guān)注拉丁美洲的現(xiàn)實。1950—1960年間,格林曾走訪海地、古巴、巴拉圭、巴拿馬等地,并以拉美為背景創(chuàng)作小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多方面接入拉美的政治承諾”。在他晚年創(chuàng)作的更為激進的文章中,對相繼出現(xiàn)于拉美的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權(quán),他表示了絕對的贊同,且呼吁一種“具有人性面貌的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在多次旅行過程中,他與古巴領(lǐng)導(dǎo)人卡斯特羅、巴拿馬領(lǐng)袖托里霍斯等都建立了私交。
《哈瓦那特派員》并不是真的描寫哈瓦那,而是格林以哈瓦那為背景嘲弄間諜服務(wù):之所以選擇哈瓦那作為背景是因為格林在卡斯特羅執(zhí)政前后曾多次拜訪過古巴那個國家,對那個國家較熟悉。
三、《喜劇演員》:“醫(yī)生爸爸”獨裁統(tǒng)治下的海地
《喜劇演員》的故事發(fā)生在海地。格林曾經(jīng)三次去過海地,前兩次是1954年和1956年,那是在獨裁總統(tǒng)杜瓦利埃統(tǒng)治海地之前。1957年杜瓦利埃上臺后,在海地實行巫術(shù)和血腥高壓相結(jié)合的政策,建立死人衛(wèi)隊,鎮(zhèn)壓異己,以殺人為樂,臭名昭著。杜瓦利埃在海地的血腥統(tǒng)治延續(xù)了14年,一直到他的死亡。格林決定鋌而走險,1963年8月,他第三次來到海地。海地已經(jīng)與記憶中的完全不同,充滿饑荒,反對總統(tǒng)的人不但要被處以死刑,還不許收尸。格林后來依據(jù)他三次海地之行的經(jīng)驗寫出《喜劇演員》,對杜瓦利埃的獨裁統(tǒng)治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故事敘述者布朗是一家旅館的老板,這家旅館是他母親留給他的,他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在來海地繼承這家旅館之前,為了謀生,他曾干過各種各樣的低級職業(yè),生活的經(jīng)歷使他變成了失去理想的人。海地總統(tǒng)的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使經(jīng)濟一敗涂地,布朗的生意也經(jīng)濟蕭條。他與一位有夫之婦之間產(chǎn)生了一段荒唐的風流韻事, 然后他想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朋友瓊斯少校和史密斯先生卻在英勇地投身于反抗暴政的政治運動,瓊斯少校還為此獻出了生命。布朗認為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像是在演戲,他對此漠不關(guān)心,抱著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但是到了最后,他在一個天主教牧師和一個信仰共產(chǎn)主義醫(yī)生的共同勸導(dǎo)下,幡然醒悟,但為時太晚。這部作品也描寫了不同的人類群體之間的政治差異。主人公從有神論者轉(zhuǎn)變?yōu)樘摕o主義者,作品的主題是:如果人想避免絕望,他就需要相信某種價值觀。
四、《名譽領(lǐng)事》
《名譽領(lǐng)事》是格林個人最鐘愛也是最受評論家好評的一部作品。小說描寫的是發(fā)生在巴拉圭和阿根廷邊界小城查科的一起綁架人質(zhì)事件。一個激進的革命小組在被解除神職的神父利瓦斯的領(lǐng)導(dǎo)下,計劃劫持美國駐阿根廷大使,希望以他為籌碼要求當局釋放十名政治犯。事后他們才發(fā)現(xiàn)抓錯了人,抓來的是英國駐查科城的名譽領(lǐng)事福特那姆——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醫(yī)生愛德華多·普拉爾卷入了綁架案,他與福特那姆的妻子私通,出于人道主義和對福特那姆的負罪心理,他不愿綁架者殺死人質(zhì)。利瓦斯神父也陷于人道與殺戮的矛盾中。在他們的遲疑等待中,他們的藏身之地被警察團團圍住,福特那姆生還,而利瓦斯神父和普拉爾醫(yī)生被打死。
20世紀的南美洲是一個濃縮了骯臟政治、血腥鎮(zhèn)壓和普遍貧困的大舞臺,格林用它為背景戲劇性地揭示了人在殘酷、黑暗的政治斗爭中的困境。普拉爾醫(yī)生不贊成恐怖手段,力阻殺死福特那姆,希望英國政府會為了人的生命而對綁架者讓步。但當局根本不把福特那姆的生命當回事,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消滅綁架者。最后,當普拉爾醫(yī)生走出綁架者的小屋想跟與他熟識的警長說個情時,無情的子彈將他擊斃。普拉爾醫(yī)生的死昭示了黑暗現(xiàn)實對人性的摧殘和對人權(quán)的踐踏。
小說家把綁架這樣一個政治性事件作為故事的主要內(nèi)容,描寫第三世界國家中錯綜復(fù)雜的政治斗爭。他認為,政治在社會生活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地位,伴隨政治斗爭的往往是暴力、恐怖和殘忍,而人性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變形扭曲。無論是綁架者的頭目,還是警長和英國政府的官員們,他們都是按照政治的邏輯處理問題,或是為了國家,或是為了革命,個人在強大的、無情而荒謬的政治邏輯面前沉浮飄搖。
格林的宗教小說深受他信仰的天主教的影響;同樣,他的政治小說留下了東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和重大國際政治事件的影子。雖然格林反對美國插手越南民族解放運動,反對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控制,同情第三世界和弱小群體,但作為西方自由知識分子,格林是帶著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來觀察問題的。如把越南共產(chǎn)主義稱為“紅色的威脅”;他有抵制美國霸權(quán)的態(tài)度和言行,也許是因為美國取代了英國的日不落帝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