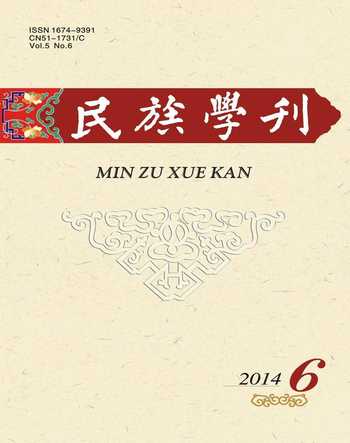李紹明“武陵民族區”概念內涵與“黔中文化研究”基礎理論
[摘要]李紹明先生對“武陵民族區”的闡釋,界定了一個內涵清楚的民族學概念,是對費孝通先生“板塊與走廊”學說學科特征辨識后,做出的新的學術闡釋,是對民族走廊學說的豐富,不是回到區域民族學“封閉”研究的傳統思路,而是觀照于武陵民族區“這一個”民族區域發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學理論。《彭水縣志》的相關閱讀,即能意識到武陵民族區“不被‘整合的向心力”的事實存在。
[關鍵詞]李紹明;武陵民族區概念;內涵理解;黔中文化研究基礎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9391(2014)06-0063-09
基金項目:重慶市2013年度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慶武陵山片區民族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13YBMK145)階段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趙心憲,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史、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學。重慶,400010
一、《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誤讀問題
《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1],是我國當代著名民族學家李紹明先生,生前于2007年在《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發表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民族學論文。主要涉及兩個核心學術概念:1、“武陵民族區”,2、“民族走廊”。細讀全文,論證的主要篇幅均圍繞“武陵民族區”民族學概念內涵界定展開,分列四部分標題綱要式闡述。
1、“武陵山及武陵民族區概說”:從地理學武陵山概念的內涵界定,延伸到民族學武陵民族區概念的內涵說明。
2、“武陵民族區的族群互動與文化多樣”:論說武陵地區土家族、苗族等族群分布格局,土家族、苗族、侗族的“民族互動”歷史線索,清初改土歸流后所受漢文化程度不同的影響,及其各具特色的多樣文化,三族的“民族共同性與地域相異性”。
3、“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問題”:認為費孝通先生民族走廊學說沒有論及“武陵民族區”,多次提及“武陵地區”,但從“未明確指出其究竟是板塊或走廊”,“武陵民族走廊”是否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學概念成為問題,因此“武陵民族區屬于板塊或走廊”是“武陵民族區”應該專門探討的民族學基本理論問題。從李星星、王元林等學者有爭議的研究結論看,可見“武陵民族區從民族學、人類學角度而言,是個富礦。雖然我們的研究已經有了一些成績,但對其深入認識遠遠不夠,有待繼續努力。”
4、“武陵民族區研究的展望”:首先提出“武陵民族區的綜合研究”命題,認為“武陵民族區若從費老板塊與走廊學說而論,它系一個板塊,而非走廊。因為它并不具備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從而具有相對穩定性。當然,并不是說這個板塊之中沒有通途,因為從古到今,板塊與走廊均與外地交通相連的。”武陵民族區“完全符合民族學蘇維埃學派所主張的‘歷史民族區或‘經濟文化類型的概念……從歷史到現狀,從經濟到政治,從社會到人文,縱橫交錯地進行全面綜合研究。”其次,提出“武陵民族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學術目標。認為武陵民族區的研究,可以從多學科多視角出發。基礎研究涉及學科的根本,也涉及人們對這一區域科學的認識,“一切均應從此入手”;同時,重視民族學、人類學的應用部分,武陵民族區“民族文化傳承和調適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從提出武陵民族區概念,武陵民族區概念內涵的主要民族學內涵解說,到武陵民族區概念作為民族學基本理論問題重要性的簡明闡釋,最后提出“武陵民族區研究的展望”共四個層次。全文觀點鮮明,思路清晰,立論有據,見解獨到,應該是不會讓讀者產生歧義的。簡言之,論文的理論建構目標不是“武陵民族走廊”,而是“武陵民族區”民族學概念。可以認為,作為一位當代中外知名的民族學家,李紹明先生在這篇西南民族學研究總結式的學術論文中,立足于自己扎實的,中國西南、武陵地區民族學研究五十余年的經驗理性認識基礎上,全力維護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板塊與走廊”理論權威性的同時,以“武陵民族區”概念的論證、提出,豐富而不是否定了費先生的民族走廊學說。但近年有關民族走廊理論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對《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一文基本內容的誤讀,不能不引起學界的注意。
《論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三個問題》(2011年)[2]第一部分“關于民族走廊概念的界定”,在明確指出,費孝通先生“初步描繪出了中國民族走廊的大體格局,但未就民族走廊的概念進行專門論述”后,引用李紹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首次對民族走廊的界定:“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或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這條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的沉淀。”(1994年)然后說,“據李先生的理解,判斷民族走廊的前提主要是‘走廊式的自然地理。因此,他分析武陵民族區的屬性時認為,其屬于‘一個板塊而非走廊的依據是,‘它并不具備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從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言下之意甚為明顯,即武陵山區的地形地貌并不具有‘走廊狀的地理特征,故其不屬于民族走廊大家庭的一員。”《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是2007年發表的,由提出武陵民族區概念,涉及到武陵山區是否存在民族走廊問題,不是像提出武陵民族區概念那樣,理論建構民族走廊觀念,因為論文理論針對性明確,隨便引申李紹明先生關于民族走廊判斷的理論普適性,顯然屬于《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一文的誤讀。李紹明先生的觀念是很清楚的,是否成為民族走廊,板塊與走廊的特征哪一方面更突出,就是依據。武陵山區“民族板塊”的特征明顯比“民族走廊”的特征更明顯,“武陵民族走廊”的界說就應三思而行。不然,就會自相矛盾。在指出李紹明先生民族走廊界定的“過于嚴格”,事實上的否定之后,該文第一部分最后的表述出現這樣的論斷:“民族走廊研究就一定程度而言,是一種區域研究,但也有其獨特性,即它是某一或某些族群或民族長期在走廊式的自然地理環境中遷徙、活動所形成的民族地區。如果在其概念甚至研究中弱化、忽略其地理學的意義,民族走廊研究必將失其獨特性,由此淹沒在區域研究的汪洋大海中。”[2]這與李紹明先生的武陵民族區論說意旨何其近似!也就是說,該文否定李紹明先生對武陵民族走廊的質疑之后,又基本認同李先生的“武陵民族區”,作為“民族地區”民族學研究的概念了。
《李紹明先生與武陵民族走廊研究》(2012年)[3]開篇就從誤讀開始:“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提出‘民族走廊理論以來,李紹明就敏銳地觀察到我國武陵地區多民族互動與文化多樣性,多次親自深入武陵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試圖從學理上建構并完善民族走廊理論”。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以“板塊與走廊”學說為基本內容,而不是放棄“板塊”的“走廊”研究,“板塊與走廊”觀念的整體構建,內中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李紹明先生武陵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的終極理論目標,也不是“學理上建構并完善民族走廊理論”,而是完善民族走廊相關理論的武陵民族區學說。該文第一部分“‘民族走廊與‘武陵民族走廊”,撇開武陵民族區學說,圍繞李紹明先生如何“對‘民族走廊和‘武陵民族走廊理論,進行進一步的理論闡釋和學術建構”的誤讀展開,當然會順理成章地認為,支持“2006年黃柏權‘武陵民族走廊研究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說明李先生對武陵民族走廊這個學術話語和學術概念的事實上的思考、認可和接受。”[3]這顯然背離了基本事實。因為2007年《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文中,李紹明先生才正式提出武陵民族區的民族學概念。這樣,該文的第二部分,有關“李紹明先生對武陵民族走廊的理論建構和學術實踐”的論證,整個立論的基礎因為誤讀被“空心化”了,成為進一步的誤讀。因為這部分援引的主要理論資料,就是《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一文的基本論說。該文第三部分,“李紹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是為論文的結論。全文從問題的提出就存在誤讀,第二部分的分析問題與第三部分解決問題的結論,當然也只能屬于誤讀。
《論民族走廊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2013年)[4],探討民族走廊研究中的基本理論問題。從走廊的本義開始,回顧費孝通先生將“走廊一詞運用到民族研究領域”的過程,特別列出“六板塊三走廊”中國民族格局理論提出之后,費老對民族走廊說法的三次修正:1、1985年8月將西北走廊修正為隴西走廊;2、1991年10月考察武陵地區后,增加了武陵地區“這條多民族接觸交流的走廊”;3、2003年10月對中國民族走廊總數的“3條”,修正為“幾個”的約數,“中國存在幾個這樣的民族走廊”。作者認為:“按費先生最后的修正,他最終提出了四條民族學意義上的民族走廊,即‘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隴西走廊和‘武陵走廊。”而費先生對民族走廊內涵的理論概括,主要論點有4個:“不同民族接觸的地帶”,“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區”,“民族情況復雜的地區”,“在歷史上出現過政治上拉鋸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忽略了費先生對民族走廊內涵理論概括的地域性前提,即這四條民族走廊各自能夠存在的自然地理條件的獨特性。因為這個疏忽,文中對李紹明先生的民族學概念就直接批評了:“李紹明把民族走廊說成‘民族遷徙與流動的線路,明顯偏離了費先生原來的意思。但納入民族學理論,為后面的民族走廊學說建構作了鋪墊。”[4]發表于2007年的《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并沒有界定民族走廊概念,而是應用費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板塊與走廊”學說,對武陵民族區界定所展開的綱要式論證。何來“明顯偏離了費先生原來的意思”?如果不是沒有讀過李紹明先生的這篇重要論文,就是對這篇論著的誤讀!
二、“武陵民族區”的學術影響、理論依據及其相關地域概念問題
李紹明先生涉及民族走廊的界說曾引起眾多誤讀的回應,但他提出的關于武陵民族區的民族學闡釋,迄今為止,沒有檢索到一篇商榷的文章,反而是不少研究者因此開拓了思路,推出系列的民族學理論成果。
首先是李星星對李紹明先生民族走廊界定的拓展。在對民族走廊地理特征要求的相對模糊認識下,李星星“更強調地形地貌的總體走向,以及文明中心的政治經略與開發在民族走廊形成中的作用”(曹大明三個問題),將費老所說的“三大走廊”外增加兩條,即“土家-苗瑤走廊”和“古氐羌走廊”。“土家-苗瑤走廊”的民族學描述,與李紹明先生的“武陵民族區”論說接近。而且,還找出武陵走廊的五條通道:1、從長江巫山峽區南入武陵;2、從長江入清江入武陵;3、從長江溯烏江入武陵;4、從洞庭湖溯沅江入武陵;5、從洞庭湖于沅江東側入武陵。當然,進入武陵后,還可以繼續南下、東進與西遷[5]。
其次是對古苗疆走廊的研究。“苗”是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統稱,“苗疆”相當于今天所說的民族地區。“古代苗疆”是清代以后涵蓋貴州及周邊地區的地緣概念。“古苗疆走廊,是從以漢代文化為中心的兩湖平原地區,跨越到非漢族族群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湘黔滇高原地區的跨地形帶的走廊,兼有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等多種地貌。”[6]與上述其他民族走廊比較,古苗疆走廊不是依據山川地勢等地理條件自然形成的,而是主要在國家意識的“操控下”,元明清時期以后開辟的,“在地理位置上連接了西南邊陲云南和湖廣兩地的一條驛道(湖南常德為起點,終點抵達昆明——引者),當然也包括其周邊呈帶狀分布的地域。”其地貌的多樣性、民族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對周邊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極為重大,其多樣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的歷史文化遺存”非常厚重。值得注意的是,武陵民族區就是古苗疆走廊的周邊之一[6]。
關于武陵山區“民族區域性”的認識,應該是在武陵民族區概念影響下,近年出現的重要民族學成果。《武陵山區:內地的邊緣》[7]一文,在筆者看來,就是李紹明先生武陵民族區“綜合研究”預設的代表性理論表述。武陵山區作為“連接內地與西南的民族走廊”,“地處江漢平原農業文明與云貴高原山地的復合經濟區的過渡地帶”,“保存著深厚的民族歷史文化底蘊。從200多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到夏商周時期,這里都留有人類文明的遺跡,保持著很強的歷史連續性。”從漢唐時期“武陵蠻”稱呼的出現;宋元明土司制度的推行,到明清“改土歸流”后,大批的漢族移民進入,武陵山區原有族群出現較大流動;特別是“趕苗拓業”迫使苗族原住民的區內遷徙,武陵山區作為“傳統中國內地的‘化外之區”特征明顯。似乎成為著名史學家許倬云所說的中華帝國的“隙地”:“中國地方遼闊,即使有干道交通網絡,聯系各處地方,干道之外,又有分支道路分布,猶如人體的血管與神經網絡,聯絡中國為一體。但是,分支道路之間,總有遠鄉離村,形成網絡中的空隙,訊息物質都難出入。這些隙地如邊陲地區,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數民族,他們雖已為‘中國族群的行政單位納入中國版圖,卻仍是文化的‘他者,也是一國的‘內在普羅”[7]。
應該說,這種“隙地”內生的文化穩定性及其相關的史實與規律,是值得認真深入研究的,因為歷史上武陵民族區出現的這種“隙地”不少(后文將重點引述《彭水縣志》略作說明,此處姑且不再展開)。《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已經清楚地指出過相關問題:
其一,“武陵民族區自古迄今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同時它也處在祖國內地腹心地區,深受漢文化影響,故較之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較快。但因它系山區,山地深丘與淺丘縱橫,谷地平壩甚少,交通相對不便,較之內地許多地區封閉性較強,其發展程度又不能與內地一般漢區相比。”[1]其相對穩定性是民族學關注的課題。
其二,“武陵民族區以武陵山脈為主,幾乎覆蓋全區,山間又有沅、清、烏三江縱橫穿過。土家、苗、侗為主的各民族先民世居于此,互通有無,無論歷史上有何矛盾,但其主流是彼此能在此相處,構建一個共同的家園。自漢迄宋,武陵民族區有統一的行政管理,加速了區內的整合。自宋迄今,武陵民族區分屬不同的行政管轄,但由于歷史積淀,地理相通,民族相同,其經濟、文化乃至政治聯系從未中斷”[1]。
可見,李紹明先生武陵民族區的理論前瞻性是事實存在的,不能因為涉及武陵民族走廊問題,武陵民族區這個重要的民族學原創概念,就草率地被視為不周延的理論話語。筆者以為,造成這類誤讀的眾多原因之一,是我們對支撐李紹明先生武陵民族區理論構建的文化哲學依據可能不甚了了。
《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第四部分,展望武陵民族區“綜合研究”的學術建設,認為“完全符合民族學蘇維埃學派所主張的‘歷史民族區或‘經濟文化類型的概念”,或者可以這樣認為,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就是武陵民族區民族學研究的主要理論依據。首屆全國民族文化論壇(2004年9月23日),蔣立松先生《研究西南地區民族文化的兩個重要理論評述》可以基本了解這個理論的發展演變軌跡。
“歷史民族區/經濟文化類型”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初前蘇聯民族學家托爾斯托夫等提出的,核心內涵即“一定的經濟與文化特點的綜合體,它在歷史上形成于處在相似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并居住在同樣自然地理條件下的不同民族中。”[8]
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個理論得到發展,經濟文化類型被重新定義為:“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9](P86)。1997年,宋蜀華先生在此基礎上,提出“中華民族生態文化區”的概念[10](P412-425),將中國劃分出多民族的八大生態文化區(其中第四類“湘、桂、滇、黔山區的耕獵文化區,發展為苗、瑤、畬等族文化”,與武陵民族區的生態文化類型相似——引者)。中華民族生態文化區理論應用于西南民族地區研究,以下四個論斷是應該認真領會的。
其一,由于中國西南地區“經濟文化類型的多樣性”,各民族所操持的生計方式多元化,從而使得這個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具備了客觀基礎”。
其二,不同民族或族群的經濟文化類型不同,生計方式也不相同,由此而使其經濟文化類型和生計方式具有了“民族的特征”。中國西南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民族格局及其居住形式的“大雜居,小聚居”特點,民族交往雖然“容易實現”,但這種交往的空間范圍往往因此“比較狹小”。
其三,生態文化區的經濟文化類型和生計方式選擇,是動態的調節過程,而不是恒久不變的模式認定。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向“定居農耕過渡和發展”的脈絡很清晰,“定居農耕”構成了整個中國西南地區向工業文明過渡“最重要的基礎”。定居農耕的“趨同式”發展,在西南地區民族關系中的影響“十分明顯”,即“在歷史上構成了西南地區民族關系演變中的一條基本線索”:明清以后各民族對漢文化的認同,即對于定居農耕文化的認同;在定居農耕基礎上,“客觀形成”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層次結構”——先進與落后的分野。農耕技術比較先進的民族,在民族關系構建中,往往居于主動地位。
其四,地理環境特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南地區各民族與中原和其他地區的廣泛交往與聯系。“如今西南各民族大體‘聚族而居的歷史格局并沒有多少改變,雖然在更廣闊的空間上看,仍然是‘大雜居,小聚居的一部分。”[10]這個由自然地理條件和國家歷史進程合成的西南民族地區特點,武陵民族區最具有民族學理論解剖的個案典型意義。武陵、武陵山、武陵山區三個地域概念的內涵辨析,就是避免誤讀李紹明先生武陵民族區概念,最基礎性的常識了解。
《辭海》“武陵”辭條共下面三個義項:(1)山名。貴州苗嶺的一支,分布于貴州、湖南、湖北三省邊界地區,為武陵山脈。其湖南邊界部分,迤于澧沅二水之間,至常德西而止。故常德西的平山亦稱武陵山,又稱武山。參閱《嘉慶一統志》三六四《常德府》。(2)郡名。秦昭襄王三十年取楚巫黔及江南地,置黔中郡。漢高祖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隋廢,改朗州。宋建隆間稱朗州武陵郡,大中祥符中改為鼎州。乾道元年升為常德府。元為常德路。明清復為常德府。自東漢起,郡治武陵。在今常德市。參閱《嘉慶一統志》三六四《常德府》。(3)縣名。屬湖南省。漢臨沅縣。隋平陳改為武陵。明清為常德府治。公元1913年改為常德縣。參閱《寰宇通志》五七《常德府》。[11](P1617)
從自然地理的空間位置到人文地理的地名歷史沿革,《辭海》“武陵”辭條把武陵山、武陵郡、武陵縣三個有關武陵的地域概念辨析得既清楚又明白。但我們應該很清醒,這還不是民族學視域的武陵概念內涵。李紹明先生《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第一部分,“武陵山及武陵民族區概說”,就是從民族學的“武陵”應有的內涵闡釋開始的:
武陵山是一地理學名詞,指我國南部一座山脈,其來源與漢代于此置武陵郡有關。起始于貴州苗嶺山脈,武陵為其支脈。發源于梵凈山(主峰2494米),盤亙于渝湘之烏沅二江之間,入湘蔓延于澧水之南,止于常德縣西境,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為烏江、沅江、澧水之分水嶺,呈東北——西南走向。武陵山區一帶的民族,在漢代統稱為武陵蠻。主要指今鄂西恩施州及湘西州一帶的先民。東漢至宋在沅水上游五溪地區的又稱為五溪蠻。武陵郡始置于漢代高帝時,治義陵(今湖南溆浦南),轄境相當于今湖北長陽、五峰、鶴峰、來鳳等縣。湖南沅水流域以西,貴州東部及廣西三江、龍勝等地,東漢時移治臨沅(今常德西),其后轄境縮小。唐即改朗州,又復置武陵郡,宋置朗州,武陵郡尋廢。總之,歷史上的武陵郡這片區域,即今恩施州南部、宜昌市南部、常德市南部、張家界市、湘西州大部、懷化市大部、銅仁地區東北部,原黔江地區東部這一大片區域。[1]
因為從自覺的民族學視域審視,所以,在上述引文辨析有關“武陵山”、“武陵山區”、“武陵蠻”、“武陵郡”之“武陵”含義之后,李紹明先生下這樣的判斷:“武陵應先有郡名,然后有山名。現今上述地區的少數民族為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等等。當然,漢族仍然是此區人口眾多的民族。”[1]武陵山實因武陵蠻土著得名,說明李紹明先生覺得這個地名文化的人文文脈很有些古老,不容漠視,因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置郡,邏輯關系是世居族群在前,行政區劃在后。有意思的是,2009年《簡論古代武陵的地理范圍》一文的有關考證,說明了這一點:“武陵地區的范圍,一般認為起湘鄂渝黔邊的武陵山區,而實際上長江以北的巫山山脈,漢中地區也在武陵地區的范圍內。這一地區不僅歷史地名有淵源關系,而且在空間上具有整體性,更重要的是,這地區文化具有同一性,同屬巫文化圈子。武陵地區應包括大巫山山脈和武陵山脈及其周邊地區。”[12]
武陵山的古老,根源在于武陵山區世居民族、族群文化的古老。柴煥波先生在十年武陵山區考古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認為武陵民族區有其“獨立的發展邏輯”:“以平原、大河流域為中心的原始農業文明,從很早時候起就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這是華夏文明的基礎。武陵山區崇山峻嶺,地老天荒,東漢馬援稱之為‘鳥不飛度,獸不敢臨;唐代李吉甫謂‘溪山阻隔,非人跡所履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土著政權擁兵割據。文化上,武陵山處于洞庭湖區與四川盆地兩個文化中心之間的邊緣地帶,這種文化上的邊緣地位,從上古一直持續到今天。它的歷史發展,有自己獨立的發展邏輯。”[13](P4)在筆者看來,李紹明先生的武陵民族區概念,正是從民族學理論的構建上,表達了對武陵山區世居民族、族群古老文化的尊重、武陵山區獨特的“歷史發展邏輯”的敬畏,及其地域文化傳承的當代意旨。
行文至此,我們或者應該這樣認為:李紹明先生闡釋的“武陵民族區”,是一個內涵清楚的民族學概念,是對費孝通先生“板塊與走廊”學說辨識后,新的學術闡釋,是對民族走廊概念的豐富,不是回到區域民族學“封閉”研究的傳統思路,而是觀照于武陵民族區“這一個”民族區域發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學理論。武陵民族區概念內涵的界定似強調了以下三個要點:
1弱化“走廊”的理論預設干擾,突出民族融合地域文化特征生成過程特殊性的研究,與長期民族識別田野調查豐富的經驗理性認識對應。說明區域民族學個案研究需要宏觀、整體、全局的理論引導,但理論預設不可取代特殊現實的具體存在,切忌先入之見的理論盲視。
2作為民族文化區域的武陵山區(武陵民族區),地域文化特征的“板塊式”生成,在中華文化傳統形成過程中具有獨特價值,包括漢文化在內的各民族文化在武陵山區的文化融合,其求同存異、互動發展的規律性特征值得珍視。
3武陵民族區經濟文化發展規律的民族學認識,需要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支撐,但不是照搬。由自然地理條件和國家歷史進程合成的西南民族地區特點,武陵民族區最具有民族學理論解剖的個案意義。在筆者看來,其中對于渝東南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利用,特別具有國家戰略實踐的重大意義。
三、武陵民族區概念引導下1998年版《彭水縣志》的細讀舉例
武陵民族區黔中文化的源頭,在重慶市渝東南六區縣之一的彭水[14],1998年版《彭水縣志》有關縣域變遷過程的文獻整理,在武陵民族區理論的觀照下,應該屬于能夠闡述這個學術命題的權威史料之一。
首先,盡可能熟悉彭水縣域所在的地理位置、地域分區與地貌特征,所在武陵山區的自然地理特點。今天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位于四川省東南部、烏江下游。北連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東北接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利川縣,東連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東南接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南接貴州省沿河〖JP2〗土家族自治縣、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西南連貴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西連武隆縣,西北與酆都縣接壤。地處北緯28°57′-29°50′,東經107°48′-108°35′之間。東西寬7788公里,南北長964公里,幅員面積390379平方公里。最高點為七曜山大王洞,海拔18596米;最低點為共和鄉木棕河入口處,海拔190米,相對高度16696米。”[15](P31)“彭水地域分區屬四川臺地東南邊沿和川湘凹陷過渡帶,區域底層屬武陵山小區”[15](P33);“地貌類型復雜,自然環境各異。‘兩江夾一槽是彭水地貌的主要特征。山脈走向呈北北東向,谷地、低階地、坡麓、巖溶洼地及小型山間盆地相間,逆順地貌并存。各類地貌面積百分比為:丘陵河谷區1339%,低山區占5288%,中山區占3403%。”[15](P35)《彭水縣志》(1998年版)的以上描述,似已經可以印證李紹明先生所說武陵民族區(當然是彭水縣這個田野調查點)地域文化特征“板塊式”生成的自然地理面貌了。李先生闡述“武陵民族區的族群互動與文化多樣”時認為:“武陵地區的民族皆有悠久的歷史,而且世居多年,為開辟這片土地貢獻很大。學術界一般認為,土家族族源與古代巴人有關,苗族族源與古代苗蠻人有關,侗族族源與古代百越人有關。如今武陵地區完整地具有漢藏語系的四大語族的民族,即漢語族的漢族,藏緬語族的土家族,苗瑤語族的苗族、瑤族,以及壯侗語族的侗族。此四大語族下的這些民族,長期在此互動交融,形成既有分又有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在其他地區是較為罕見的。”[1]據筆者田野調查的經驗看來,彭水地區在武陵民族區的這個特點更為罕見。
《彭水縣志》(1998年版)第四十章“民族”第一節“民族分布”,有這樣的記載:“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全縣漢族333038人,少數民族僅9人(其中:回族4人,苗族4人,藏族1人),少數民族占全縣總人口的100萬分之27。1981年始,落實民族政策,恢復民族成分,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全縣有漢族417116,苗族74153人。土家族29571人,蒙古族1526人,回族82人,侗族82人,藏族5人,彝族2人,其他未識別民族1人,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2043%(其中苗族1418%,土家族565%,蒙古族029%,其他010%)。1983年底,少數民族、漢族占全縣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4070%和5930%。1985年底統計,全縣苗族160736人,分別比1982年上升了11676%,少數民族占全縣人口的比重大為增加”[15](P726)。彭水20世紀80年代初民族識別數年,少數民族人數統計一年比一年多了,這是什么原因?
歷史上遷入彭水地區的少數民族,甚至世居于此的少數民族家族,因為歷史上特殊的國家政策的擠壓,族群自我保護意識的代代接續,十數代人沿襲家族族群身份保密規則的強化,甚至族群源頭特征的“遺忘”,給20世紀80年代初本地的民族識別造成很大困難。例如“清代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大力經營,國力日漸增強,開始在土司統治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運動,對于武陵山腹地‘生苗地區,經歷了‘開辟苗疆的血腥歲月。《貴州通志》載:‘皆毀其室戶,戮其丁壯,系其老幼,闔寨不留一人;‘至是殺戮什之七八,或數十百寨無一人。”[13](P3)鎮壓苗民起義以后,清政府對武陵山區苗民施行的“屯防制度”,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要想維系族群的生存需要,最終選擇彭水這樣的武陵山主脈的邊緣地區,以求“避開文明中心政治經略開發,便于遷徙流動,又便于躲避以自保”(李星星語)的所在,于是,彭水地區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使之成為苗族“內遷”的福地。讀黃柏權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武陵民族走廊研究”系列成果,特別是《元明清時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16]一文,可以較全面認識上述問題,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彭水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歷史事實,《彭水縣志》(1998年版)記載甚詳:“據1982年人口統計:苗族上1000人的鄉有靛水、普子、棣棠、砂石、桐榮、三義、龍溪、朱砂、連湖、聯合(含石柳)、新田、新場、諸佛、珍加、梅子埡、新化、鞍子、上巖西、龍塘壩、潤溪、龍洋、朗溪、鹿鳴、平安、龍射、葡萄等27個,其中,最多的梅子埡鄉8039人,鞍子次之為4563人。土家族人口上1000人的有太原、棣棠、砂石、三義、連湖、遷橋、珍加、善感、鹿鳴、龍射10個鄉,其中,最多的連湖鄉為3039人。蒙古族聚居于鹿鳴鄉向家村和太原鄉香樹壩村。其他各少數民族則散居全縣。”[15](P727)
在筆者看來,縣志依據歷史文獻整理的彭水“縣域變遷”軌跡,已經能夠從一個特定的側面,清楚地看到大一統“國家化”意識,推動彭水如何利用自身的自然地理條件,成為武陵民族區黔中文化的源頭之一,并持續不斷地,給武陵地區周邊的歷史文化造成影響。
縣境“商至春秋屬巴;戰國屬楚黔中郡,秦仍屬黔中郡。”[15](P78)西漢建元元年(前140)置涪陵縣,治今彭水郁山鎮。
涪陵縣始置時,轄今彭水、黔江、酉陽、石柱、武隆、道真、正安、沿河、務川、印江、德江、思南等縣和秀山縣西部,面積約35萬平方公里。建安六年(201)分地置縣后,境內存涪陵、漢葭兩縣,境域縮小。延熙十三年(250)分涪陵西北部屬漢平縣管轄。太康元年(280),并丹興縣地入涪陵、漢葭。
隋開皇十三年(593)彭水縣始置之初,地轄今彭水、武隆東北部、務川北部。大業二年(606)石城縣并入。唐武德元年(618)又分置石城(黔江)縣。次年,析彭水縣地置盈隆、洪杜縣。現縣境存彭水、盈隆、洪杜3縣。盈隆轄今彭水西南、務川北部地;彭水轄今縣地東、西、北3部;洪杜轄今彭水南部、酉陽西部和沿河北部地。貞觀二十年(646)分盈隆地置都濡縣。嘉佑八年(1063),洪杜、洋水廢縣改寨,都濡、信寧廢縣立鎮,地均入彭水轄境,縣境轄今彭水縣和酉陽西部、沿河北部、務川北部、道真東部、武隆東北部。洪武五年(1372),黔江來屬;洪武十年(1377)武隆并入。明洪武十三年(1380),武隆分治;次年黔江另置。分置時將《宋史·地理志》所載屬黔江的安樂(今連湖鄉安樂壩)、石柱(今連湖鄉石柱山)、馬欄(今石柳鄉馬蘭坪)、小溪(今龍溪鄉境內)、石門(今走馬鄉萬家村石門壩)、東流(今東流鄉)、土溪(今大河壩鄉土溪溝)、茅田(今桑拓區境內)、鹿角(今鹿角沱)、萬蹴(今萬足場西北的寨堡)10寨劃入彭水縣。民國28年(1939)量測面積,全縣幅員59216平方公里。[15](P85)
“涪陵縣始置時”,轄區不但囊括了今渝東南地區,還包括今貴州省的東北部,湖南省湘西所在的西南,烏江流域東部的大片武陵山邊緣地區,其地形、地貌最為復雜,也是人文歷史更為悠久的地區。縣域轄區從大到小,與周邊地方不斷的分分合合歷史進程中,其核心轄區的自然地理特征依然。似乎可以典型地說明這樣一個著名判斷:“中國是一個在不同時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個地區的結果。它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17]彭水縣域的歷史變遷也能夠讓我們意識到,武陵民族區“不被‘整合的向心力”的事實存在,正是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格局生成的根本原因的實際表現。這不是僅僅憑借民族走廊的理論預設所能闡釋到位的歷史規律,而是“板塊與走廊”互動生成的武陵民族區概念提示的綜合研究方向。當然,這個課題涉及的學術問題,應該以系列專題研究團隊配合的方式具體展開,本文僅僅論及這個話題的可行性而已。
參考文獻:
[1]李紹明論武陵民族區與民族走廊研究[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2]曹大明論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三個問題[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1,(4)
[3]黃金李紹明先生與武陵民族走廊[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9)
[4]葛政委論民族走廊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J]銅仁學院學報,2013,(2)
[5]李星星論“民族走廊”及“二縱三橫”的格局[J]中華文化論壇,2005,(3)
[6]郭俊,等色彩多樣的古苗疆走廊[N]中國民族報,2014-03-28:7
[7]曹大明武陵山區“內地的邊緣”[DB/OL] (2012-04-13)[2012-05-23]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294171-1htm
[8]蔣立松研究西南地區民族文化的兩個重要理論評述[J]萬方數據,2009-02-16
[9]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修訂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10]宋蜀華人類學與研究中國民族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J]//人類學講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1]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12]劉自兵,等簡論古代武陵的地理范圍[J]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
[13]柴煥波武陵山區古代文化概論[M]長沙岳麓書社,2004
[14]趙心憲地域文化與文化區域的文化研究:“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學價值問題[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6)
[15]蔡盛熾彭水縣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6]黃柏權元明清時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三峽大學學報,2009,(1)
[17]岳小國,等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國家化”研究[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13,(2)
收稿日期:2014-09-28 責任編輯:許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