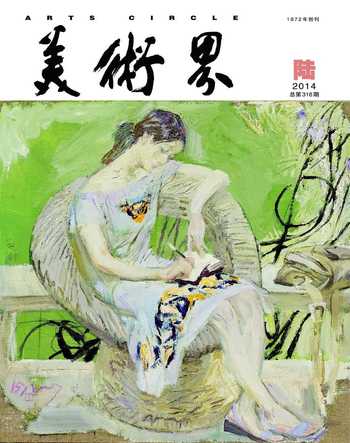試論《元本出相北西廂記》(起鳳館刊本)版畫的藝術特色
尉笑
【摘要】戲曲小說插圖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大量涌現,成為中國傳統版畫的重要門類之一,它的傳承伴隨著文本的流傳得以保存。在版畫范疇的研究中,多研究圖像的風格演變、版本類比、探討圖文關系等,得出以地域或圖像風格為基礎進行劃分的派別、以時間為單位的分期,本文在此基礎之上關注戲曲小說插圖的版畫屬性,即以起鳳館刊本西廂記版畫為對象,通過分析其出版前提、語言藝術特點,以管窺豹,探究戲曲小說插圖的版畫本體語言。
【關鍵詞】起鳳館刊本西廂記;版畫;再現行為
引言
《元本出相北西廂記》(起鳳館刊本)刻于明萬歷庚戌年(三十八年,1610)冬,起鳳館主人曹以杜作序;上、下兩卷各二十出,插圖共20幅,每出一幅,合頁連式;繪者歙人汪耕,字于田;刻工黃一楷(1580-1622)、黃一彬(1586-),書中署刻工款識;偽托李卓吾、王世貞二位先生評本。與同時期玩虎軒、繼志齋、容與堂等刊本相較,起鳳館刊本西廂記版畫以精工細致的風格稱著,人物造型纖長頗具宋人遺風,特別是衣紋的處理,順暢流線型,線條組織有序,頭身比例恰當,環境刻畫圖案修飾繁密,也正是由于該本的紋飾繁復的特點,在諸多研究中被學者冠以匠氣或者造型公式化傾向嚴重等藝術修為不高的論斷,筆者對此略有不同看法,試圖從三個方面論證該本西廂記版畫工而不匠,于規矩之中尋趣味的精神內核。
一、起鳳館刊本《西廂記》的出版前提
《西廂記》是一部中國經典戲曲名劇,流傳改編自《鶯鶯傳》至王實甫《西廂記》已逾500多年,期間代代相傳,對后代戲曲小說創作影響深遠。
明代版刻刊印盛行,于中國版畫史上造光芒萬丈之勢,戲曲小說是其重要題材之一,這與中央政權的支持有密切關系,明代戶部曾印刷多種文娛游樂為內容的書籍,督察院所刊30種數目就有《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種。官方尚且如此,地方私坊刻印文娛書籍的盛況就可想而知了。萬歷朝進入戲曲小說刊刻出版的全盛時期,對《西廂記》刊印的頻率高得驚人,萬歷四十八年間,共刊刻34種,傳本存世25種。
1498年《西廂記》第一次以版畫插圖本刊刻,出版人在牌記中寫明它的出版用途“唱與圖合”,并且讓觀眾“了然爽人心意”。這里提出了西廂記版畫最初的觀者是得到了視聽享受,基于此,為了迎合觀者的視覺欲望,出版商在版畫上花費更多的氣力,即起到宣傳作用又能拓寬銷路。漸漸形成中國傳統木刻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盡管最初是為把握商機為文字作陪襯,難免簡單粗陋,其后,由于官府的參與,文人士大夫的玩味訴求,從一定程度上指明了當時的觀看趨向。
一部作品的刊印出版,離不開繪者、刻工。起鳳館本西廂記繪者汪耕,繪畫作品罕有傳世,他的作品以版畫插圖的形式為今人所知,受雇于徽籍儒商汪廷訥繪稿1599年刊本《人鏡陽秋》22卷、1609年刊本《坐隱先生奕譜》,皆為中國傳統木刻版畫經典。刻工黃一楷,黃一彬兄弟二人系古歙黃氏一門,遷居杭州,鐫刻此書時正值黃氏刻工妙擅絕藝巔峰之時,明代最后70年間的印行的書籍中,50種為黃家所刻。
二、戲曲版畫的創作特點
戲曲小說版畫的創作前提,由文本引導,從而再現文本中的“瞬間”,兼具敘事性特征。戲曲小說版畫的創作不同于原創版畫,文本內容作為母題影響圖像的精神傳達,這就導致即使是閔寓五本西廂記版畫這般并非傳統圖配文式的版畫作品,雖然堪稱中國版畫創作意識的濫觴之作,圖像間依然能尋得文本故事的蛛絲馬跡,并且以此為主線貫穿其間。
戲曲版畫創作的出發點是文本,這就造成畫面中的人物是參與文本故事起承轉合的連結點,也是畫面中的敘事性表現的關鍵元素,例如西廂記中張生、鶯鶯、紅娘在版畫插圖中幾乎每一出都有描繪此三人,而且圖畫間傳達的人物關系與敘事關系也是圍繞三人展開的,那么這就要求不同刊本的繪者必須在人物之外的環境上大做文章,以達到創新的目的。例如《第二十出 衣錦還鄉》起鳳館刊本(圖1)與玩虎軒刊本(圖2)相較構圖類似,描繪大團圓的局面,顯然起鳳館本紋飾繁復,地面、屏風、門窗、人物衣著均飾有精密花紋,人物造型修長,相較之下更具有觀賞性與趣味性,細膩的環境描繪將衣錦還鄉的氛圍烘托得飽滿熱烈,同時稠密的圖案形成一個色塊反而將重要的人物造型襯托出來,而玩虎軒刊本白描表現則略顯平淡。不得不承認,細密的紋飾在氛圍的烘托上起到關鍵作用,畫面疏密關系對比相互襯托,繪者的意圖更為突出。
三、起鳳館刊本《西廂記》的藝術特點分析
《西廂記》的故事情節在流傳過程中已有更變,《鶯鶯傳》以張生始亂終棄,鶯鶯委身他人的悲劇收尾。至宋金以后,鶯鶯愛情故事被改編為戲曲以說唱形式廣為流傳,并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結局取代悲劇故事。以文本為創作前提,就對繪者提出一個要求,即在規矩之中求變化,文悲則畫悲,文喜則畫喜。下舉兩例起鳳館本西廂記版畫引證其繪者如何在規矩之中尋趣味。
《第十一出 乘夜踰墻》構圖以假山石居中,鶯鶯蹲坐于石上,紅娘立于石邊墻下與攀樹而上的張生對臉相迎,沒有過多紋飾,玩虎軒、環翠堂等刊本踰墻一出均以上述構圖,以下三點是起鳳館本的取眾家之長集大成的體現:首先,院墻、山石、圍欄三者均以“S”形表現,卻主次分明,互不沖突,院墻取直、立造型硬挺,山石用剔刀點刻法渲染,層次厚重,又不失玲瓏,圍欄白描勾線在畫面層次上較前兩者推后;其次,期間點綴植物,柳梢微拂,與張生的動勢相得益彰,與鶯鶯處的靜態對比明顯;最為精巧之處是鶯鶯背對觀者,以手掩面,或是嗔怪,或是羞愧,無可知曉,但就當時社會背景下待字閨中的小姐與書生私會,想必心情也是五味雜陳的相仿,中國傳統繪畫中,人物造型幾乎不會處理成背對觀者,將鶯鶯作此處理,難免讓人設想繪者汪耕的出發點,刻意為之所表達的意圖就是繪者的態度。
《第十四出 堂前巧辯》老婦人察覺張生與鶯鶯二人情愫,拷問了紅娘,紅娘直訴其事,巧辯堂前。夫人只得同意婚事,惟約張生考取功名后成婚。滿地萬字紋方磚,前景兩盆假山石打破刻板的方磚圖形。崔氏一改夫人的嚴厲形象,笑容映面,反而男仆手持棍棒,惡顏兇煞,紅娘一臉的無懼,跪于堂前,巧言辯駁。屏風曲折恰好擋住崔氏視線的余光,而透過方格窗欞隱約看到鶯鶯在俯身偷聽,拂袖掩面透著懷中的忐忑,這一安排匠心獨具!鶯鶯繪像的線條連貫流暢,沒有因窗欞的阻隔而磕絆,表情傳神,刻工的精湛技藝無以復加。
四、結語
西廂記版畫的創作,不同于獨立的版畫原創,文本作為藍本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創作的限制,各版本繪者在此前提下,習前人之作而再次進行創作表現,匠心獨運。起鳳館本西廂記版畫,紋飾冗繁,人物造型優雅,雖工細卻不致刻板,十分強調疏密對比,以達到營造氣氛的目的,人物間的動勢關系自然生動,明確其敘事性表達,工而不匠,于規矩之中尋趣味。
參考文獻:
[1]錢存訓 著《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56頁。
[2]文言內容參,錢存訓 著《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242頁
[3]張秀民《明代徽派版畫黃姓刻工考略》,《圖書館》1964,第一期,61~64頁。
【尉 笑,廣西藝術學院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