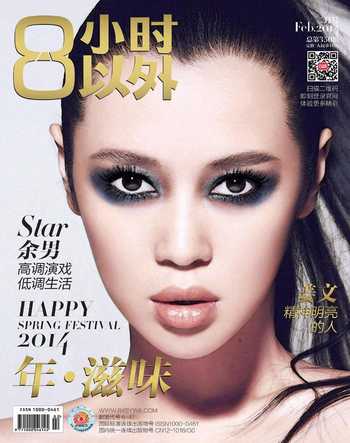老上海的年俗
程乃珊

老上海雖為十里洋場,但濃厚的傳統文化仍為強勢。堅守傳統文化的上海人家被稱為“老派人”,而新派人大多為洋大學生或在洋行現代企業任職的,盡管他們認為傳統過年繁瑣費神費時,但一年就這么一次,也就順水推舟乘機熱鬧一番。
老上海的居住模式,還是遵循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模式,家里大都會有個“高老太爺”或“賈母”。“五四”以后的文藝小說,他們大多被作為阻擋社會前進的典型,其實現實中他們并非如此不堪,某程度上他們為家庭文化的圖騰,絕對權威地維持了大家庭的和諧和包容,是傳統文化忠實的守護神。新派人在外面洋文再流利職位再高,在家里還是成不了氣候。故而老上海的過年,還是很傳統的。
中國過年習俗看似都是吃吃喝喝,其實內里傳遞的信息是十分深遠的。常年農業社會的生活模式,沒有社會福利沒有社會保障,也無太多娛樂,老百姓賴以依仗的,唯有家族間的相互提攜交往。故而,中國人從來十分看重宗族內的交往。過年的一切風俗傳統,其實就是緊緊圍繞著家族宗親四個字。
俗話說:年廿十,數銀紙,即此時此日過年的資金要到位。放出的債和借貸的債也要收回和還清。年廿開始,就要忙送年禮和收年禮。
老百姓間互送年禮,原本是一份挺樸素的感情交往,通常為自制的糕點自腌的咸肉風雞之類。客氣點的,為原只火腿、鮑魚海味;洋派點的有聽裝糖果餅干,洋煙洋酒;也有送衣料絨線等,這是十分海派的了。除非客戶商家之間,一般不會送太重的禮,以免對方有壓力,因為要回禮的。從前送年禮極少有送現金的(壓歲鈿除外),除非送大公司的禮券。老上海習俗,送現金似有看低對方的意思。
大年夜是過大年的高潮,猶如西方的圣誕夜。這一晚,不要說在外地的小輩,哪怕已分家住出去的本地小輩也一定要回來交人。大年夜最重要的一個儀程就是祭祖,所以決不能無理缺席。
大年夜的團年飯,不僅僅是寓意合家團圓吉祥,更是生動的傳承家族文化的一課。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祭祖,起的就是這個作用。老上海人家女兒嫁妝中,總有一套包括蠟簽、香爐、酒壺、桌圍的祭具。祭具是錫制的。曾問老人為啥不用黃銅,答曰可能黃銅太亮不夠肅穆。桌圍是緞子,紫色的繡花。嫁妝中有這樣一份祭器,意即從此女兒姓夫家姓,要用心供奉夫家的祖宗。
年卅傍晚時分,廳堂已布置好,朝南墻上刷刷掛出列代祖宗畫像,俗稱“尊”。祖宗眉目都是一樣的,身穿朝服掛朝珠。小時候不懂事,以為祖上真是做大官的。原來“尊”上的祖宗都是穿官服的。這種“尊”是人手繪制的工筆畫,十分細膩。“尊”下是一條供桌,上面排列著密密集集的酒盅碗筷,那是為列代祖宗準備的餐具。一張八仙桌與供桌成T型。八仙桌最朝外側一邊系著桌圍,桌前有拜墊。桌上放著供菜,其中一定會有條生猛的活鯉魚,在供桌上還是潑拉拉的,最外沿就是蠟簽香爐等祭具。
老上海人家,大年夜祭祖時就已換上過年新衣,嶄嶄新的齊齊圍站在廳堂。特別要提的是,小老婆不能參加祭祖。
祭禮由家中最年長最有權威的成員主持,上香灑酒后,他就如宣讀年終小結一樣將家族中一年發生的大小事宜一一向祖宗宣讀,其實是通報給各位家庭成員。從前通訊不發達,難得一年中人到得最齊,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然后眾人依資排輩向老祖宗磕頭。酒過三巡后禮畢。在天井或花園中已設有一只大火盤裝滿錫箔,仍由最年長之成員在大火盤前灑三杯酒,再繞盤灑一圈酒,然后點燃錫箔,直到全部燒盡,祭祖始結束。這時,熱熱鬧鬧的年夜飯就開始了。
老上海習俗,最高年資家長是在年夜飯桌上發壓歲鈿的,也可能因為此時小輩們到得最齊。說起壓歲錢,也是源自農業社會大家族的循規:古時大家同工同酬吃大鍋飯,沒有自己分配銀錢的權利,過年時做長輩的體恤小輩,就分發給小輩一點零花錢可以讓他們自由支配。這就是壓歲鈿的初衷。一旦成家另開門戶,自然就不再有壓歲鈿拿了。故而老風俗只要一天不成家就可以拿壓歲鈿,也不用給別人分發壓歲鈿。
大年夜是狂歡的一夜,再嚴格的家庭在大年夜也可以大開賭禁。長輩和小輩,主子和仆人,上上下下一起賭。最常見的是推牌九,熱鬧又有氣氛。當然搓麻將也十分時興。新派點的人,特別關系已確定的戀人,可以出去看一場半夜電影。張愛玲的《半生緣》中也提到過。
從年卅祭祖始,祖宗像就一直掛著,天天要上香,香茗鮮花供奉。上門的拜年客,因大家都是親友或姻親過房親,擁有共同的祖宗,都要上香。民俗所說的“香火不斷”就是這個意思。如是直到正月十五,“尊”就一一請下,也一樣有儀式,由家長帶領全家敬香,俗稱“收尊”。
少小時總覺得祭祖是“迷信”,現今有了相當生活資歷,方才悟到,在我們漫長坎坷的人生之旅,那自小耳提面命的祖訓家風猶如親人的叮嚀,我們懂得不能辱沒祖宗們庭,我們也懂得感恩回報……那深深扎入中華大地的宗族之根,令我們的文化靈魂得以依仗有所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