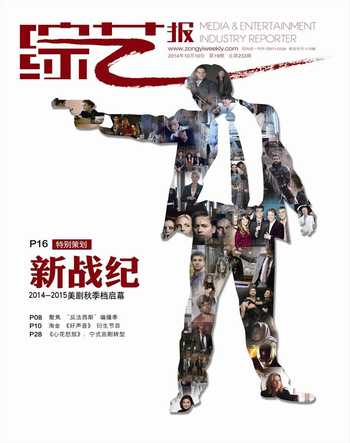《黃金時代》 愈是本真,愈是動人

文化圈中的民國熱已有些時日,銀幕上的民國范兒正方興未艾。前有王家衛以光影寫詩,憑《一代宗師》塑武人情義;后有許鞍華為才女著文,在《黃金時代》里溯文人風骨。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講,《黃金時代》都是一部勇敢的電影。這不僅在于該片逆天的3小時篇幅直接挑戰著院線排片的耐心,更在于其在別人都恨不能把電影拍得更感官、更直接的世道里,依托蕭紅的生平,交織民國文人眾生相,洋洋灑灑揮就一篇縱橫捭闔的論文。
沒錯,這就是一部用影像寫成的論文。從開頭蕭紅自報生卒年份之時起,影片就不時提醒觀眾要跳脫出封閉敘事的觀賞經驗,在視聽欣賞之余,要嘗試將更多的思考納入觀感,與創作者一起完成這幅叫做《黃金時代》的拼圖。電影大致上還是順時結構,所采擷的論據,除了片中其余人等直面鏡頭的口述之外,更加倚重的還是蕭紅作品所提供的信息。李檣和許鞍華試圖在這位女作家筆下找到她生活與情感的對應,傾聽她的心聲、捕捉她的脈息,并在她的一回身、一凝眸中,蒼涼而又抽離地看這世界。如此這般想要證明的論點,無非是呈示蕭紅的不朽——待時光飛轉七十年,較之同輩其他作家,特立獨行、追求自由,一直與時代主潮若有若無地保持距離的蕭紅,卻擁有更加綿長的生命力。
在電影約3個小時的時長里,一旦接受了編導這種間離式的講述,進入蕭紅的生命時空,就不得不承認,這無疑是最合適的表達方式。蕭紅的故事有太多演繹,稍有不慎便可能墮入狗血境地,拍成一部女作家的燦爛情史,淹沒了人物,卻失去了時代。與其這樣,倒不如將種種爭議直白地呈之于大銀幕之上。就像是蕭軍從延安回到西安、見到蕭紅與端木葒良的段落,借聶紺弩的復述,影片將坊間幾種傳聞一一呈現出來,相信哪個,那是觀眾的自由。
影片中的蕭紅,反抗包辦婚姻而從東北的呼蘭小城出逃,歷經哈爾濱、上海、武漢、山西、重慶、香港等,我筆寫我心。輾轉半世、飄零一生,所追求的無非就是自由。在她和三郎蕭軍相處的歲月里,蕭紅領略到最刻骨銘心的愛情,也遍嘗人間的苦難,但最終發覺,即便愛情也束縛不了她自由的心靈。影片就在不斷的抽離和審視之中,將蕭紅純粹性格之中的敏感與執拗,淋漓盡致地呈示出來,愈是本真,愈是動人。
電影里的蕭紅與蕭軍經歷了一場穿越愛情的漫長旅程。電影之外,觀眾也跟隨他們愛情的腳步,進入一個久違的民國文人生態圈,他們為救亡圖存奔走吶喊,卻依然保持著優雅的姿態,甚至連以筆為槍戰斗著的魯迅先生,在這部電影里也前所未見地溫和。
在這個影像紛呈、卻難見性情的時代里,許鞍華和李檣任性地拍了這部電影,足見其勇敢。《黃金時代》不僅以其不乏實驗性的筆法,豐富著當下的電影實踐,同時也為今年國慶檔的電影市場增加了一絲別樣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