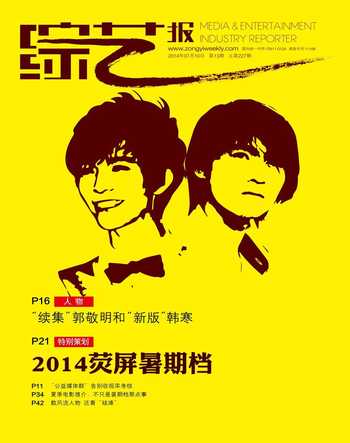《中國成語大會》中的張騰岳
因為好奇,我問了張騰岳一個問題,“在央視出鏡多年,為什么你的知名度一直不高?”他回答說:“別人認為我知名度低的時候,我做著自己喜歡的節目,挺快樂。”
很多人看過張騰岳主持的科教節目,有幾個標簽都可以貼給他:會講科學故事的人,把青春獻給科教節目的主持人,學播音主持的理科生。
在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的譜系里,張騰岳很難定位。他既不是新聞主播,也不是綜藝大咖,他主持的節目隱藏著娛樂性,又不乏趣味,足可以引起關注。
在《中國成語大會》中成長
張騰岳把自己從科學節目的嚴肅風格中解放出來,發展了綜藝節目主持的潛質。就像一名運動員,在訓練中,完成一套新動作,能量倍增的狀態。
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這一年格外顯眼,因為《中國成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均進入央視一套晚間黃金時段播出,兩檔節目的總導演關正文稱張騰岳為“早該被關注的當今最有才華的主持人之一” 。主持《中國成語大會》的經歷,對于張騰岳來說,有如天啟。“當時確定我主持這檔節目的時候,關正文導演給了我一本上百頁的主持人方式、心態和臨場把握手冊。”張騰岳對這個節目的主持要求感到驚奇。他與關正文導演見面,并在節目中互動。在錄制的全過程中,他把自己從科學節目的嚴肅風格中解放出來,發揮了自己綜藝節目主持的潛質。他的鋒利語言和張弛有度的節奏把握,屢屢激發出選手的神來之筆。如,用俚語解釋現代漢語、用典故原文闡釋白話、用街頭語言表達情緒。他與選手中的每一個人交流——包括用外號稱呼他們,并互加微博。他甚至轉換了角色,和選手一樣,惴惴不安,低著頭,用余光看著答題者,在舞臺上踱來踱去,像是一個準備逃課的孩子。
張騰岳對場上選手對待搭檔變幻無常的態度有著敏銳的感覺。“從進入決賽開始,這一場他們是搭檔,下一場可能就是對手。怎么處理自己與隊友的關系變得很微妙。每場都有人在哭。”
采訪張騰岳的時候,距離他錄制節目的時間,大概過去了三個月,他可以毫不猶疑地說出錄制時,每個選手的小插曲,甚至坦言,現在還沒緩過神兒來。就像一名運動員,在訓練中,完成一套新動作,能量倍增的狀態。
蘭州起步
對于學理科的張騰岳來說,被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錄取的時候,他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上世紀60年代,張騰岳的父母供職于鐵路系統,從北京支邊來到甘肅蘭州,母親希望張騰岳考回北京的強烈愿望,影響著他的人生方向。高考的時候,他準備填報的志愿是北方交通大學,最終錄取他的是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學院)。初中階段,張騰岳用學生式朗誦,在教師節獻詞、班隊會主持、團委會召集等活動中訓練了自己的語言能力。高中階段,經歷了擇校考試,張騰岳與重點高中的學霸站在同一起跑線上。1994年,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實行文理兼收,有三男三女理科生被錄取,他是其中之一。對于張家來說,這是個天大的好消息,對于張騰岳來說,他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畢竟這是個與藝術不怎么沾邊的家庭。
“到了播音系,上的都是文科生的課程,一個學理科的學生,一開始都不會做筆記。”據張騰岳回憶,他們宿舍里住著一幫子當年的文藝青年,寫文章都非常厲害,說話更是引經據典,他這個學播音的科班生,插不上嘴,說不上話。宿舍里同學聊到半宿,他是那個聽著睡著的人。
這段經歷讓張騰岳很有挫敗感,也激發了他的斗志,逐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堅守。
蟄伏時期
《中國成語大會》讓張騰岳撿起了自己,沒有在時代的洪流中沉寂下去。
從1998年大學畢業,加入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到2004年,整整五年間,張騰岳沒有明確的主持風格,那是一個“吸取思想養分,積累沉淀的五年”。之后,他在《走進科學》欄目中經常以休閑裝示人、以說故事的方式講科學知識,這種形式逐漸成為他的風格。
2012年底,《中國好聲音》啟動了中國電視業制播分離的新模式,決心“開門辦臺”的中央電視臺,吸引了更多社會力量的加盟。張騰岳從前在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的不少師友,或出國,或下海,或歸隱,星流云散,一批專業精英,人生走向就此改變。
從青澀到成熟,由青年到中年,主持人的新聞理想,文化人的媒體擔當,職業生涯的螺旋上升,當下方興未艾的主持人跨界轉型,市場化的制播分離運作,在張騰岳的頭腦中彼此交錯沖突。而它的交匯點,就是對未來發展的擔憂。這時的張騰岳愈來愈有一種想突破自己瓶頸的愿望。他說,“《中國成語大會》讓他撿起了自己,沒有沉寂下去”。
在多個層面與時代共舞
張騰岳沒有將自己置身于市場化的風口浪尖,也沒有將自己在體制內刻意地邊緣化。他寧愿消耗巨大能量,盡力與我們所居的這個時代在多個層面共舞。
對于張騰岳的風格,頻道總監金越和節目總導演關正文,有相同的觀點:有文化人的氣質、不乏幽默、與節目風格搭調、有檔期。
在節目錄制前,張騰岳看完了整本成語詞典。但這遠遠不夠。
“錄這檔節目首先是個體力活,比做直播難很多。”張騰岳思考片刻后說:“任何一個直播都有時間限定,分給主持人的活兒就是其中一段,我只要完成分配的任務就足夠了。比如直播‘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對接,欄目組的預案甚至精細到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直播現場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時候天宮運行的位置,所處姿態,之后的環節安排,我們心理完全清楚,唯一可能的變化就是它失靈了。這個我們同樣也有預案。這種直播過程,我們沒有更多的負擔,考驗的是主持人統籌時間的能力。而在《中國成語大會》中,要求主持人的狀態完全不一樣。”
“《中國成語大會》錄制時間不管有多長,主持人必須要保證自己的頭腦是清晰的,反應是敏捷的。當一個選手對一個詞語做出一種解釋后,是否符合賽制要求,是否成為一個高水準的表達,主持人需要在第一時間作出判斷。如果選手的解釋有偏差,主持人還要及時調度嘉賓給予補充解釋,比如成語的來源,具體的含義,解釋它的其他辦法。在這檔節目中,腦力激蕩的成分甚至大于體力消耗。”
舞臺上,張騰岳和選手距離咫尺之間,他們能互相感受到對方的緊張情緒,選手負責比賽,主持人則更像是導演,現場調度“演員們”的情緒、控制節目的節奏、恰如其分地制造節目高潮。
2014年的節目市場上,文化節目持續發酵,幾乎每一家電視臺至少有一檔這樣的節目。為什么《中國成語大會》脫穎而出?一位行業記者分析:《中國成語大會》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度,這將它置于粗糙節目的范圍之外。它沒有簡單的復制某個節目模式,而是注重節目形式與內容的均衡發展。她說:“《中國成語大會》沒有沿用‘青歌賽的形式,也沒有復制《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模式,因此,它有熟悉的陌生感。我并不是批評其他節目,相反,我認為節目創作者很高明,他使《中國成語大會》在節目博弈的夾縫中得以生存。”
承認市場競爭,然后謹慎地尋求自我生存的空間,這種策略決定了《中國成語大會》的生存能力,也讓張騰岳感受到好節目帶給主持人的成長。
在科教頻道工作十年有余,張騰岳沒有將自己置身于市場化的風口浪尖,也沒有將自己在體制內刻意地邊緣化。市場化或邊緣化是一種愜意的狀態,但他寧愿消耗巨大能量,盡力與我們所居的這個時代在多個層面共舞。正如他在開始學習播音的那些年,從不完美中養成追求完美的習慣。
(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