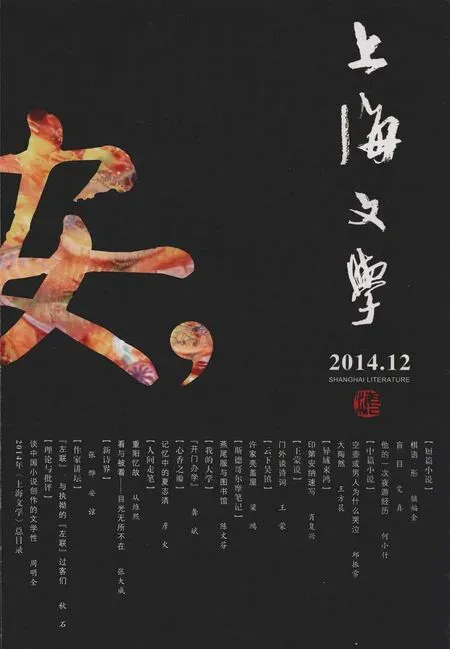“左聯”,與執拗的“左聯”過客們
秋石
“左聯”成立至今,已經八十四年了。然“左聯”的精神,左翼文化運動的深遠影響力,迄今熠熠生輝。
如何看待“左聯”,給“左聯”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地位與評價,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并不因為“文革”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幫”的蓄意歪曲與破壞,而改變其本來的面目。誠如“左聯”盟員、原上海市委副書記夏征農同志1998年(時年九十四歲)在為工人研究者姚辛所著的第二部“左聯”研究專著《左聯畫史》所作的序中指出的:“左聯”和她從事的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是在我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她的成績與缺點都是與這個時代背景相聯系的。現在有的文藝界人士,離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離開歷史事實,說什么左翼運動,不是運動,是政治運動;說什么“左聯”只提口號,沒有創作;說什么魯迅到死才擺脫“左”的束縛等等,這就等于否認“左聯”的存在,否認她的歷史地位。因此,為了糾正這些偏見,把“左聯”成立的時代背景和她在國民黨文化圍剿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斗爭經歷,把“左聯”盟員致力于左翼文藝活動的奉獻精神和他們的深得青年喜愛的創作,把“左聯”的各種活動及其在當時文藝界產生的影響,采用各種形式,全面如實地介紹給廣大讀者和國內外研究者,使人們能根據可靠的歷史資料,對“左聯”的是非功過,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是當前文藝界的一項迫切任務。
夏征農的這一評析,對于后來的研究者,無疑是深有裨益的教誨。
夏征農同志如此,另一位老人,雖非“左聯”盟員但是屬于左翼文化人與學者行列的著名文藝理論家、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先生,也不住地向我們發出呼吁。
記得還是在十多年前,為筆者的兩部左翼作家研究著作《蕭紅與蕭軍》與《兩個倔強的靈魂》作序時,賈植芳十分感慨地回憶起十年前他應邀赴日本講學時,時任東京大學教授、日本共產黨的老一代黨員丸山升先生對他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1930年代‘左聯文學,你們中國人現在不研究了,而我們日本人還在研究。”對此,賈植芳先生認為: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如果我們想把這份歷史遺產傳到后世手中,確鑿的材料可能要比倉促的結論更顯得重要切實。搶救歷史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歷史責任。
其實,早在賈植芳先生發出上述感嘆,呼吁“把這份歷史遺產傳到后世手中”,拿出更多更“確鑿的材料”之前,就有不少人在做這項工作了。值得書上一筆的是,有一位普通工人出身名叫姚辛的老人,直到2011年1月三九寒天時節臨離開人世時,其清貧至極,以致于尋覓不到一套像樣的衣物可以裝殮的七十七歲老人,卻在“左聯”這片富礦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了五十五個年頭。遠在賈植芳先生發出呼吁的多年前,就為史學界捧出了厚厚兩大本史料巨著:1994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萬字的《左聯詞典》,1999年同樣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有著上千幅圖文并茂的《左聯畫史》。在這之后的2006年,依然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達一百萬字的《左聯史》。其中,《左聯詞典》由原“左聯”領導人夏衍先生作序,《左聯畫史》,則由一直關注并給以他熱忱幫助的“左聯”老戰士夏征農撰序。
上世紀30年代的“左聯”,及以“左聯”為主導的左翼文藝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文化現象。誠如賈植芳先生指出的:“左聯”的發生、發展,受當時國際左翼風潮的影響,尤其是受蘇聯、日本的影響。1920年代中后期,太陽社作家對“五四”作家魯迅、茅盾、冰心等人進行粗暴批判,他們罵魯迅是“封建余孽”、“雙重反革命”等,否定“五四”傳統。周恩來對中國的政治形勢、文化力量的認識頗有遠見,指出對魯迅的圍攻是錯誤的。馮雪峰根據文委書記潘漢年的意見,要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合作,魯迅也意識到進步作家聯合起來的必要。這樣,1930年年初,“左聯”成立了,魯迅是“左聯”的旗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上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消息傳遍了四方,并且很快輻射到了全國各地,乃至鄰近的海外國家。
毋庸置疑,“左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是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的。她確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令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恐懼萬分,特別有戰斗力的一支文化軍隊。誠然,在其六年的存在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包括自成立那天魯迅在發言中高瞻遠矚警示的那個日趨嚴重的“左”。然而,她的功績畢竟是第一位的。
不錯,有關“左聯”和“左聯”的歷史的方方面面,在國外,尤其是當時普羅文藝同樣盛行的日本,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歐美一些國家的學者(多為高校)也都“還在研究”,而且也出過一些成果。但,話又得說回來,他們的這些研究與成果,無論是規模、深度,還是質量,都是遠遠不能與中國國內學者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的。而有關“你們中國人現在不研究了”的說法,筆者認為,更是失之偏頗。在國內,研究“左聯”是大有人在的,不僅僅是在高校與研究機構內,幾十年中,還吸引了一些來自民間各階層的業余研究者。他們雖然沒有經費,沒有唾手可查的史料,但他們舍得投入,有一股子韌的獻身精神,出版了不少引起學術界重視的大部頭著作。他們中的佼佼者,憑著自己的刻苦與努力,最終成為了有所建樹的學者、專家行列中的一員。
對此,筆者的經歷或可作為例證。自1979年8月在哈爾濱與著名老作家蕭軍相識相交始,先后同1930年代走過來的三十余位左翼文藝前輩面對面敘談印證。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活在縣級基層,沒有經費依托,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詢,只有一紙化工中專文憑的筆者先后出版了《蕭紅與蕭軍》、《我為魯迅茅盾辯護》等五部專著,也發表了四萬余字的左翼文學研究論文,就印證了這一點。
所以,中國對于“左聯”的研究,決不是這位名叫丸山升的日本教授口中不明就里發出的“你們中國人現在不研究了”的說法,而是更紅火更有深度了。但是,這個“紅火”、“更有深度”,是相對于自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至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而論的。在1966年2月林彪與江青勾結,反復修改形成的那個所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江青聲稱新中國的十七年文藝界,是“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紀要》還在文化革命的口號下,基本否定了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而實際情況呢,“文革”前新中國十七年的文化學術界,對于“左聯”,對于左翼文化運動的研究,面是比較狹窄的,也談不上有什么深度的研究。除了少數擔負領導工作的親歷者偶爾應約寫的一些回憶文字,鮮有什么深度研究的著述問世。如若說有,要么是對延安文藝運動的歌頌與闡述,要么也只是局限于魯迅的研究,或以魯迅為中心展開,稍帶一下“正確”的左翼文學作品。就是這樣的魯迅研究,也是帶著濃厚的時代政治色彩。其個中的緣由,復雜而又多樣。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基于魯迅晚年的一系列論述,特別是其臨終前夕所持的態度和立場。當然,“左聯”后期的領導人周揚、夏衍們對魯迅的不尊重,同樣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關上述兩個原因,都可以從魯迅臨終前兩個月出于一時憤怒寫下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找見答案。故而,新中國成立后,在當局要求進一步高高舉起的魯迅這面“文化革命的旗幟”的號召面前,無論是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親歷者,還是新一代研究者,無不為之小心翼翼地加以傾力維護這面旗幟,無法進行深入的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探討與研究。再有一個原因是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如1955年的“全國共誅之的”反胡風運動與1957年的全民“反右”運動,令一大批自1930年代起就跟著中國共產黨一路艱難跋涉進入新中國的文藝界人士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被歸入另類。
林彪、“四人幫”一伙視“左聯”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為黑線,及對幾乎所有健在的“左聯”盟員實施法西斯摧殘這一基本事實,與當年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當局實施文化圍剿的做法,是同出一轍的:都在制造文化沙漠,以達到其從精神上麻痹、奴役國民的目的。
隨著林彪、“四人幫”這兩個擅長制造文化沙漠的反革命集團的相繼被粉碎,人們從源頭上擺脫了羈絆,思想獲得了空前的解放。與此同時,一度高聳入云天的魯迅回歸了人間,卸脫了“神”的面紗。誠如在那個黑暗年代共同反對國民黨當局實施的文化圍剿中并肩作戰的魯迅親密戰友茅盾先生,在其《答〈魯迅研究年刊〉記者的訪問》(刊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一文中指出的:“魯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學,把魯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魯迅歪曲了。魯迅最反對別人神化他。魯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這個樣子。”茅盾先生還特別指出,魯迅研究中也有“兩個凡是”的問題,即:“凡是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魯迅賞識的就好到底。”正是在這么一種寬松的研究氛圍下,使得人們前所未有地給松了綁,對魯迅以及與魯迅有關的人和事,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整得死去活來的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曾被魯迅生前不當譏諷為“四條漢子”為首的一大批1930年代左翼文藝前輩,從源頭上展開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實事求是的評判。從而使“左聯”,以及“左聯”領導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研究,在回歸本位的同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全面的、深入挖掘、搶救、整理史料的紅火局面。
1979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后的第一個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而不受任何羈絆的難忘歲月。正是在這樣思想空前活躍,文藝走向全面復興的新時代氛圍下,由剛組建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牽頭主持,編寫了一套以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為主線的“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一直持續到1990年左右。距今十五年前,在復旦大學第九教工宿舍,聽參與此項工程的分組負責人賈植芳先生講述,1979年剛進行這項工程時,經中宣部批準,還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一批或親歷過那個年代的斗爭實踐,或在建國后從事過這方面教學、研究的學者、專家,進京編寫。北京魯迅博物館,以及北大、人大、北師大等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機構,以及已故史學家、《新文學史料》的創刊者牛漢先生,曾為人文社社長、馮雪峰研究專家的陳早春等專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而昔日“左聯”活躍過的天津、青島、廣州等地,有關“左聯”、左翼文藝運動的研究,自“文革”結束至今的三十多年間,同樣從來不曾間斷過。特別是《左聯回憶錄》、《左聯紀念集》、《左聯論文集》,以及茅盾、夏衍等“左聯”領導成員撰寫的回憶錄的相繼出版,更是說明了一切。這與日本丸山升教授的那個“你們中國人現在不研究了”的說法是明顯不符的。
下面,就以“左聯”誕生地上海為例論述對于“左聯”的研究狀況。多年來,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大學、上海戲劇學院,以及交大、同濟的文科師生,多以“左聯”為題材展開研究,或作畢業論文時為首選題。而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及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又以出版“左聯”研究及相關延伸專著為最。上海社科院、魯迅研究館也如此,不過,這兩個研究機構多以注重科班、名家研究為主。歷史悠久,由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見證者、親歷者巴金先生等老一代作家創辦的《上海文學》、《收獲》雜志等,幾十年來,領銜刊發了相當數量的研究作品,對推動全國范圍的左翼文藝運動研究的深入開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正是基于巴金先生、靳以先生等人身體力行經年累月的推動,上海市作家協會圖書資料室收藏的有關1930年代的珍貴文藝資料,堪與徐家匯藏書樓相媲美。筆者曾不止一次在這里查閱到有關“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上海文壇的積極行動,以及同年末展開的文藝社團論爭的史料。此外,在上海,“左聯”誕生原址上建有國內唯一一家“左聯”紀念館。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其藏書、資料及收集到的相關文物,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左聯”紀念館成立后,還相繼組織籌備舉行了大規模的“左聯”成立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和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不僅邀請當時仍健在的“左聯”盟員出席并演講,而且還云集了來自全國各地以及海外的學者。彌足珍貴的是,“左聯”紀念館不做象牙塔,他們不但重視名流大家的研究,同時也特別關注小人物民間草根的研究成果。如本文開首時提及的來自浙江嘉興的工人學者姚辛,“左聯”紀念館對其格外關注。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們還給由于沒有收入一度陷入困境的姚辛發放過與其工作人員不相上下的“工資”呢!對此,同樣作為研究左翼文化運動的民間草根研究家的筆者,在同“左聯”紀念館工作人員的近十年交往中,感受頗深。他們尊重每一位研究者,無論你是科班出身,還是來自基層的小人物,均予以一視同仁,從不厚此薄彼。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將“左聯”歷史、“左聯”傳統與愛國主義教育緊密地結合在一塊,并將其普及到中小學生中去。
在“左聯”研究領域成果較為突出者,當數老一輩研究家、“左聯”時代同行者的丁景唐先生,以及他的女兒、第二代研究者丁言昭等。
在上海眾多的研究者中,有一個人是不能不提及的。她就是擔任過“左聯”紀念館副館長與中共一大紀念館副館長的張小紅女士。在其有限的二十多年研究生涯中,張小紅先后出版了《文化名人蹤跡尋——文壇之光》、《左聯五烈士傳略》、《左聯與中國共產黨》三部著作。此外,她還組織編寫出版了《陶晶孫百年誕辰紀念集》等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張小紅還撰寫、發表了有關柔石、馮雪峰、魯迅、瞿秋白、歐陽山、徐懋庸等“左聯”盟員的系列論文。令人遺憾的是,自己一生孤獨而熱衷于“左聯”研究的張小紅2011年1月14日去世時,年僅四十九歲。
另一位是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孔海珠女士。幾十年來,在其父親——也是1930年代左翼文化人的孔另境的熏陶下,潛心于左翼文化事業的研究,其成果不可謂之不斐:先后出版了《痛別魯迅》、《聚散之間》、《左翼·上海》等多部專著,有的史料為其獨家擁有。
在江蘇鹽城市黨史辦工作的傳記文學作家劉小清先生,在歷時數年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的三十五萬字《紅色狂飚——左聯實錄》一書(200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則是一部較為完整闡述“左聯”歷程、史料較為豐富的著作,有著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行文至此,筆者還需為已故工人學者姚辛對“左聯”研究所作的特殊貢獻再書上一筆。
在多年的研究中,姚辛驚訝地發現,盡管只有短短的六年,但先后參加“左聯”的作家和文學青年有四百多人,可在文學史上有記載的僅五六十人,“左聯”大部分盟員失傳;許多對革命、對新文學運動卓有貢獻的盟員長期被湮沒。就連《中國大百科全書》這樣的經典史著,其所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詞條,也被含糊其辭地寫為“盟員總數達數百人”。
考慮到健在的“左聯”盟員越來越少,如不加緊搶救、整理,上世紀30年代乃至20世紀文學史上這一段精彩紛呈高潮迭起的歷史,將因此留下一段空白。還是在1976年的深秋,“四人幫”剛剛被粉碎,中斷“左聯”研究多年的草根學者姚辛又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的新長征:自費到全國各地尋訪那些健在的“左聯”盟員。每每尋訪到一個“左聯”盟員。姚辛都要千方百計地找尋與“左聯”時代相匹配的史料、照片等。僅就環境氛圍較為寬松的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間,姚辛先后訪問了九十多位“左聯”盟員,還與先期逝世的四十余位“左聯”盟員的親屬,以及臧克家、杜宣、蔡若虹等與“左聯”盟員有過密切交往的1930年代著名作家藝術家進行訪談印證。而到了2000年3月2日“左聯”誕生七十周年時,幸存于世的“左聯”盟員也就十來個人了。有的,是在即將離世前的病榻上與他會的面。著名老作家,歷史上備受魯迅、毛澤東關懷的老作家丁玲,就是在北京醫院的病室里與他會的面。會面后不多日,丁玲就告別了人世。姚辛每每與人談及這些,就會唏噓不已。
“左聯”盟員王志之,在所有盟員中,有著極其顯赫的經歷:1927年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31年加入“左聯”,1933年又在華北長城前線參加了馮玉祥領導的抗日同盟軍。1932年11月魯迅來北平省親時,是他邀請魯迅在北平師范大學演講《再論“第三種人”》;1933年4月23日又由其代表北平“左聯”在北海公園玉龍亭主持召開有著名學者朱自清、鄭振鐸、范文瀾等人出席的文藝茶話會。在1936年國民黨御用工具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發布的“查禁反動刊物《新認識》等29種”P223號通告中,他的《魯迅印象記》與《租妻》兩書名列其中。但就是這樣一位對革命對新文學運動作出了杰出貢獻的老知識分子,解放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卻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被送去勞改,直到1979年方獲平反。由他親筆撰寫的《南昌八一起義散記》,在1981年的《人民日報》上作了連載。他的《記北方左聯》一文(發表于《新文學史料》)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王志之老人手中掌握著大量鮮為人知的極為珍貴的北方“左聯”史料,搶救、整理迫在眉睫。在北京的一次訪問活動中,姚辛及時捕捉到了這一信息。幾經周折,姚辛打聽到王志之在吉林東北師范大學任教的蹤跡,于是就連夜坐車北上趕了過去。就在姚辛和他會面不久,八十五歲的王志之老人心滿意足地合上了眼睛。正是有關王志之的詞條,進一步豐富了《左聯詞典》的內容,讓人們見到了“右派”分子王志之背后光彩奪目的一生。
尋訪中,姚辛還澄清了許多有關“左聯”的歷史誤會。為了澄清是否曾有“湖南左聯作家群”,他借錢趕往湖南,冒著三九嚴寒,翻山越嶺,深入到洞庭湖北岸的安鄉縣遍訪有關人士,終于從源頭上澄清并否定了所謂歷史上存在過的“湖南左聯”及“湖南左聯負責人曾白原”的這一說辭。
丁銳爪、馬子華、韓勁風、巴夫……近百位一度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左聯”成員,都是經姚辛的一手挖掘才得以重見天日。最后載入《左聯詞典》的盟員多達二百八十八人,這是國內關于“左聯”盟員最具權威最為詳盡的記錄。
令人扼腕的是,長達五十五年的無私奉獻,擁有煌煌四大部學術著作,臨終時卻沒有任何職稱,由于長期積勞成疾,于2011年1月21日的凌晨時分,倒在了他畢生為之鐘情、奮力行進的“左聯”研究征途上。較一周前去世的原“左聯”紀念館副館長張小紅,他在這個世上多活了二十八個年頭。如今,他已逝世三周年,作為他的幾十年的草根同行謹以此文紀念之,并將他的未竟事業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