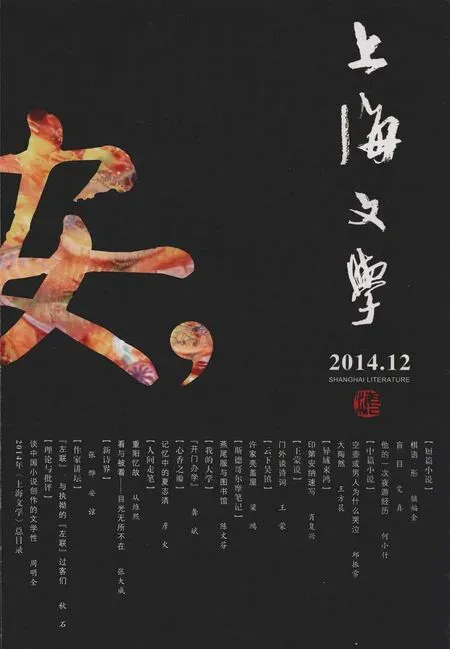談中國小說創作的文學性
周明全
近年,馬原推出了《牛鬼蛇神》、余華推出了《第七天》、閻連科推出了《炸裂志》等,這些作品,甫一面世,就遭到了毀譽參半的評價。褒者認為,這些作品是批判現實主義之力作,是當代非常優秀的小說。貶者則說,這些作品晦澀難讀,了無新意,雖然打著現實主義的旗號,但在表現現實時卻顯得蒼白無力、隔靴搔癢。于我理解,這些作品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但問題是,這些作品和現實貼得太近,作家們在悲天憫人的文學面具的遮掩下,恨不得以新聞體來直接呈現現實,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文學本身。當然現實性,是文學的一個重要指標,但當文學性喪失之后,現實感再強烈,對文學本身又有何意義呢?面對這個題目,心里出現一個影像,一只漏水的木桶,它的短板,正如當今的作品一樣,皆由文學性那塊最終的板子,出了問題。現實主義只是文學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手段。無論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罷,都可以是木桶上的板子。文學創作的目的,是使作品具有文學性。但現在,不少作家,運用著這樣的主義,那樣的想像,就是罔顧文學性這塊最需要老老實實對待的真正指標。“手段”當成了目的,本末倒置了,作品當然要出問題。文學性是文學的重要指標,文學性達不到,其他一切指標再強大,再離奇,都只是怪胎。所以,我覺得,當下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最根本的問題是回到常識上來,重構作品的文學性——這一真正的指標。
文學創作將現實生活的原材料作為創作的基石,通過藝術加工,生發出既來源于現實生活又有別于現實生活的具有超越性的“建筑品”,這個超然于現實之上的“建筑品”,才是文學和藝術所要達到的目的。18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巴爾扎克,闡明了文學高于生活的兩層含義:其一,文學對生活的反映超越了現象摹寫的層面,而是尋找和揭示隱藏在生活現象背后的各種動因,對生活做出藝術概括;其二,文學不僅是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人生感悟和理想追求的表現。此兩點將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作了精辟的論述,他的最終旨意是,文學應在現實之上。以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為例,雖然描寫一個浪蕩公子始亂終棄的故事構成,是如此的簡單和司空見慣,但由于它極為生動、真實、甚而美妙的文學性的緣故,終究成為我們常看常新的經典。
文學的創作要貼近現實,要接地氣。同時,文學必須是對生活的嚴肅審慎的思考,但又能飄逸輕盈地抽身于現實之外。比如老村的《騷土》,整個故事架構來源于“文革”,和現實貼得相當近,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從頭至尾一直是在老老實實、極其文學性地講故事,最終超越了現實本身。態度決定一切,在我看來,當今的文學問題,首先是態度問題。
文學是現實的影子,它不是現實本身,而是“光”的作用后的顯影。一位作家,若“現實”到把“黑暗”原封不動地搬出來,那大家就瞎了,以盲致盲,什么都看不見了。大家本來就在現實里,若作家的職責只是“搬”,那讀者就沒有必要看小說了。優秀的作家,要賦予影子以靈魂,讓影子有靈氣,讓文學升華為現實的最終的影子,有靈氣有溫度的影子。這影子其實也是作家自己的影子。所以影子的心是怎樣的,作品就是怎樣的。而唯有貼著靈魂的寫作,才能寫出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
再者,由于語言的有限性、故事的歧義性,作家要努力讓讀者看清楚自己要表達些什么。要想表達明晰,首先作家心里要有光亮,眼里要有光亮,要透過黑暗,不受遮蔽,給思考的結晶鍍上光。比如蕭紅,她1911年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她的出生、成長正值中國最混亂的時期,民不聊生,唯剩黑暗。但她的文字,卻是思考黑暗的果實,黑暗的結晶體,閃著亮光。她的《生死場》,寫東北農村人民在沉滯閉塞生活中的掙扎和對命運的抗爭,《呼蘭河傳》則來源于蕭紅的童年生活回憶,描寫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這兩部小說,成了那個時代很重要的現實主義力作,至今都頗受關注。
要做到上述這些,必須關注作品的“文學性”。文學性是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術語,意指文學的本質特征。雅各布森認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并非文學而是‘文學性,即那種使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文學性指的是文學文本有別于其他文本的獨特性。在雅各布森看來,如果文學批評僅僅關注文學作品的道德內容和社會意義,那是舍本求末。文學形式所顯示出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才是文學理論應該討論的對象。簡而言之,文學性是文學內部研究的基本問題,它研究文學的元素及其構成方式。
以小說為例,文學性主要指的是小說的故事、語言、人物、結構等基本要素。中國的小說創作,必須具備獨特的品質和面貌。真正的“中國小說”,必須逐漸擺脫對西方經驗的被動依賴,主動而自覺地返回到中國人自己的文學經驗的“原鄉”。它來源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是我們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也是描述我們自己精神生活與現實生活的一種極其高級的寫作范式。從文學性上講,它應該具備八個方面的向度。
第一是故事性。應該說,中國小說特別是幾部古典名著,故事都是非常精彩的。這幾乎是中國小說最重要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們民族文學的最重要的品質之一。《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聊齋》等,它們中的故事和人物不僅養育了我們的戲曲、評書、民族通俗文化,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氣質乃至于精神生活。作家曹文軒就認為,“故事與小說的關系是無法解除的,是一種生死之戀”(曹文軒《小說門》)。但遺憾的是,改革開放以后,爭先恐后地追趕潮流的中國作家們一時間學習西方模仿西方,把西方文學技巧幾乎全部演練了一遍。什么無故事無主人公,甚至無主題的寫作,也成為一時的風尚。“……瞧不起故事和人物,現在文學要回歸,寫故事能力太差了。小說寫不好故事是很大缺陷,作家應把精力的百分之七十下到故事里。小說不可以丟失故事,沒有好故事是失去讀者的一個原因”(鄭麗虹,蔣子龍《小說沒有好故事是失去讀者的原因》)。無獨有偶,同樣的意思,香港作家金庸說得似乎就更明白了:“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茅或魯迅,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那傳統意義的中國小說是什么樣的呢?我覺得首先應該是好的故事,細致入微,曲折動人,一章一回,環環相扣。作者要先踏踏實實把故事講好,別急著抒情、議論,更別先想著什么‘文字的張力、‘意象的感人之類,就是所謂的以辭害意。”(金庸,徐德亮《寫小說先得會講好故事》)可是,近年來,有些作家急切地拋棄了故事,玩弄技巧,有意忽視,甚至看不見故事。故事是什么?福斯特說,故事雖是最低下和最簡陋的文學機體,卻是小說這種非常復雜的機體中最高的要素。同時,福斯特也一再強調,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面。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
余華的《活著》,就是講述福貴的親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頭行將死去的老牛孤苦無依的故事;莫言的《豐乳肥臀》講述的是母親苦難的一生;賈平凹的新作《帶燈》,通過最基層、最日常的瑣事,講述了帶燈這個女鄉村干部的故事。他們故事講得好,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讀者,只有讀者愿意讀,寫作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從讀者接受小說的度上看,“長期以來,人們對小說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故事。古往今來的人們對故事的傳播和接受表明了愛聽故事乃是人類的一種本性”(徐岱《小說形態學》)。
馬原的《牛鬼蛇神》出版后,遭受不少質疑。但他在接受采訪時辯解道:“一場大病會讓任何人成為哲學家。面對生死,我會想能不能繼續活著,在被迫成為哲學家的過程中,有了《牛鬼蛇神》這部小說。”我個人覺得這可能是馬原為炒作新書的說辭吧。小說就是小說,“為小說爭得巨大榮譽的,也只有故事。一名小說家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如何講好一個故事。舍此別無他途”(徐岱《小說形態學》)。
第二是人物塑造。小說中的人物,可以說是讀者打開小說之門的一把鑰匙。比如,莫言《豐乳肥臀》中的主人公母親,她是我們理解整部小說的關鍵,亦是理解莫言筆下那個時代的關鍵。“如果把一篇小說比作一件衣裳,那么人物就是這件衣裳的衣領,衣領具有統攝全局的重要作用。沒有衣領的衣裳只能是奇裝異服,沒有人物的小說也只能是偶爾為之的探索性新潮小說,常規意義上的小說都應該有人物,而且,還應該將塑造人物形象作為小說創作的核心任務”(納張元《寫活人物是小說創作的重心》)。
古往今來,每個時代的作家,都為我們塑造了不少性格突出的典型人物,多少年過去了,可能讀者已然忘記了作品的名稱、忘記了作者,但那些典型人物,還是被我們銘記在心。“一部小說讀過一段時間后,書中的人物仍能活生生地留在我們心中,人們不僅記得他們,而且推斷得出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應,這就是好小說”([西班牙]德利維斯,見《“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下冊)。
文學的真正動力只有這么幾個——生、死、人性、人生、心靈。塑造人物,最終還是需要往這些終極命題上靠。比如,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對反面人物司馬庫的塑造上,通過司馬庫火燒村頭石橋以及破壞日軍鐵路橋梁的兩次戰斗,將其英雄本色、有勇有謀,最重要的是人性,給寫活了,讓人過目難忘。
第三是語言。童慶炳認為,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它往往比題材等更能顯示作家的個性(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但時下,幾個月搞一部數十萬字長篇的小說家比比皆是。但這些小說,語言粗糙得驚人,語言的真實性、語言的氣質、語言的狀態完全被忽略了。整部小說,“只見語言的奔跑,看不清語言所指的世界本身。極度的語言過剩就是極度的語言匱乏,當代眾多作家的作品,都呈現出這種荒唐的語言學悖論”(郜元寶《眺望語言》)。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就是他一貫的風格展現,王朔的風格則是對現實、對權威的調侃與無情嘲弄……而風格又是和語言密切相關的。一個作家風格的最終定型,和其對語言的使用有著最直接的勾連。
曾幾何時,網絡文學大行其道,這似乎消解了語言的嚴肅性,同時,小說也就跟著衰落了。用郜元寶的話說,那就是“語言過剩”了。“開放的社會最不缺的東西,或許就是語言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作家寫作時必定有許多紛至沓來的語匯和語法誘惑著他,有許多語言的碎片在他周圍漫天飛舞。但是,在這種語言氛圍中,并沒有他最親近的語言。他奮力謀求個人語言的某種整體性效果,留給讀者的卻往往是極易解散的語言堆積物。語言太多了,好語言太少了”(郜元寶《眺望語言》)。
“五四”前后,雖然很多作家反傳統,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們的語言是浸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他們的成長是根植在濃厚的中華文化土壤中的。就如林語堂、沈從文、魯迅等人,西方漢學家很認可他們,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漢語底子很厚實。直到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作家們基本上還是尊重語言的,此后不知何故作家們對語言的敏感性慢慢地喪失了。像余華寫《活著》時,他把漢語的體味帶進了小說里,《活著》自然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但是到了《兄弟》、《第七天》時,余華的語言也開始顯得很粗糙起來,這或許是余華被不少讀者批評的一個因素吧。
海德格爾在《語言就是語言》中說,語言就是語言這句為邏輯學家所不齒的“同義反復”,昭示我們以全新的思考,回到語言本身,這便是回到此在同存在的融合。語言作為一種存在,它自有其自身所具有的狀態,比如,語言的概括性、語言的真實性、語言的氣質等等。另外,中國的漢語,其實一直有民間性和殿堂性,兩者無優劣之別,都是漢語最本真的一種狀態。比如,莫言的《紅高粱》等小說,語言就很放肆、充滿鄉野味,而畢飛宇的不少小說,語言則很華貴,簡潔明了。
再好的大師,面對真正要寫的一部小說時,如同女人生孩子——你無法掌控你生的孩子是否如你想像的完美,是否是健康的,這就是小說的魅力。雖不可控,但語言的力量和作用卻是至關重要的。
第四是詩性。文學是想像的藝術,如果太滿,回味的空間不大,會使得小說的藝術感下降。在小說中,詩性和意境相通。
意境是我國傳統美學和藝術理論的概念,主要用于詩論和畫論中。近代學者王國維借鑒西方文藝理論,對傳統觀念加以闡發,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被認為是意境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在《人間詞話》開篇就提出“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把“境界”即意境,看作創作的審美最高標準。他說:“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指出了意境所應具備的鮮明生動性和藝術感染力。他還從創作原則、情感色彩等方面論及意境的分類等問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在小說創作上,意境和詩性也尤為重要。作家曹文軒這樣總結:“作為文學之一種的小說,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精神形式,它的特色就是采用隱蔽的方式去呈現現實,而它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的隱蔽——就是因為使用了隱蔽的手法,才生成了一種叫‘小說的精神形式。……只要是一種被稱為‘小說的精神形式,就肯定要使用這一手法——這一手法是它的必備手法——它甚至就不是一種手法,而就是小說本身”(曹文軒《小說門》)。
在詩意的提煉上,老村的《騷土》值得贊許。比如他對鄉紳鄧連山上吊的描寫——“告密者的確是鄧連山。這事后來為人知曉。鄧連山做好人不成,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冬某日,在村東高崖上的柿樹自縊身亡。首先看見的是早起上學的碎娃。紅彤彤的太陽將高崖上的柿樹和懸掛的尸首陪襯得十分美麗,像是一副精致的剪紙……”這一意象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典型。在對鄧連山的塑造上,老村完成了對所處時代文學描寫中鄉紳這一典型形象的超越。鄧連山在《騷土》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從他命運的變遷上,可以看出中國式鄉紳的悲情色彩。而在莫言的《蛙》中,蝌蚪給杉谷義人的第一封信里,有這樣幾句話:“正月二十五那天,我家院里那株樹形奇特而被您喻為‘才華橫溢的老梅,綻放了紅色的花朵。好多人都到我家去賞梅,我姑姑也去了。我父親說那天下著毛茸茸的大雪,梅花的香氣彌漫在雪花中,嗅之令人頭腦清醒。”這亦是莫言以老梅開花來暗指寬容,對姑姑的寬容、對歷史的寬容。老梅開花這一意象,給莫言的創作帶來了震撼,亦是《蛙》的魅力所在。
在小說創作中,所指要及物,不能言而無物,但也不應實得過頭,恰當地留白,小說才會具有張力。
第五是歷史感。優秀的小說應該具有比較強大的歷史感。所謂歷史感,我認為相當于我們所說的生物的DNA,你看不見它,但它卻構造了你,是文學千古不變的一條主線。
當然,小說的歷史感不等同于歷史小說。歷史小說是小說的一種形式,它以歷史人物和事件為題材,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的生活面貌。那什么是小說的歷史感?“批評家張艷梅曾經有過很好的解說:‘歷史感到底是什么?寫歷史,不一定有歷史感;寫現實,也不一定沒有歷史感。歷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場,是細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質探求。一句話,要想使自己的長篇小說顯得雄渾博大,擁有突出的‘歷史感,就不能僅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層次進行浮光掠影淺嘗輒止的掃描,就必須以足夠犀利尖銳的思想能力穿越表象,徑直刺進現實和歷史的縱深處方可。”(王春林《2013年長篇小說:“70后”作家克服歷史感不足之局限》)如何才能使小說具有歷史感,程光煒給出了答案,他說,要使小說有歷史感,應和傳統接軌。“我們都知道艾略特有《傳統與個人才能》這篇杰出的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優秀的作家只能在‘偉大傳統的軌道上實現自己的才華,沒有一個人是能夠脫離本國傳統文化而取得藝術成就的”(程光煒《當代小說應如何面對文化傳統》)。
謝有順在《小說是活著的歷史》中認為,小說是關于生命的敘事,也是一部活著的歷史——生命與歷史的同構,是真正的小說之道。借由小說的書寫,當下、此時可以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也能成為永恒的歷史景觀。所以說,小說的歷史感,并不在于說一定要寫歷史。比如,張怡微的中篇小說《試驗》,寫的是當下的上海最平常的家庭和人,但她筆觸深處是寫計劃生育推行數十年后,各種因意外或不愿意結婚的獨生子女們,嘗試用各種方式相互取暖。小說雖寫現實,但卻有歷史的縱深感。而劉震云的《溫故1942》、張浩文的《絕秦書》等,也都是極有歷史厚重感的佳作。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前代文學往往是后來文學的滋養,或者作為進一步創造的‘材料,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是在話本、講史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紅樓夢》與《金瓶梅》有著密切的演進關系;《聊齋志異》說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與前代志怪小說、唐人傳奇,一脈相承;其文學語言的典雅、簡潔,兼有駢文和古文的優長。戲曲如《西廂記》、《長生殿》,更是《會真記》、《鶯鶯傳》、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長恨歌》、《梧桐雨》的新變,脫胎于前代而獨具自家面目,是戲劇史上的典范”(雷恩海《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學的價值》)。要使小說具有歷史感,深耕文化傳統,在傳統中汲取資源,乃是最佳之道。
第六是經典性。所謂經典,就是放在任何時代,它依舊能掀起大風暴。如莎士比亞之于英國和英國文學,魯迅之于中國文學,他們的經典都遠遠超越了個人意義,上升成為一個民族,甚至是全人類的共同經典。所謂小說的經典,應該暗合時代的基本面,反映時代最本質的包括社會和人的各方面特性,并為后世了解此前的社會提供必要的文學范本。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它是那樣深邃而明晰地反映了一個特定時代中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當然,重要的還是它再現了那個時代最本質的社會景象。
賈平凹的《廢都》出版后,一度引起巨大爭議。但作者顯然對作品的經典性有著自覺的追求。《廢都》通過大量的性描寫,將以莊之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虛無、頹廢等世紀末的精神廢墟景象很好地表現出來,小說也證明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在理想上的崩潰,信念上的荒蕪。“小說所寫到的備受爭議的性苦惱,其實也是精神危機的一個寫照,因為現代人精神空虛之后往往會用性的放縱來填補。”謝有順認為,“但多年之后,我們必須承認,這是本重要的小說,它生動地寫出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價值迷茫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參見李培《專家:〈廢都〉是當代知識分子的鏡子》)。
博爾赫斯在《論經典》一文中說,所謂經典著作,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或一段很長的時間決定閱讀的一本書,仿佛在這本書的書頁之中,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簡直就如宇宙那樣博大,并且一起都可引出無止境的解釋。([阿根廷]豪·路·博爾赫斯《作家們的作家》)
可見,真正有生命力的經典,是能經得住反復解讀的。具體地說,經典小說應該在以下方面有出色的表現:①以“故事”為最重要的要素;②浸漬于人性之中;③包含哲學意蘊;④富于獨特的語言魅力;⑤超越時空。(胡德才:《當代文學經典應有的特征》)
從胡德才對經典的概括看,幾乎包括了我在上述已經論及的故事、人物、語言等諸多方面。小說能在這幾個面上做好,已屬不易。但要達到最好的狀態,我以為,光靠這幾點還差點火候,這就是為什么我僅僅將經典性作為優秀小說標準之一。因為還有比經典性更為深層的要素,比如拙樸和渾然。
第七是拙樸。這是一個古代詩學概念。語見北宋陳師道《后山詩話》:“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樸,質樸,樸素。拙,粗糙未經雕琢,《老子》“大巧若拙”之謂。作為一種藝術風格,“樸拙”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美,因而對后代頗有影響。明代詩論家謝榛《四溟詩話》說:“千拙養氣根,一巧喪心萌”,主張“返樸復拙,以全其真”。又說:“詩惟拙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把“樸拙”與內心之“真”聯系起來,因而獲得了新的內容。“拙樸”的本義是怎樣的呢?拙樸指的是敦厚和樸實。“拙”指不靈巧,不靈活。從造字來看,“拙”以“手”作偏旁,所以和勞動有關。許慎《說文解字·手部》解釋“不巧謂之拙”。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拙”:“不能為技巧也。”《廣雅》:“拙,鈍也。”《墨子·貴義》:“不利于人謂之拙。”《抱樸子》:“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這里的“拙”指為人或做事粗劣,不精巧,當然也可以引申為質樸無華。“樸”本義指的是沒有細加工的木料,比喻不加修飾,有樸素,質樸的含義。《說文解字》:“樸,木素也。”在語義上,“拙樸”指的是事物敦厚古樸的質地(參見高陽《水墨畫風格與拙樸論》)。
中國早期的一些文學故事,譬如《山海經》里的精衛填海,譬如源自民間傳說的牛郎織女,初聽,既樸又拙,但是它具備一種穿透時空的特質。中國小說,深受西方之影響,一個世紀前的“小說界革命”,使中國小說的創作陷入了困境,大家攀比著炫耀技法,什么無主題寫作、零度敘述、魔幻現實主義、暴力美學等,充斥在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可以說當代作家大多很聰明,但也失卻了“拙樸感”,更少有天真之趣。但其實,小說寫“笨”一點未嘗不好,少些對技巧的追逐,多些踏實,自有別樣的美。
第八是渾然。渾然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文學的渾厚依賴于作者氣養的渾厚,這種渾厚之所以名曰渾厚,因為作者的情思不是在個人感受范圍內兜圈子,而是與社會、國家、個人,乃至自然宇宙的渾然歸一。武漢工程大學外語學院教授李利民在《論盛唐氣象的渾然美》中,從盛唐詩歌著手,論述了盛唐詩歌的渾然美。李利民認為,盛唐詩歌之所以具有渾然美,乃是因其境界渾灝、氣勢渾雄、風神渾逸、意境渾融、氣格渾雅、語言渾成。渾然美,是盛唐詩人氣養達到渾然境界后,在詩歌領域表現出來的總體特征。李利民分析認為,這主要是三方面原因所致:一是元氣的混沌狀態是對人精神修養的范本;二是儒家和道家的渾然境界,是對人精神理想修養的兩個主要目標;三是盛唐時代的渾然氣象,反映的是人類理想通往現實的橋梁。(李利民《論盛唐氣象的渾然美》)
從李利民的分析不難看出,當下中國小說家為何難以創作出具有渾然美的小說。從作家的層面看,渾然是一種大的社會氣象,乃至于成為某些作家最終的精神構成,當下即便有幾個真正有追求、脊梁骨硬的作家,但離蔚然成風,顯然還有相當的距離。相反,在物質主義的壓榨下,時下軟骨癥、精神侏儒癥遍地皆是,要想出現那種詩意的渾然美來,便尤顯艱難。不單單作家,整個社會也陷入了一種虛無狀態,先前儒家和道家的渾然境界,在當下社會里已經喪失殆盡,歷史殘剩的丁點兒輝光已很少得見。人不聚氣,修養達不到,自然無法創作出具有渾然美的小說來。
這八個向度,或許不夠完備,但我以為卻是好的寫作者、好的作品,應該具備的文學狀態。只有聚焦在小說的文學性上,中國的小說才會有更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