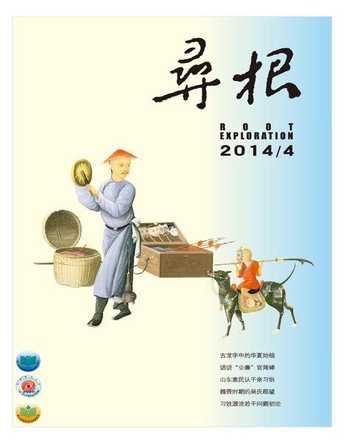道家智慧:歷史深處的心靈呵護
孫恪廉
在當今社會,怎樣面對物質(zhì)發(fā)展帶來的潛在危機,避免“虛無主義”的到來,已經(jīng)不僅是尼采以來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是我國不能回避的一個潛在問題。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勢頭強勁的“人為物役”的趨向。這種“物役”狀態(tài),與莊子當時的憂心,雖形式不同,但本質(zhì)無異,都表現(xiàn)為心靈自由喪失的一種精神性衰竭。
“人為物役”:遠超莊子的預(yù)想
現(xiàn)代工業(yè)和科學(xué)技術(shù),即所謂“技術(shù)理性”,共同構(gòu)成了推動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的基本動力。啟蒙運動以來,科學(xué)方法的運用及其在財富創(chuàng)造上的巨大成就,產(chǎn)生了新的迷信,即以為,人類越是追隨理性就越能獲得成功,并促成了理性誘惑與物質(zhì)誘惑的天然聯(lián)姻,日愈強勁地擠逼著人們的精神領(lǐng)域。
外部“必然”的物質(zhì)力量造成的精神性死亡,讓人想到的已不僅是將人淪落為機器部件的泰勒制。今天,科學(xué)技術(shù)獲得爆炸式的發(fā)展,電子郵件已不再是軍事工具,登錄互聯(lián)網(wǎng),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們在數(shù)分鐘內(nèi)即可取得聯(lián)系。電腦從昂貴、笨重的主機到伴隨芯片革命進入了尋常人家,從手提電腦、掌上電腦到無線上網(wǎng)、3G、4G手機上網(wǎng),微博、微信又把我們帶進一個“無微不至”的時代。各式名牌和時尚的翻新頻率不斷加快,讓人目不暇接。過多的信息使人們一時間難以承受,也無法做出恰當?shù)倪x擇。2013年“雙十一”節(jié)一天之內(nèi)的網(wǎng)上交易有350多億元人民幣,電子商務(wù)取代傳統(tǒng)商務(wù)似乎已成趨勢。人們在沉溺一切的信息(符號)海洋中隨波逐流。
結(jié)果,消費成了生活目標,形成消費社會。生產(chǎn)裝配的流水作業(yè)線、刺激消費欲望的無孔不入的廣告、購物按揭分期付款,此三者把當今社會的人們帶進了如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博德里拉所說的“一個被物所包圍、以物的大規(guī)模消費為特征的消費社會”。在這個社會,不是生產(chǎn)決定消費,而是消費引導(dǎo)生產(chǎn),生產(chǎn)什么、生產(chǎn)多少完全由消費者的需要所決定。人的社會角色從“生產(chǎn)主人公”轉(zhuǎn)變?yōu)椤跋M主人公”,消費享受從作為人時刻要爭取的“權(quán)利”轉(zhuǎn)變?yōu)椤肮窳x務(wù)約束機制”。博得里拉認為,客體(信息、媒體、商品等)已經(jīng)超越了它們的界限,逃出了主體的控制。不僅如此,在他的《宿命策略》中,博德里拉暗示,在新的高科技的社會中,客體已經(jīng)取代了主體的地位并主宰了不幸的主體。帶著些許嘲諷,博德里拉建議自我應(yīng)當向客體世界投降,并放棄主宰客體的計劃。
其實,這不過是博德里拉對物化憂心的一種激進表達而已。今天,馬爾庫塞提示的只有物質(zhì)向度的“單面人”沒有減少,反而呈現(xiàn)出日益加重的人的“物化”趨勢,沒有精神一維而只有物質(zhì)這一維的孤獨的消費者,熱衷于被廣告煽動的虛假的消費,形成了羅蘭·巴特爾《神話學(xué)》一書中所批判的那樣狀況,把虛假的消費與永恒的“人性”相聯(lián)系,各種廣告、形象、類象渲染出這種聯(lián)系的“天然感”。用后現(xiàn)代學(xué)者布迪厄的話來講就是,你屬于哪個階層,不在于你擁有什么、創(chuàng)造了什么,而在于你消費了什么。消費成了人的價值的確證,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唯一追求和終身志趣。
生活節(jié)奏變得更快,也更無目標。T.S.艾略特的話值得玩味,他說:沒有宗教便沒有文化,今天的文化不成其為文化,就是因為沒有了宗教。資本主義是個世俗化的社會,并不直接由宗教價值觀形成。因此艾略特認為資本主義沒有文化。顯然,艾略特并不是在玩幽默,艾略特曾說,拯救必須經(jīng)歷精神上的磨難,即對死亡的焦慮和恐懼,晚年的他很富有宗教意味。另一美國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魯克通過美國近30年的物化的對比,以一個沉重的問題作為他一部新作的書名:《美國人何以如此郁悶》。
悟性與理性的互濟互補
老莊思想集中體現(xiàn)了東方悟性主義的思想方式,它與西方理性主義大異其趣,卻又相得益彰,把我們對自我的認識引向開闊廣袤的思維空間,尋覓到人類精神的另一瑰麗綻放。
技術(shù)理性無助于個體心靈。在西方,不管是傳統(tǒng)基督教的理性實體論,還是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或自然神學(xué),把人生是否有意義理解為是否與必然性相符合,實際上都取消了關(guān)于人的重要問題,即愛與善、有限與無限、拯救與超越等人生的深沉關(guān)切問題。畢竟,理性自身并不能賦予世界、人生以意義。世界應(yīng)該是怎么樣,自我和人類應(yīng)該是怎么樣?對于這些與人生有關(guān)的終極價值信念問題,理性本身并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盡管理性可以極大限度地在物質(zhì)上膨脹人類的力量,但對于個體心靈世界的建構(gòu),幾乎無處著力,因而乏善可陳。當代偉大物理學(xué)家埃爾文·薛定諤雖然在科學(xué)上的成就令人仰止,但他并未陷于理性崇拜或者說科學(xué)迷信的泥淖,他說:“科學(xué)給予我周圍世界的圖像是非常欠缺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只敘述事實的信息,將我們的一切經(jīng)驗都放置在一個嚴密的秩序之中,這個秩序固然宏偉,但它對于一切真正接近我們心靈、對我們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事物,則是可怕的緘默。”
在理性緘默的地方,方顯出道家智慧。《道德經(jīng)》中開宗明義的第一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似乎就明示了語言與理性在探索宇宙、人世、自我真諦過程中其作用的有限性。由于“道”具有超越語言的性質(zhì),因而,在道家“與道合一”或“與道逍遙”的意境中,很少看到邏輯推理、理性思維的套路。如果借用西方哲學(xué)話語,更多看到的是采取反理性主義或者非理性主義的語調(diào)來運思行文。在老子,是以“玄之又玄”的方式,以期探尋道的奧秘,開啟眾妙之門;在莊子,則是在自然的大背景下以隱喻、借喻、轉(zhuǎn)喻等詩化寫作方式來表現(xiàn)逍遙游的人生至境。這種“另類”于邏輯的思維方式,已然接近宗教智慧了。莊子似乎認定邏輯話語難以把握和再現(xiàn)“自然的簫聲”,反而可能磨滅自然有機體的多樣性,將自然個體細微差別單一化。在這里,不由使人想到西方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對理性批判所表現(xiàn)出的非理性特征。的確,理性的抽象,只會破壞莊子筆下存與滅、生與死、夢與酲的靈動變化;理性的反思,不可能賦予人們以曠達包容的澄明心態(tài);理性的推理,不可能給人推出恬淡適意的心境。而這些,恰恰是處于變幻不居、寵辱不定的人們最需要的。克爾凱郭爾的話意味深長:“人們是多么沒有理智啊!他們從未運用他們所擁有的自由,卻要求他們并不擁有的;他們有思想的自由——卻要求言論的自由。”他甚至說:“我寧可與孩子們談話。”無獨有偶,老子將德行高尚的人比為“赤子”,即嬰兒。老子寫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jù),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道德經(jīng)》第五十五章)
此外,道家悟性的“主客互泯”,是對西方理性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積極補益。
在道家看來,只有超越任何分區(qū)、當然包括超越主客二分,才能認識“道”。在抹去自我的一切個別性東西的“主客雙泯”狀態(tài)下,于“絕慮忘緣”的空靈中達到與道合一。“道”雖是可以說的,但說出來了,就不是那恒常的“道”了。只有那個無分別的狀態(tài),才是天地的本源,即所謂“無,名天地之始”(《道德經(jīng)》第一章)。正因為如此,只有回到恒常而無分別的狀態(tài),才可以觀看到道體的奧妙;而經(jīng)由恒常而現(xiàn)出分別的跡象,便只可看見道體的表現(xiàn),以老子的話來講,即是“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道德經(jīng)》第一章)。這里的“徼”,可以理解為道的現(xiàn)象、端倪或外表。如果沒有對種類分別的超越,偏執(zhí)一端,那也就無所謂“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了,即是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道德經(jīng)》第二章)。天下人都執(zhí)著什么是“美”,這樣就無所謂不美了;天下人都執(zhí)著什么是“善”,這樣就無所謂不善了。可見,之所以應(yīng)當超越一切分別,避免偏執(zhí),就在于所有的分別、差異是相互依存的:“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道德經(jīng)》第二章)。所以,圣人用“無為”來處事,以“無言”來行教。盡可能地淡然處理萬物之間的主客分別、貴賤優(yōu)劣,方有可能接近于道。否則,只能看見道的末端表征,并因為高低分別而招致紛爭不斷。為此,老子提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道德經(jīng)》第三章)
當全社會都在不遺余力地將“更高、更快、更強”作為個體生命無可爭議的價值取向時,原來在悠遠的過去,對自我心靈還有看似“另類”智慧的安排,給今天浮躁的人們留下的一項構(gòu)建心靈驛站的社會方案。安頓自我,是主“靜”,還是主“動”,因人而異,彼此之間亦無優(yōu)劣高下之分。然而,這卻向人們展開了選擇的另一維度,并拓寬了奔向“更高、更快、更強”的預(yù)跑空間。
水泥森林深處的一縷新綠
在幾乎物質(zhì)統(tǒng)治一切的社會條件下,只要敞開中華文化的精髓——老莊道家文化,就能在鋼筋水泥森林的灰色深處發(fā)現(xiàn)一縷新綠,于浮躁與浮動的迷惘中,重新感悟到人生的另一極——淡定與超然。
在跨入現(xiàn)代社會門檻的中國,不難看到遠遠超出人的生存需要的畸形消費,就如手機更新?lián)Q代的頻率急劇加快一樣,在加速耗損資源的同時(比如欲從3G“進步”到4G,必須淘汰3G手機),人們也在加速跨進一個物質(zhì)充實、精神空虛的消費社會。我們一不小心便陷入看似主動、實則是被廣告煽起的永不饜足的消費潮流之中,有道是“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經(jīng)》第十二章)。然而,生命不是商品,這個世界并不是一個消費的天堂。我們不能為所欲為地搶購和掠奪。
物極必反,在“產(chǎn)能過剩”的今天,人們?nèi)找婵粗貙凫`的自我。實際上,物質(zhì)上帶來的快樂,無論肌膚之樂,還是口腹之樂,稍縱即逝;電腦、轎車能帶來方便和舒適,但帶不來心靈寄托。當物質(zhì)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時,幸福感再也不可能通過盤子端上桌面。相反,物欲化、技術(shù)理性對人的壓制等現(xiàn)代性的弊病也逐漸展露,無意義感、虛無感就將凸顯。在只管掙錢消費的職場領(lǐng)域,人們陷于饕餮般消費快感之中,對于終極關(guān)懷、超越價值,要么遺忘,要么漠視,乃至于輕嘲蔑視。結(jié)果是,把生命擲入“無聊”加“痛苦”的往復(fù)循環(huán)之中:當物欲未滿足時,感到痛苦;滿足后,又感到無聊。人們已經(jīng)隱約地注意到,幸福是心靈的,因為人在本質(zhì)上是屬于精神的。怎樣拓展自我的精神空間,走出經(jīng)濟動物的“非人”狀態(tài),日益成為空靈而虛靜的自我?正是這一文化追問,所以,道家文化在日益廣泛的層面重新回到生活世界。道家看重空靈、淡定之境,放空心靈,強調(diào)“虛其心”“弱其志”,以“無為”而“無不為”,在“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大自由中,領(lǐng)受精靈妙透的人生至境。
“致虛極,守靜篤”(《道德經(jīng)》第十六章),才能達到自我與自然和合統(tǒng)一。抵達這一境界的路徑,不是依靠邏輯推理,如果執(zhí)著于此,弄不好“機關(guān)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絕學(xué)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老子認為,要極力地回到虛靈的本心,篤實地守著寧靜的元神,就能夠回復(fù)到自家生命本源。“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fù)。夫物蕓蕓,各復(fù)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復(fù)命。復(fù)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道德經(jīng)》第十六章)“清靜無為”“恬淡寡欲”是老子的人生態(tài)度,為此,他特別看重致虛守靜的功夫。從“致虛”“清靜”“歸根”“復(fù)命”“知常”直至“沒身不殆”的遞進次序看,老子把“致虛”視為修身的前提。“致虛”是要人們排除物欲的誘惑,回歸到虛靜的本性,進而在完全虛靜的狀態(tài)下“歸根”“復(fù)命”,回歸到一切存在的根源,這樣才能認識“道”。司馬遷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太史公自序》)
老子“虛靜”“無為”的思想,表現(xiàn)為莊子關(guān)于人的真實自我在自然主義的回歸之上。莊子以為,自我的拯救之途、立命之所,不在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分別,而在于天地自然中實現(xiàn)自我與“道”和諧共處;道家尊奉的人生的價值,不在于“修齊治平”與道德功名,而在于精神的獨立與自由。有道是“君子謀道不謀官”,即所謂“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教在道家基礎(chǔ)上進一步認為,世俗的一切得失、功名、榮辱都微不足道,故它能夠超脫凡俗,不食人間煙火(辟谷),清凈寡欲,煉氣食丹,最終實現(xiàn)長生久視、羽化升天。實際上,道教是改造了道家的思想,把道家追求與道合一、與道逍遙改變?yōu)榈玫莱上桑馍聿凰馈5兰也⒉徽J為肉身可以成仙,它以精神不死為人生目的。要實現(xiàn)這一理想,必須灰身滅智,去掉一切帶有個別性特征的東西,即“坐忘”,不落言筌理障,留下一個純粹的心性與“道”相融合,并過程化為“精氣神”的修煉程序。
道家要求人們的行為要順應(yīng)自然,清靜無為,無欲無爭,以保持純樸的本性,超越主客對立,了悟“物我同根”,實現(xiàn)“天人合一”。外圓內(nèi)方,是中國知識分子欲塑造的理想人格,表現(xiàn)于安身立命上,總是外儒內(nèi)佛,或者外儒內(nèi)道,或者佛道兼收。一部電視劇《三國演義》,讓人們對明朝狀元楊升庵的“滾滾長江東逝水”耳熟能詳,辭章中的寥寥數(shù)語,便不難于虛寂之境中領(lǐng)悟到濃郁的禪理道機。“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面對人世的滄桑與炎涼,歷朝歷代,不知有多少宦海官場的折戟者、科舉考場的落第者,正是道家以高邁、超逸的態(tài)度,給這些數(shù)不盡、說不完的絕望心田,澆灌了多少心靈甘露。如若沒有道家這般灑脫,我們看到的舊時知識分子,要么是《儒林外史》中的范進,要么是魯迅筆下的孔乙己。
市場化改革取得了輝煌的經(jīng)濟成就。但是,只要是市場化,“利潤最大化”就是鐵的規(guī)律,它可能成為失去韁繩的“野馬”,奔騰到經(jīng)濟之外的其他領(lǐng)域。如果,天下熙熙皆為利趨,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那么,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難免出現(xiàn)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可人心偏偏不是這樣,在紅塵滾滾中,耀眼地閃動著商品拜教情節(jié)。今天,我們談老莊哲學(xué),已不再是“坐而論道”。殊不知,在物欲膨脹、精神萎縮的情狀之下,對于老莊思想的當代價值,無論怎樣高估都不過分。
繼馬克思之后,物化的問題,也是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核心問題,他們憂心于人們主體性的衰落,擔心人類被物化,變成物一樣的東西。遙想20世紀80年代,薩特等西方理論在中國大學(xué)校園紅極一時,我們沉醉在各種妙語睿智之中,一時間,似乎都成了拿來主義者,熱情洋溢、如饑似渴地閱覽西方哲學(xué)書籍。然而,在異域思想世界經(jīng)歷了多年的漫步,驀然回首,原來,在燈火闌珊處,讓人心動的,早已在那歷史深處呵護多年。真正的拿來主義不會數(shù)典忘祖,也不會舍近求遠、無視現(xiàn)代化處境中的道家的不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