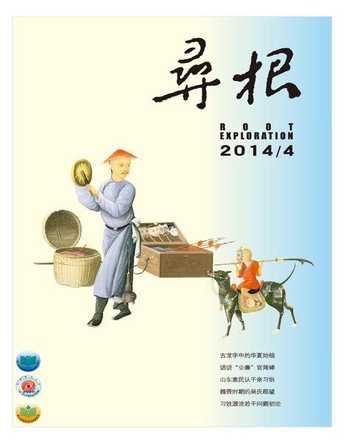安徽會館百年紀及期待
劉辰
清末安徽省府州縣在北京有會館30余處,以安徽省館最大,也稱安徽會館。它位于北京宣武區(qū)后孫胡同北側,始建于同光年間,占地約10000平方米。歷經150余年滄桑之變,至今其部分建筑猶存,依稀保持著清末的格局。1984年,會館戲樓被列入北京市第3批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年底,戲樓一度險遭拆毀,幸得北京專家學者緊急呼吁乃得幸免。2000年前后北京市文物局對戲樓等主體建筑進行了修繕。2006年被列入第6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北京市游覽景點之一,但會館的大部分建筑至今仍未修復。2005~2006年間,安徽的學者、政協委員曾多次呼吁修復安徽會館,徽商集團集資8000多萬元,在省政府的支持下,派小組駐京專門聯絡修復事宜,惜未達成一致意見。安徽會館的百年創(chuàng)傷何時能愈?會館期盼各界人士繼續(xù)給予更多眷顧。
會館之興建
北京安徽會館是皖籍官員集資興建的同鄉(xiāng)會館。清同治五年(1866年),皖籍京官吳廷棟等75人因安徽在京無省級的會館,發(fā)起建館之議,得到湖廣總督李翰章、直隸總督李鴻章的支持。其時淮系勢力正熾,李氏一呼,和者百應。到同治七年,共有154人捐銀33500兩。乃公推內閣學士江人鏡總其成,陸續(xù)購得后孫公園周邊房宅加以改建,同治十年基本建成。后又有同治十一年、光緒八年(1882年)兩次擴建,光緒十五年五月火災后重建,更臻完備。
據《京城安徽會館存冊》記載,同治七年十一月,用銀3000兩購得后孫公園胡同路北司氏磚瓦大房一所,共有房產80間,經修建后成為安徽會館中院及后花園。同年十二月,用銀2200兩購得路北李張氏等住房一所,前后統計房屋72間半,設施完好,修建后成為會館東院。同治八年十一月,用銀578兩,購得興勝寺口內路西湯氏住房一所,有灰瓦屋25間半,整修為會館車場。同治十一年擴建,用銀950兩,購得后孫公園胡同路南許氏坐南北向房一所,有瓦房29間。光緒十年第二次擴建,用銀6500兩,購得后孫公園胡同西頭路北王氏住房一所,計房39間,改造為會館西院,主要用于出租。至此,會館主體部分的規(guī)模和布局基本形成。 光緒十五年,西鄰泉郡會館燃放鞭炮,引起安徽會館西院起火,大火依風張勢,烈焰沖天,延至中院、東院半成焦土,會館建筑燒毀十之六七。時皖籍京官孫家鼐、方汝紹、陳同禮、江昌燕等聯名致信李鴻章,迭請盡快修繕。又得李鴻章等淮軍將領公捐銀1萬兩,各省皖籍官員續(xù)捐萬余兩,至八月初六,總計捐2.5萬余兩。乃委候補知縣張廣生董率工役重修,翌年八月告竣。不僅“重復舊觀”,乃得“益臻美備”。
會館既為皖籍京官聚會、團拜、居留之所,又建于淮系方熾之際,自然流露出特有的氣派。據《京師安徽會館存冊》及其所附京師安徽會館圖說看,建成后的北京安徽會館主體部分坐落在后孫公園路以北,有東、中、西三座庭院,中間以夾道分開。夾道間開門,將多座院落連為一體。中院5進,南端為大門,面闊5間,有文聚堂、戲樓、神樓等建筑,房屋75間。東院3進,是鄉(xiāng)賢祠,有奎光閣,思敬堂、龍光燕譽等建筑,房51間。西院為留賃住房,3進49間。北面是花園,有假山、亭閣、小橋、池塘。總共有房屋165間。重門疊院,亭臺樓閣,園林山水,冠于一時,規(guī)模雄踞北京各省會館之首。
安徽會館的前身后孫公園,原為明末清初官吏、著名史學家、方志學家孫承澤的故居,清初已經頗具規(guī)模。公園分前后兩部分,南面前孫公園是主宅,以北后孫公園是別業(yè)。孫承澤字耳伯,號北海、退谷。崇禎進士,官刑部給事中。李自成進北京,孫投井自殺,為家人救出,“吐血水斗余”得生。后出為清吏。據王崇簡《孫公承澤行狀》等文記載,他習掌故,精鑒賞。平生無聲色之好,嘗貯古器及名人字畫,與客談經史之余出以為娛,負當世盛名,四方士大夫樂從之游。交顧炎武、吳偉業(yè)、王崇信、朱彝尊、王鐸、錢牧齋等著名學者。孫承澤于順治十一年休致,康熙十五年去世。其間20余年目不釋卷,著述有40余種,其《天府廣記》《春明夢余錄》等為時所重。后孫公園是他與文人聚會的地方。
維新變法的策源地
1895年甲午戰(zhàn)敗,康有為、梁啟超聯絡各省進京應試的舉人1300余名聯名上書請求變法無果,決定留京師廣造變法輿論。經會館管理人大學士孫家鼐租得會館一部分,在這里發(fā)起強學會,致力辦報、譯書、集會,意圖改變社會風氣,推進變法,這里遂成為戊戌變法的策源地。梁啟超曾敘其原委說:“當甲午喪師以后,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fā)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遂在后孫公園設立會所。”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萬國公報》在安徽會館創(chuàng)刊,由康有為發(fā)起,梁啟超、麥孟華撰稿,當時無自購機器,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板雕印,日刊千份,由送京報人隨《宮門抄》分送諸官宅。內容主要選登閣抄,譯錄新聞,推介西方政治、社會、文化、科學知識,辦報月余居然每日可發(fā)出3000張。“朝士日聞所不聞,識議為之一變。”后將《萬國公報》更名《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機關報。強學會又邀集士大夫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同時編售西書,購買儀器書籍,為辦新學作準備。南洋大臣張之洞寄5000金以充會用。安徽會館一時成為維新人士活動的中心。會館還與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創(chuàng)建有關。梁啟超在《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講詞》里談及北京大學的發(fā)端時稱:“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于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之知識于我國民。且于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焉。”1918年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也認為,“本校造端,基于光緒二十一年之強學會”。這一點,從京師大學校創(chuàng)建的過程也可以得到證實。
1895年,強學會的活動引起保守派的強烈不滿。1896年1月20日,御史楊崇伊上疏極言強學會置黨營私,請敕嚴禁。強學會因之被封,圖書儀器皆被查抄。但當時改革思想已有不可遏制之勢,不久御史胡孚辰上奏書局有益人才,建議將書局改為官辦。清政府乃下令改設官書局,發(fā)還查抄的圖書儀器,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臣。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孫家鼐上《官書局奏定章程疏》,提出“擬設學堂一所”。此為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校最早的提議。
孫家鼐,安徽壽州人,咸豐間狀元,官至大學士,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列名強學會,傾向變法。光緒二十二年他提出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校的建議顯然承繼了強學會的宗旨。兩年以后戊戌變法,作為當時的新政措施之一,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亦由孫家鼐管理。故梁啟超說京師大學堂“之前身為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為強學會”。
近代國恥紀念地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德軍2000余人在安徽等處駐扎長達9個月。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罪行累累。仲芳氏在《庚子記事·洋兵進京逐日見聞紀略》中詳細地記錄了親歷、親見的事實。該書序言中說:“是書也,乃于亂世親經親歷,或見或聞,逐日記載,皆屬實事。待以承平之日樂以忘憂之戒也……光緒辛丑嘉平月仲芳氏記錄于宣武城南椿樹二巷寄寓叢桂山房之南窗。”仲芳氏留下的這筆“樂以忘憂之戒”,至今仍是值得國人認真汲取的。下面節(jié)錄部分記載:
庚子七月二十日,各國洋人襲
陷京師。
八月初八日,孫公園安徽會
館,琉璃窯并廠甸呂祖祠,均屯駐
洋兵,共兩千余名。附近各街巷,
洋人來往甚眾。各戶挨門搜查,索
掠衣飾財物無數。又在各處擄捉
行人,至營中與之拉炮、掮物、鋤
草、抬糧,非常苦累,直至夜半方
得釋放。無論貧富一概并捉,人心
惶恐,路少行人。
十三日,洋人搜劫,竟有帶同
二套大車數乘。在各胡同挨戶裝運。不獨細軟之物,即衣服、床帳、米面、木器無所不擄。在院則無所不到,在屋則無所不搜。家中人多者,尚有攜取數件而行,若家中人藏避,僅留一二人看守者,則任其打擄,至凈盡而后已。倏聞前街某家被擾,又聞后街某家被搜;將聞左鄰洋人才走,又聞右鄰進去洋人;自天曉至日暮,不下數十起,魂夢皆驚。
九月初五日,安徽館駐扎之統領,派兵在附近街巷,將行路良民與京官住戶擒獲數十名,誣為盜匪,非刑拷打,死而復生者數人。各家設法婉轉始得釋放。如此荼毒,人民何堪凌虐哉!(轉引自《北京安徽會館志稿》第50頁)
京劇發(fā)祥地物證
據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周華斌研究,北京會館是北京作為京劇發(fā)祥地的唯一實物見證。故該會館曾被列入《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中國戲曲志·北京卷))《北京名勝古跡辭典》,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重視。
京劇的形成與徽班的活動有直接的聯系。京劇形成在乾隆道光年間,發(fā)端于徽班進京。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80壽辰,閩浙總督覺羅五那拉命浙江鹽官把安徽三慶班帶入京都參加祝壽活動,戲班因而在京出了名,站住了腳。以后嘉慶、道光年間,陸續(xù)有四喜、春臺、和春班進京演出。徽戲與當時的昆曲及以后漢戲的聲腔、表演相結合,在北京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了京劇。四大徽班進京演出對京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這就是京劇史上有名的“徽班進京”。徽戲活動與會館的關系待考。
會館的守護者
同光年間,淮系將領多居要津,又兼皖省科名蔚起,人文盛極一時。會館建成后,自然成為皖籍將領活動的基地。李鴻章也曾在這里接見過朝鮮國的使者。會館有神樓供奉關圣帝君、閔子、朱子及歷代鄉(xiāng)賢牌位,每年三月初三祭文昌,五月十三祭關帝,九月十五祭朱子、閔子。這些皆有文字記載,所以也是了解近代鄉(xiāng)幫文化難得的典型。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度經駐京安徽同鄉(xiāng)選舉,組成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接管會館,負責人朱蘊山,為民革組織部長。1954年后會館移交北京市,住房多數變?yōu)槊窬樱@里也辦過小學、“萬人大食堂”、食品廠。居民們既是會館的占用者,也是保護者,盡管有不少的搭建、改動,且隨著年代日益破舊,會館框架終究得以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1994年,占用會館中路戲樓一帶的椿樹整流器廠計劃在12月6日到12日拆除會館舊建筑,改建幼兒園。這一消息被周華斌先生獲悉,他心急如焚,當即于12月1日致信北京市政協委員、著名史志學家王燦熾先生,說明安徽會館是明清時期北京著名史學家、北京第一個地方史志學家孫承澤的故居孫公園,又是清末淮軍將領重要的活動場所,是北京城區(qū)罕見的園林式建筑和北京作為京劇發(fā)祥地的唯一實物見證,請王燦熾委員緊急呼吁保護會館。王先生收信后十分重視,立即打電話到北京市文物局,建議緊急阻止拆建,同時向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員會提交一份緊急提案,請緊急阻止整流器廠的拆建行動。
20世紀末,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區(qū)政府決定逐步修復安徽會館,第一批工程計劃2000年年底完工,由北京市學者型企業(yè)家黃宗漢承擔。黃曾結合電視連續(xù)劇《紅樓夢》的拍攝利用制景經費按照《紅樓夢》的記述,建成了美輪美奐的大觀園。20世紀80年代中又集資3000余萬元修復了北京湖廣會館。在承擔安徽會館一期工程后,黃特約請王燦熾先生撰寫了8卷35萬字的《北京安徽會館志稿》。王先生引用古今大量資料詳細記述了會館的沿革、館舍、房產、經費、規(guī)章、古物、石刻、故跡。書成,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為之作序。這不僅為一期工程提供了重要參考,而且是研究近代會館文化變遷的一份極具價值的文獻。一期修復工程包括戲樓、文聚堂、碧玲瓏館等建筑。
2006年,會館終被列入第3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由于種種條件限制,會館的大部分建筑仍然待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