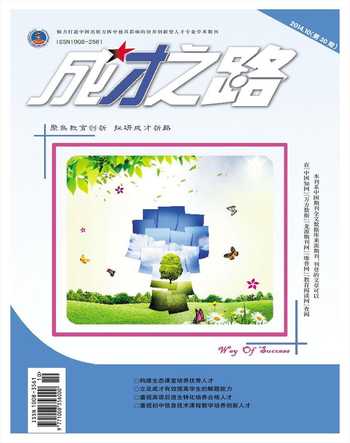中外教育家評介(連載)
張在軍
30. 克魯普斯卡婭
一、生平介紹
克魯普斯卡婭,全名叫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一生致力于研究馬克思主義教育科學,并做出了突出貢獻。
1869年2月26日,克魯普斯卡婭出生在俄國彼得堡一個破產的貴族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原是個舊軍官,因同情革命被革職,其母婚前曾任小學教師。
她14歲時,父親病逝。此后與母親相依為命。上中學時,受一位鄉村女教師的影響,對教師工作產生了興趣,中學畢業后當過一個時期的家庭教師。
1889年,進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專門學校學習。不久,加入了馬克思主義小組,大量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1891年~1896年,在彼得堡郊區的工人夜校當教師,向工人們宣傳革命道理。在此期間,列寧來到了彼得堡,她認識了列寧,并于1895年加入了列寧創建的“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
1896年被沙皇政府逮捕,與列寧一同流放到西伯利亞米奴新斯克州的壽山村。從此,她成了列寧最親密的戰友和助手。
1907年,流放期滿后,和列寧一起僑居國外。這時除了參加革命工作外,還考察了不少學校,研究了西方古典教育家的著作,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一書(1917年正式出版)。這是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的教育專著,得到了列寧的高度評價。
“十月革命”勝利后,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先后任副委員、委員職務。1921年,任成立的國家學術委員會主席,直接參與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科書的制訂、編寫工作和有關學校創建工作。
1929年,擔任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她是前蘇聯第一位教育科學博士學位獲得者。1939年2月,不幸逝世,享年70歲。
她一生發表了許多有關教育的演說和著作,出版過其教育文集11卷,我國也翻譯出版了《克魯普斯卡婭教育文選》等文獻。
克魯普斯卡婭把自己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所做出的不朽貢獻將永載歷史史冊。
二、教育思想
(1)論社會主義學校的教育目的。克魯普斯卡婭強調,不僅要把學校辦成讀書的學校,還必須辦成勞動的學校。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社會主義學校的特點,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教育要培養能“改造整個社會”的新一代,而不是像資本主義教育那樣,其“目的是把學生培養成為能享樂和統治的人”。這是社會主義教育與資本主義的最根本區別。
(2)論集體主義教育。克魯普斯卡婭認為,集體主義教育是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她說:“資產階級力圖把兒童培養成個人主義者……我們卻努力把我國的兒童培養成集體主義者。”個人主義者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他們與群眾對立起來;而集體主義卻將自己置于群眾之中,視自己為集體的一部分力量。
在談到培養集體主義精神與發展個性之間的關系時,她明確指出:“兒童的個性只有在集體當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發展。集體不會消滅兒童的個性,但能影響教育的性質和教育的內容。”
關于集體主義教育的實施問題,她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如要求學校、團、隊組織互相配合,一致對青少年實施集體主義教育,并提出了在幼兒園就開始實施集體主義教育等主張。
(3)論勞動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在《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一書中,她詳細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清楚地認識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僅是改造舊社會強有力的工具,而且也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她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少爺和游手好閑的人,學校應該教給兒童生活和勞動的本領。要讓兒童從小參加一定的勞動,受系統的勞動教育,培養勞動觀點和勞動技能,最好是參加集體勞動(貫徹集體主義教育思想 )。“十月革命”勝利后,她在改造舊學校的過程中,致力于由讀書學校向勞動學校的過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克魯普斯卡婭要求學校實施系統的勞動教育時,必須考慮學生的年齡特點及接受能力。1936年她提出了一個從一年級到十年級的勞動教育設想:一二年級的勞動以游戲和自我服務為主;三四年級的勞動具有生產勞動的性質;五至七年級的學生應進入實習工廠勞動;八至十年級的學生則與成人一起在工廠(或農場)勞動,這就要求勞動教育與綜合技術教育配合進行。
在她看來,實施綜合技術教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它不僅使學生了解現代技術原理,獲得一定的勞動技能,而且將來這些人易于適應各部門的勞動,成為“生產部門真正的主人”,進而增進勞動效益,加速工業化的進程。
(4)論學前教育、少先隊教育和校外教育。克魯普斯卡婭十分關注學前教育工作,將其視作國家的事業,視作國民教育體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并進行了前蘇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擴展學前教育機關網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幼兒園規程》《幼兒園教養員工作指南》等文件。
她是前蘇聯少先隊的組織者,號召“通過少年先鋒隊組織活動,廣泛地對兒童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使他們從小立志:長大后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她主張學校與少先隊有分工、有配合,強調少先隊工作要注意發展隊員有主動性、創造性和獨立性,鼓勵所有男女兒童都應參加少先隊組織,不得采取關門主義態度,不得把少先隊變成少數兒童的特權機構。
她也是校外教育活動的積極倡導者。她說:“校外工作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這種工作對正確地教育兒童很有幫助,它可以給兒童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為此,應該“盡一切力量來鞏固兒童技術站,組織他們參觀各個企業和電站……文化宮里應該辟出一個工作室,讓兒童在那里做他們想做的東西”。
(作者系本刊編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