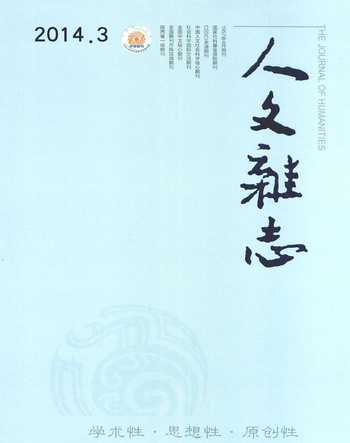經學統合完成于《五經正義》的歷史動因
張分田 張鴻
內容提要經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三教之爭的積極推動、中國統一的政治契機和制度創新的特殊需求是經學統合完成于《五經正義》的歷史動因。隋唐以前,沒有必須將經典注疏規范化的特殊需求,故歷代國學通行的做法是經學諸派共存并立,而隋唐以降,科舉考試需要統一的教材及考試標準,必須提供統一的經典文本及其注疏。因此,制度創新是經學統合的主要動因。中華帝制的統治者不以統一經學的方式維護思想統一,這種歷史現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關鍵詞《五經正義》孔穎達經學國學帝制
〔中圖分類號〕G25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3-0079-08
在隋唐,帝制國學及其國家學術從五經諸派時期,步入經學統合時期。孔穎達奉命主編的欽定經典注疏《五經正義》的問世是經學統合的歷史過程基本完成的標志性歷史事件。經學的統合與帝制的成熟是相互匹配的歷史現象。國家學術的重大進展意味著政治理論的重大進展。經學統合是隋唐政治思想史的首要篇章,而經學統合的淵源與動因又是隋唐時期思想傳承與演化的重要歷史背景。本文著重探究經學統合于隋唐的主要歷史動因。
一、經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學的統合是其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與必然結果,而完成經學統合的《五經正義》有其深遠的經學淵源。為了全面認識《五經正義》的形成原因和歷史價值,有必要先簡略地追述一下經學的歷史。
“經”字的本義是經緯之經,即織物之縱線,引申為常道、規范,因而“經”字很早便有了“常”、“道”、“理”、“義”、“法”等義項。在先秦,“經”可以用于指稱一本書的主旨、提綱、要點。后來人們往往將一些被尊為典范的著作稱之為“經”。不同的思想流派會尊奉不同的“經”。
廣義的經學,亦即傳授某些經典的學問,理應追溯到這些經典問世之時。在西周及春秋戰國,國學及各類官學傳授《詩》、《書》等典籍,各種私學傳授某些古代典籍,這都屬于廣義的“經學”范疇。先秦諸子常常引據春秋以前的典籍,他們對典籍的研修也應屬于廣義的“經學”范疇。但是,在古代文獻中,“經書”特指“儒經”,“經學”特指“儒術”,而“經藝”一詞既可以指稱“經書”,也可以指稱“經學”,還可以作為“經書”與“經學”的統稱。
以“經”特指“儒經”是帝制國學的產物。漢武帝崇“六經”,尊“儒術”,在太學設立《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漢儒將五經之學據為專利,稱“五經”乃“圣人之作”,為“五常之道”,并強調“經”字的“常”、“道”、“理”、“義”、“法”義項。于是“經”被賦予特定的內涵,特指皇帝欽定的“圣人之作”、“典誥之書”,“圣哲彝訓曰經”,由此而逐漸形成的“經、史、子、集”圖書分類方式,進一步強化了“經”即“儒經”的意蘊。因此,在古代文獻中,“經”通常特指帝制皇權欽定之“儒經”,故“經”亦有“帝典”之稱。
古代學者很少使用“儒家經典”的提法,就連“儒典”、“儒經”的提法也不多見,更沒有“儒家經學”的提法。導致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沒有必要刻意強調“儒家經典”,只需單用一個“經”字即可指稱一批據說由孔子等人編訂或撰寫的典籍。于是“經典”、“經籍”是“儒經”的統稱;“經傳”是“儒典”經與傳的統稱;“經義”特指“儒經”義理;“經訓”、“經解”、“經說”通常是指對“儒經”的傳注解說;“經師”、“經生”特指傳授經學的學官;“經筵”、“經帷”、“經幄”是指皇帝研讀“儒經”之處。與此相應,“經學”之“經”特指“儒經”。這些詞匯的特定內涵都是帝制統治者獨尊“儒術”的產物。
西漢以來,經學始終是官方學說及主流文化的主要載體,經學的分流與合流也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現象。導致經學分化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經典文本不同。漢代經典有今文經與古文經之別,如《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兩種文本多有篇幅與字句的差異,因而尊奉不同經典文本的學者之間在經義理解上多有爭議。
二是學術旨趣不同。漢代有“今學”與“古學”的分野。“今學”關注經文“書法”所蘊含的深意,著力于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方法上側重于經典思想的演繹,特別是對經文遣詞用字的意圖的解讀;“古學”關注經文所記事件的過程和原委,著力于史實的考究和古制的闡述,在方法上側重訓詁文字,考證本義,還原史實。兩種學風之爭有時形同水火。
三是師說家法不同。例如,《春秋》之學有傳承《公羊傳》的公羊學與傳承《谷梁傳》的谷梁學之別。兩大派別的師承關系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都使用今文經,學術旨趣都屬于學術界通常所說的“今文經學”。但是,這兩大學術流派不僅所依據的經傳文本有明顯差異,而且在學術上、思想上多有分歧,彼此之間爭論不休。
四是術業專攻不同。諸如通常被歸入“今文經學”的有三家詩(申培的《魯詩》、轅固生的《齊詩》、韓嬰的《韓詩》),出于伏生的《尚書》(分為歐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出于高堂生的《禮》(分為戴德、戴圣、慶普三家),出于田何的《易》(分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出于胡母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分為嚴彭祖、顏安樂兩家)和江公所傳的《谷梁春秋》等。各種流派之間也存在學術、思想與地位之爭。
在漢代,由于在文本選用、學術旨趣、術業專攻、師法傳授、治學方法、具體解讀和政治境遇等諸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各家各派的經學宗師及其傳人對許多理論問題、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多有分歧與爭論。一般說來,“今學”長期占據主流學術的地位,而“古學”的影響則逐步拓展。二者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交流,總的趨勢是兩種各有特色的學風逐步走向融合,形成相對統合的經學流派。
漢代著名經學大師大多不株守一經,他們博覽群經,廣采眾說,因而統合“古學”與“今學”是經學演化的大趨勢。東漢末年的鄭玄師從著名經學家馬融,精通今、古文經,學術旨趣以“古學”為主,兼采“今學”的成果。他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集兩漢經學之大成,創造了一個統合諸派、自成體系的經學流派。到魏晉,鄭玄所注的《周易》《尚書》《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等先后立于國學,一度出現鄭學稱雄于國學的局面。這標志著帝制國學統合“古學”、“今學”的歷史過程大體完成。
繼之而起的是鄭學與王學之爭。魏晉時期,相繼有人批評鄭玄之學,王肅是典型代表人物。他也采用統合“古學”、“今學”的治經方法。王肅注解群經,處處與鄭玄對立,凡是鄭玄采用“今學”的,王肅就引用“古學”予以批駁;凡是鄭玄采用“古學”的,王肅就引用“今學”予以批駁。王肅之學倡導天道自然無為思想,強調存亡禍福取決于人事,與“天災地妖”無關,從而清除了鄭玄經注中的若干讖緯思想。王肅注解的“三禮”等皆被立于國學,對當時的學術有較大的影響。
在晉朝,朝廷所尊、士人所習大多是鄭、王之學的經典文本及其注本。漢代立于國學的各種今學名家注本則失去往日的華彩,后來大多佚失。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統合“古學”與“今學”的治經方法成為主流。當時最有影響的經學學派均具有“統合五經諸派”特征。這種現象標志著原本由于尊崇不同經典文本和堅持不同學術風格而導致的經學內部的對立已經基本上化解,以綜合化的方式統合經學成為國家學術的發展趨勢。
在南北朝時期,由于長期的政治分裂,南朝與北朝的國學體制、社會風俗、文化傳承存在明顯差異,經學逐漸形成了南北兩派不同的風格,由于分別使用不同的經典傳注本,史稱“南學”與“北學”。北學較多保持了漢魏經學的傳統,一般不采納玄學家的經注。南學則明顯具有玄學化的特征,而玄學化更能代表經學在哲學思辨上的最新進展。南學與北學之爭源于政治長期分裂。一旦這種政治局面結束,“南學”與“北學”勢必走向統合。
在隋唐,中國社會從分裂走向統一,學術亦從“析同為異”走向“合異為同”。一時之間形成了一股進一步統合經學的思潮。《五經正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問世的。
二、三教之爭的積極推動
許多思想文化史的著作籠統地談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的衰落”。這個提法很容易誤導人們的歷史認識,導致夸大玄學、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力,忽略經學的新進展和影響力。
一般說來,在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領域,由于受到玄學、道教、佛教的沖擊,經學的權威地位有所削弱,儒者的感召力也大不如前。但是,經學對這個時期統治思想的影響不可低估。這集中表現為:許多皇帝(包括許多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皇帝)尊崇經學,國學只設五經諸派博士,經學的官方學說地位并沒有動搖;在官僚、士人群體中,信奉經學政治價值的居大多數,許多讀書人專攻儒典,“素不玄學”,《魏書》卷八四《儒林傳·李業興傳》,中華書局,1974年。歷代名臣也不乏博學鴻儒;在朝堂議政中,經學依然是最具權威性的依據,其引用率和有效性皆為其他學派所望塵莫及,這表明經學依然是維系帝制統治的重要理論依據和思想支柱;許多士人博通融會百家之言,無法簡單地將其歸入某一學派,而其政治思想大多有濃重的經學背景,就連玄學、道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價值也深受經學的影響,著名道教思想家葛洪便是典型例證。這就是說,從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大眾的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經學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價值依然占據主流地位,所謂“經學的衰落”只是相對而言。
漢魏以來的三教之爭,為經學的發展創造了最佳的文化氛圍。在魏晉時期,帶有濃重老莊色彩的玄學風行一時,在士大夫階層有廣泛的影響。到南北朝時期,迅速崛起的佛教、道教與儒教分庭抗禮,鼎立而三。從對社會大眾精神世界的影響力看,佛教、道教頗有幾分壓倒儒教的氣勢。在人類歷史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危機往往又是新生的契機,挑戰往往是發展的機遇。作為“正統思想”的經學正是在一場嚴酷的生存競爭中,將佛、道之學的某些成分轉化為思想材料,完成了自身理論形態的轉型。這一點集中體現為經學的玄學化以及其對佛教思想的吸收。
經學玄學化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漢代。當時的許多經學大師兼注《易》、《老》,揚雄、馬融、鄭玄、虞翻等都是典型代表。魏初的宋忠、王肅等人解《太玄》,治《周易》,注《老子》,這種治學方式的盛行不僅導致玄風大作,推出玄學化的經學,而且推動了經學的改造、充實和提升。“魏晉玄學”的流行也勢必影響經學的治學方式。經學的玄學化與玄學化的經學互為因果,相反相成,為經學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
吸收老莊、道教的“天道自然”論對經學提高哲學思辨程度大有裨益。其中,“魏晉玄學”為經學的新進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就學術風格和思想形式而言,玄學是對兩漢經學的反動,主要表現是:擺脫恪守經典的治學方法,探索更具綜合性的學術途徑;沖決保守僵化的師法家法,揮灑頗有創意的義理闡發;鄙薄支離破碎的章句之學,追求玄遠高妙的本體思辨;摒棄荒誕無稽的災異之說,張揚崇尚自然的天人哲理;蔑視虛偽做作的俗流禮法,標榜通脫簡易的名士風骨。在玄學的影響下,無論魏晉的學風、士風都與前代有明顯的反差。
但是,何晏集解《論語》,“善談《易》《老》”;《世說新語箋疏》卷上《文學》注引,中華書局,1983年。王弼祖述王肅,“好論儒道”;《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鐘會傳》,中華書局,1959年。向秀“著《儒道論》”;《世說新語箋疏》卷上《言語》注引。江惇“博覽墳典,儒道兼綜”;《世說新語箋疏》卷中《賞譽》注引。王昶主張“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昶傳》。玄學諸子以老莊哲理解釋《周易》、《論語》,以經義解釋《老子》、《莊子》,他們既繼承了經學的綱常思想,又發揮了老莊的思辨哲學,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玄學是一種風格別致的經學。有的學者從“玄學化經學”的角度認識玄學的本質,這是有道理的。參見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2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70-680頁。從政治思想的角度看,玄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學的發展趨勢。無論學術淵源、論題設定,還是核心價值、最終歸宿,玄學不僅沒有真正脫離主流政治文化的軌道,而且為統治思想,特別是經學理論思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源。
在政治思想發展史上,何晏、王弼、郭象等玄學家的最大貢獻是對名教與自然一致性的理論論證,從而為綱常名教思想提供了更具思辨性的哲理性依據。在玄學家中,對經學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王弼。王弼著有《老子指略》、《論語釋疑》、《周易注》等。在南北朝時期,北方學者大多尊崇鄭玄的《周易注》,南方學者大多尊崇王弼的《周易注》,還有許多經學家兼采兩種易學思想。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梁陳(《周易》)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這就是說,在南朝后期,鄭玄、王弼的《周易注》并立于國學。到隋朝,王弼的《周易注》更為盛行,鄭玄的《周易注》日漸式微。孔穎達編纂《周易正義》就采用了王弼的《周易注》。
從學術發展史和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魏晉玄學”是從“兩漢經學”向“隋唐經學”發展的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魏晉玄學”乃是經學的一個類型。經一批著名經學家的共同努力,玄學的許多思辨成果逐漸被經學所吸收。經學哲理的思辨性、完整性也因此而達到一個新的境界。當時經學有南學與北學之爭。玄學化的南學后來占據了上風,這決非偶然。
旨在闡釋佛教經典的義疏之學也為經學的統合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基礎和解讀方式。義疏又稱疏、義、講疏、述義等,意為疏通證明,發揮義理。義疏既不同于傳注或集解,也不同于玄理發揮,而是介乎義理與訓詁之間的一種新型經學著述形式。它不僅解釋經典及其傳注的詞義,串講句子,而且闡發章旨,申述全篇大義。義疏之學的出現是經學研究從單純注釋逐步向注釋、考據、申說相結合演化的重要標志。《五經正義》的“孔穎達疏”就是在義疏之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在這個時期,標志經學取得新進展歷史現象還有很多,其中對經學統合有重大影響的是《春秋經傳集解》、《孔傳古文尚書》和《論語集解義疏》等經學名著的問世與流行。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問世是經學史上一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自東漢以來,《左傳》日益受到經學家的青睞,為其作注者頗多,逐漸成為《春秋》學的主流。西晉的杜預認為,孔夫子之經與左丘明之傳是對史實的記載,解經者不應牽強附會。他將原來單行的經與傳二者合一,集經傳而解之。這個文本一問世便很快風行一時,東晉初年被立于國學。后來,孔穎達據以編纂《春秋左傳正義》,遂使之取得經學正宗的地位。
《孔傳古文尚書》的問世也是經學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東晉初期,豫章內史梅賾獻給朝廷一部《古文尚書》,共五十八篇,題為孔安國傳。這個版本補足劉向等人所說的古文經篇數,集聚春秋以來人們所引用的《尚書》文句,博采西漢以來各派經師的解說,并以通俗的語言逐句加以解釋。這個版本一經問世便獲得朝廷的青睞和學者的喜愛,于是立于國學,廣為流行,取得《書經》的正統地位。
應當指出的是:《孔傳古文尚書》是一部經學杰作。它雖被后人證偽,卻集以往《尚書》學之大成。它所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歷史文獻的孑遺,其史料價值尤為珍貴。其文句并非憑空捏造,皆有前代文獻依據,因而可以為研究東晉以前的官方學說和經學思想提供重要的佐證性史料。東晉以來,《孔傳古文尚書》被立于國學,到唐朝成為國學的標準讀本,被統治者和絕大多數讀書人奉為正經正注,因而是研究這個時期官方學說和主流文化的可靠史料。
南朝梁的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是統合經學與玄學的重要代表作,其思想特點展現了經學的演化趨勢。皇侃為玄學家何晏的《論語集解》集注作疏,兼采兩漢經學名家的訓解和魏晉玄學名家的疏解,以玄學的哲理論證經學的綱常、仁義、孝悌,這就將玄學的思維成果引入經學。這部經學名著還受到佛學的影響。皇侃的學術成果對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有重要的影響。
大量事實表明,經學在一定意義上的衰落不僅沒有導致經學的終結,反而標志著它向新的境界、新的高度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一種喪失影響力的經學衰落了,另一種更具生命力的經學萌生了。許多經學家統合諸派,博通百家,兼收并蓄,遂使一種新的學風逐步形成。他們在保持經學固有學術旨趣和堅持經學的核心價值的同時,吸收老莊、玄學、佛學的思想成果,為經學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方法,大幅度提升了經學的思辨水平。這些新進展使經學逐步解決了自身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有助于去除漢代“今學”的穿鑿虛妄,擺脫漢代“古學”的拘謹繁瑣,融會各種學術因素,發掘各種經典的義理真諦。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整合各種經典文本注疏的趨勢日益明顯,統合經學的學術條件日益成熟。集以往經學之大成的《五經正義》正是這一學術發展趨勢的產物。
三、中國統一的政治契機
思想文化的演變與社會政治的演變息息相關。國家的分裂與政治的對抗往往導致文化的分化與思想的對峙,而國家的統一也往往推出統一程度較高的思想文化。從魏晉到隋唐,中國大地大部分時間處于政治分裂狀態。與此相應,經學也處于分裂狀態。在隋唐,中國統一得以實現,從而為經學的統合創造了政治契機。
隋文帝重視經學及學校教育。他采納牛弘的建議,下詔求天下遺書,獻書一卷,賜絹一匹。他廣開庠序,優禮儒生。據《隋書·儒林傳》記載,隋文帝“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于四方,皆啟黌學校。……中州雅儒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文帝晚年不悅儒術,一度廢學,而“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征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隋書》卷七五《儒林傳》,中華書局,1973年。隋煬帝興辦學校,尊師重道,設立科舉,獎掖人才,這就為經學的繁榮興旺創造了優越的條件。
到隋煬帝時期,統合經學的各種條件已然具備。一統的帝國和創新的體制需要有相對統一的經典文本及其闡釋體系,統合經學的問題提上了政治日程。隋煬帝多次親自召集并主持經義辯論,經學界也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學術論辯。在這場波及朝野的論辯中,孔穎達就曾因扮演積極的角色而嶄露頭角。大業四年(608),隋煬帝令全國學官集會洛陽,討論經義。孔穎達辨析經義,力挫群儒,榮獲第一,補太學助教。在國家政權的干預下,經學加快了統合的步伐。如果不是隋煬帝很快就招致國破身亡,類似《五經正義》的經學巨著極有可能產生于他所統治的時代。
在唐朝,“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會要》卷三五《學校》,中華書局,1957年。國家對學校系統、分科設置、課程內容、入學資格等做出詳密的規定。據《新唐書·選舉志》記載,中央學校有六學二館,“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勛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勛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中華書局,1975年。門下省的弘文館、東宮的崇文館則是皇親國戚、宰相、功臣及其他朝廷顯貴子弟的學校。地方學校有京都學、都督府學、州學、縣學,皆設置學官,督導學政,教授經學。除個別專科性質的學校外,國學的教育內容一律以經學為主,如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皆設《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禮記》等五經博士,學生“五分其經以為業”。《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地方學校也都設經學博士、助教,以“五經”教授學生。國學及各類學校教育的發展勢必推動經學的繁榮與發展。
唐太宗奉行三教并重、經學優先的政策。他下令立周公祠,奉孔子為先圣,顏淵為先師,宣稱:“朕今所好者,惟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六《慎所好》,中華書局,2003年。皇帝尊經學為正宗,以經學來選士,據儒經以議政,并為學校教育和文化建設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充分的資源保障,這就為經學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環境。統合經學的過程正是在“貞觀之治”的大背景下得以完成的。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家統一,政治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王朝出現盛世景觀。于是朝廷的一系列文化建設構成“貞觀之治”的重要內容之一,諸如修撰《貞觀禮》、修撰“五代史”(《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和編纂《五經正義》等。于是標志經學統合過程基本完成的《五經正義》應運而生。
四、制度創新的特殊需求
在論及唐代皇帝下令編纂《五經正義》的目的時,許多學者強調“統一思想”這個政治動機。他們認為,由于政治統一要求思想統一,因而唐太宗統一經學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消除異端。正是這一政治訴求導出了經學的統一。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唐朝政治統一的程度勝過漢朝,因而統一思想、統一經學的力度也大于漢朝。這一類的說法乍然聽來不無道理,卻有待推敲。
首先,政治統一要求思想統一,這是政治統治的一般法則和文化演變的自發趨勢。古往今來,任何一種政治實體都會有統一思想的訴求并采取相關的措施。關鍵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這樣的政治訴求,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實現這種訴求。因此,無論中國是否統一,每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實體都必然以某種方式推行與思想統一相關的政治措施。在中國處于嚴重分裂狀態的南北朝時期不難找到這方面的例證,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北魏孝文帝以改革政治的方式,推廣華夏生活方式及其核心價值。這就是說,無論中國是否統一,都會有思想統一的訴求。恰恰是由于這個緣故,反而不能將這個極其重要的持續起作用的歷史因素,列為唐太宗“統一經學”這個具體事件的直接動機。從現存史料看,唐太宗并沒有公開宣布要通過編纂《五經正義》來“統一思想”。這與秦始皇焚書和漢武帝尊儒時的做法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在通常情況下,中華帝制的統治者并不以學術高度統一的方式維護思想統一。秦始皇以焚《詩》、《書》的方式統一思想,卻沒有指定某一學派為官方學說,也沒有禁止儒者在朝做官,甚至在朝廷設置學官,專門從事各種經典的研究。漢武帝尊儒術,以配套的措施扶植經學,卻沒有采取剛性措施禁絕其他學派。為了適應政治統治的需要,兩漢朝廷常常直接干預經學的發展方向,漢宣帝召開石渠閣會議、王莽刪節五經章句并在國學增設“古學”博士、漢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等都是典型事例。但是,在兩漢、魏晉、南北朝,皇帝的通行做法是將影響較大的經學派別統統立于國學。從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到漢宣帝置今學十四博士,國學的學術多樣性日益增強。漢平帝一度增置《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博士。王莽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不僅增列“古學”博士,而且大幅度增加公車征召范圍。隨著“古學”聲望的提高,東漢皇帝也多有試圖增置“古學”博士之舉,卻被學術上的既得利益者設法阻止。魏晉以來,鄭學、王學之爭形同水火,卻可以并立于國學。與“兩漢經學”有明顯差異的“魏晉玄學”并沒有遭到來自國家政權的剛性壓制。到南朝,鄭玄的《周易注》和王弼的《周易注》可以并立于國學。在經學內部,始終存在著爭立于國學的現象,而統治者常常采取“義雖相反,猶并置之”《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中華書局,1962年。的政策,甚至“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直到《五經正義》產生之前,沒有哪個朝代的統治者采取過強行統一經學的措施。甚至可以說,就連這樣做的念頭都不曾產生過。《五經正義》問世以后,唐朝統治者并沒采用剛性措施將學術統一于《五經正義》。《公羊傳》、《谷梁傳》等不僅依然列在經典名錄,而且依然被用作明經考試的“小經”,這便是最好的證據。《春秋》學在唐代的發展也表明統治者沒有采取剛性措施將經學限制在特定的框架內。顯而易見,帝制的統治者大多懂得一個道理,即統一學術有利于統一思想,而統一思想不必強求學術一元化。在維護帝制核心政治價值的前提下,保持文化與學術的多元化,這是中國古代統治者通行的做法。因此,唐太宗下令編纂《五經正義》,其主要意圖不是要以這種方式統一經學。
第三,在通常情況下,中華帝制的統治者對各種宗教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這一點與當時世界各地通行的確定國教、強迫皈依、剪除異端的做法有明顯的差別。東漢以來,道教、佛教的大發展便得益于這樣的宗教文化政策。統治者信奉乃至扶植道教、佛教的現象不勝枚舉。道教在崛起過程中也曾遭到一些統治者的打壓,而其主要動因是現實政治考慮,即防范利用道教策動反抗朝廷的行動。佛教也曾屢遭禁絕,而其主要動因源于中外兩種文化的沖突。一旦道教、佛教的教義向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貼近,這類沖突就基本化解了。因此,在隋唐時期,統治者的基本政策傾向是三教兼收并蓄。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動機也與財政、賦役等政治考慮有關。這就是說,只要核心價值與主流文化沒有根本性的沖突,只要不以宗教的方式反抗朝廷,只要對皇帝的權威不構成威脅,只要不嚴重影響國家財政,各種學術、各種宗教通常可以并行不悖,共處共存。
沿著上述思路不難推知:只要國家堅持以經學為國家學術,經學的核心價值便不難獲得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同;只要國家堅持給予必要的投入,以經學為主的國學及各級官學便不難持續下去;只要國家堅持以經義取士,經學便不難保持主流學術的地位。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都大體做到了這一點。只要瀏覽一下《北史·儒林傳》、《隋書·儒林傳》,就不難知曉北朝少數民族統治者也大多奉行尊崇經學的政策,并取得顯著成效。他們對經學各派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為了扶持微學,增廣見聞,歷代朝廷設置名目繁多、流派叢雜的經學博士,諸如漢代的“今文經十四博士”之類。當時的皇帝、朝臣也沒有感受到必須立即統一經學的迫切性。在朝堂議政中,甚至很難找到關于經學一元化的討論。因此,在考察經學統合的歷史過程的時候,既不必夸大中國統一的作用,也不必夸大皇帝獎掖經學的作用,更不必執意認定必須以統一經學的方式統一思想。
為什么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不僅容許不同文本、不同傳注、不同師說的經學分立并存,甚至將它們并立于國學,而隋唐的統治者則致力于統合經學?如果追溯歷史過程,尋求因果關系,探究變化之因,就不難發現:在隋唐以前的制度下,由于沒有必須將經典注疏規范化的特殊需求,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允許經學諸多派別共存于國學,而在隋唐制度下,由于產生了特殊需求,主要經典注疏必須統一。這就是說,統合經學最主要的歷史動因是政治制度的創新。
隋唐制度與前代制度的明顯差別之一就是廢除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長官自辟官佐僚屬制度,將選拔和任免各級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政府。與此相應,中央政府必須建立新的人才選任制度,以適應批量化、高質量優選新進官員的需要。于是一種屬于考試任用范疇的科舉制度應運而生。隋文帝、隋煬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掖經學,又創造科舉制度,不論門第,以考試經義舉士。這是政治制度的重大創新。作為新制度的配套措施,統合經學勢在必行。因此,科舉制度的產生及其特殊需要才是推動經學走向更高程度的統合的至關重要的政治因素。
科舉考試要求更高程度的經典文本及其注疏的統一。以考試方式大批量選拔人才,必須做到使用的教材大體統一,試題的依據大體統一,閱卷的標準大體統一,否則很難保證考試的公正,選拔的公平。據《北史》、《隋書》等記載,由于經學內部的差別很大,“師訓紛綸,無所取正”,《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中華書局,1974年。就連國學的博士都不可能通曉各種經說。于是在教學實踐中,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爭論不休,“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隋書》卷七五《儒林傳·房暉遠傳》。教學過程尚且如此,國家考試就更難應付。在唐朝,科舉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分科考試選拔官員成為重要仕途。科舉制度的發展迫切需要經學一定程度的統合,特別是作為主要考試科目的經典文本及其注疏的統一。如果沒有科舉制度的特殊需求,即使經學的自身演化、國家的政治統一導致經學某種程度的統合,其統合的程度也很有可能不會達到《五經正義》的水平。
自從有了科舉制度以后,歷朝歷代都有明確考試所用經典文本及其注疏的規定。北宋以來,“四書”逐步取代了“五經”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元、明、清的統治者尊崇程朱理學,于是朱熹的《四書集注》開始扮演《五經正義》一度扮演的角色,在統一思想、統合經學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歷代朝廷并沒有因此而禁止眾多經學流派同時存在。只要瀏覽一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便可大體知曉這一基本事實。不僅如此,在統治者欽命編纂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中,容納了許多與程朱之學不盡相同的學術觀點。由此可見,無論漢武帝尊儒術,漢宣帝置十四經博士,還是唐太宗欽命編纂《五經正義》,元朝皇帝欽定以《四書集注》為科舉標準讀本,都有引導學術方向、維護核心價值的訴求和功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最高統治者只允許一種學術、一種宗教、一種聲音存在,甚至刻意追求將思想統一于一種學術、一種宗教、一種聲音。
中華帝制的統治者通常不以統一經學的方式維護思想統一,這種歷史現象很值得深入研究。“統一思想”這個一般法則顯然會普遍地、持續地起作用,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統治行為。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諸多歷史事實表明,既不應將“統一思想”列為隋唐皇帝致力于統合經學的直接動機,也不應夸大統治者“消除異端”的訴求在經學統合過程中的作用。一般說來,中華帝制的統治者沒有將統治思想的源泉僅僅限定于經學,更沒有限定于經學的某一流派。中國古代文化既有高度的同一性,又有豐富的多樣性。這一特點與帝制的文化政策取向有密切的因果關系。在世界古代史上,中華帝制以尊儒經、興學校、開科舉等措施統一思想的做法有其高明之處。與以某一宗教定一尊的方法相比較,這種以具有一定開放性的學術定一尊做法既能有效地推動思想統一,促進文化統一,逐步實現社會各階層核心價值的統一,又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思想的多樣性、學術的多樣性、宗教的多樣性和地方文化的多樣性。在評說帝制的統治思想及其對思想文化演化歷程的影響時,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否則就容易導出簡單化的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