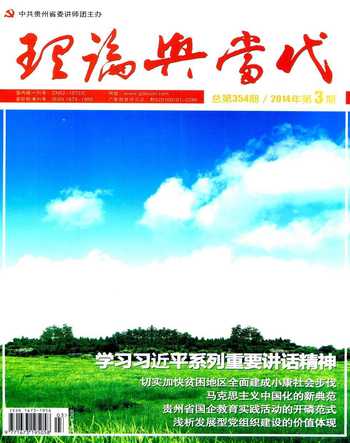嵇康接受詩學的圓融性
楊家海
嵇康接受詩學主要是在談論音樂接受過程中體現的,它與西方接受美學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接受美學往往以接受者為中心來闡釋文本,甚至忽視文本的意義,并忽視社會的規范性作用。嵇康既認識到接受者在接受和闡釋過程中的主導性作用,將之與接受對象進行對話,也認識到在接受效果上必須考慮社會規范的重要意義。
自漢代推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始,儒學逐漸成為官學和經學,在后期面臨兩種發展趨勢:“一是空守章句師說以至煩瑣迂闊”,“另一發展趨勢是與陰陽五行災異讖緯之說緊密結合,援天道以證人事以至荒誕不經。”籍此裂變,玄學興起。“魏晉玄學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從漢代的宇宙論轉向了本體論,它的中心課題就是要探求一種理想人格的本體。”作為魏晉時期的代表人物,嵇康具有多元化的文化修養,在儒學和道學上都造詣頗深。盡管當時的儒學已經異化為統治者的馭人工具,但嵇康依然認同發自內在德行生命的儒學,所謂“由仁義行”,而非外鑠的“行仁義”。在道學上,嵇康根據老莊的陰陽二氣相互交融而產生萬物的思想,將天地萬物的本源歸于元氣。同時,嵇康還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為時輩推崇,當時的風流人物鐘會曾就才性問題向嵇康請教。針對名教的約束,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稱“非湯武而薄周孔”,在《釋私論》中更是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吶喊。
籍此思想和個性,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提出了“心之與聲,明為二物”的觀點,即將“聲”從世風民情中解脫出來,也將接收者之“心”從名教束縛中解脫出來,肯定它們的獨立價值。
從“聲”的角度來說,嵇康以“聲無哀樂”名篇,認為“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就是對《樂記》的一個顛覆,直接展示其獨立地位。這也是對“聲之體”的追問。嵇康認為,聲之體在于“和”,如《聲無哀樂論》云:“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又云:“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聲音以平和為主體,而感物無常……”而且,他還分別從音樂形式和音樂形象兩個方面對之進行了論述。其音樂形式表現為“比”。音樂的聲調、節奏,各有不同,但都是有一定的形式的,所謂“聲音和比”、“聲比成音”,“比,其本義謂相親密也。……擇善而從之。”其音樂形象表現為“麗”。《琴賦》云:“狀若崇山,又像流波,浩兮湯湯,郁兮峨峨”,“鸞鳳和鳴戲云中”、“眾葩敷榮曜春風”,把難以把捉的音樂形象化為具體的自然之物呈現在讀者面前,并讓讀者在感受美好形象的體驗中,領悟音樂的自然氣質。
從“心”的角度來說,嵇康認為,稟陰陽二氣而生的人,也追求精神和情感上的自然之“和”。《明膽論》云:“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太師箴》云:“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人心之“和”在于“愛憎不棲于,隋,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體氣和平”,“神以默醇,體以和成”(《養生論》),也就是要超然于名利欲望所導致的愛憎憂喜。嵇康還將之落實為“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贈秀才入軍》十八)的理想人格,正如湯用彤先生所說,“故其時(魏晉)之思想中心不在社會而在個人,不在環境而在內心,不在形質而在精神。”
從“政”的角度來說,嵇康認為,社會應該順其自然,無為而治,實現政治之“和”。在嵇康看來,社會的運行也需要儒家的忠義道德,必須是源于個體的自然體認,不是將之作為一種必然規范而遵循。《聲無哀樂論》云:“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抱忠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甚至社會規范中的各種人倫物情都是自然的,所以《答向子期難養生論》云:“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而托身,并天地而不朽。”為此,羅宗強先生感嘆說:“嵇康是歷史上將莊子理想的人生境界具體化、人間化、詩化的第一人。”
嵇康站在自然元氣論的本體高度,俯視各種音樂現象,在闡釋音樂接受活動時不至于走向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從而形成了其接受詩學的圓融性。
從“聲”與“心”的互動關系而言,嵇康尊重音樂的獨立地位和接受者的“人情不同”,既考慮到不同的音樂形式和音樂風格對人情的調動作用,也認識到在音樂接受活動中,接收者發揮著主導作用,也因此不同的接受者對音樂形式的理解可以是多樣性的。
首先,嵇康認為,只有“和聲”才可以收到“心和”之效。《聲無哀樂論》云:“曲度雖眾,亦大同于和。”聲音雖有不同,但和聲可以調動相應的人情反應,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談論了兩種情況:一是不同器質的樂音調動人的情緒反應情況,如“琵琶箏笛,問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使人形躁而志越”。二是不同風格的曲調調動人的情緒反應情況,如“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嵇康也發現,對“和聲”的闡釋則取決于“心”,如《聲無哀樂論》云:“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這說明嵇康在論述聲音的文本形式和對人情的調動作用時,并沒有走向文本主義的單向思維,而是充分認識到音樂活動是一個音樂文本與接受者相互作用的過程。
其次,嵇康提出“樂之為體,以心為主”的主張,充分認識到“心”的主導性作用。《聲無哀樂論》云:“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各種器質和曲調的“和聲”,在應感之情上沒有固定對象。中國文化傳統和名教則認為,音樂形式和曲風與社會政治的情況是有著對應關系的。嵇康對此極力反對,認為這是“濫于名實”的,實際情況是“人情不同,自師所解”。《琴賦》云:“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僭懔慘凄,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欽愉歡釋,抃舞踴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懷戚者””康樂者”“和平者”面對同樣的音樂文本,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情感判斷的情況。這說明嵇康既認識到接受者在文本接受活動中的主導性作用,也承認了“心”對“聲”的闡釋的多樣性,這對促進文本的多元化解讀、發掘文本的多重意義,具有重要意義。
從音樂接受效果而言,嵇康認為音樂活動的目的既不在于突出音樂文本的獨立價值,也不在于突出接受者的個體差異性,而在于實現“政和”。《琴賦》云:“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原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嵇康認為歷代才士為琴音作賦之所以不能抓住其“旨趣”,是因為“未達禮樂之情”,這說明嵇康是把禮樂看作一體的,具有社會的共同性和規范性。
嵇康知道,如果不對具有“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琴賦》)作用的音樂進行引導,就會使人情“流放”,這就是圣人之所以重視樂之教化的原因。所以《聲無哀樂論》云:“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之?”由于嵇康以“和”為“聲”和“政”的本體,所以,不必以音聲之作迎合政治之需,也沒有以政治之需曲解音聲之義。實際上,他是以“和聲”來實現“政和”。《聲無哀樂論》云:“托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從中可以看出,“和聲”是通過使“心感于和”,來實現移風易俗的作用,從而達到“和聲”“心和”“政和”三位一體的。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就如何實現移風易俗做出了論述:“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后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這說明是一個長期感化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又云:“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采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這說明音樂只能起到一個誡勉的作用,不可夸大其作用。
原來,嵇康以自然元氣論作為思想基礎,認為天地萬物都是出自于元氣,以“和”為本體,故聲、心和政的本體在于“和”。因此,嵇康接受詩學不是以接受者為中心的一元論闡釋,而是“聲—心—政”三位一體的,致使他的接受詩學具有了圓融性。本文通過研究嵇康接受詩學的圓融性,為發掘魏晉接受詩學的特性,也為理解中國接受詩學的特性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視角。
參考文獻:
[1]馬良懷:崩潰與重建中的困惑:魏晉風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51-52.
[2]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7頁.
[3]戴明揚.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4]許慎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86.
[5]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6.
[6]羅宗強.秘康的心態及其人生悲劇.中國社會科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