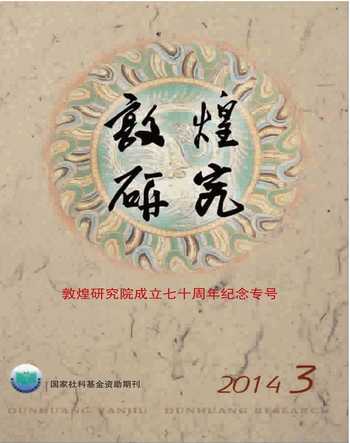敦煌藝術的文化力量
內容摘要:敦煌藝術秉承了古代印度佛教思想的傳統基因,在引進、消化和吸收過程中,進行了漢化、重組和創新的長足發展,從前秦建元二年(366)莫高窟鳴金開窟到元代(1368)敦煌營造息鼓的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里,成為推動世界佛教藝術蓬勃向前的一個巨大引擎。1900年藏經洞的發現導致了敦煌學的崛起,70年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的成立賦予敦煌藝術全新的生命力。縱觀敦煌藝術的緣起、內涵和影響,可以感受敦煌藝術的文化脈絡的傳承,感悟敦煌藝術的文化力量。
關鍵詞:敦煌藝術;敦煌研究院;文化傳承;世博演繹;數字傳播
中圖分類號:K20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3-0043-08
Cultural Force of Dunhuang Art—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unhuang Academy
CHEN Xiejun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200003)
Abstract: Dunhuang art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gene of Buddhist thoughts in ancient India and underw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iciz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Over more than 1000 years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Jianyuan (366) in the Former Qin when construction of the caves began to the Yuan dynasty (1368) when construction stopped, Dunhuang art had been a huge engine that pushed forward world Buddhist art. The discovery of the Library Cave in 1900 gave birth to Dunhuangology, while the founding of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todays Dunhuang Academy)75 years ago gave a new life to Dunhuang ar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Dunhuang art as well as its impact indicat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force of Dunhuang art.
敦煌是中國古代連接東西方文明的絲綢之路東端的一處咽喉重鎮;敦煌藝術是世界文明燦若星河的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敦煌研究院是中國設立的負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瓜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等的保護、管理和研究的一個綜合性的專門機構。時值敦煌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之際,追憶敦煌藝術近1700年來的文化傳承,回味敦煌藝術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上的成功亮相,展望敦煌藝術與現代科技高度融合而正在崛起的數字傳播,作為博物館人無不感到崇敬和喜悅,謹以此拙文,共襄盛舉。
一敦煌藝術的文化傳承
敦煌藝術源于印度佛教而又開啟了中國佛教藝術的先河,其秉承了古代印度佛教思想的傳統基因,在引進、消化和吸收過程中,進行了漢化、重組和創新的長足發展,從前秦建元二年(366)莫高窟鳴金開窟到元代(1368)敦煌營造息鼓的長達1000多年的時空經緯間,成為推動世界佛教藝術蓬勃向前的一個巨大引擎。18世紀后,被掩埋了數世紀的敦煌莫高窟終于重見天日,1900年藏經洞的發現導致了敦煌學的崛起,70年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的成立賦予敦煌藝術全新的生命力。縱觀敦煌藝術的緣起、內涵和影響,可以感受敦煌藝術文化脈絡的傳承,感悟敦煌藝術的文化力量。
敦煌藝術的發端和佛教密不可分。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紀的古代印度,相當于距今2500年左右的中國春秋時代。佛教理論的核心內容宣揚人類的現實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遵循佛教教義提倡的解決苦難、擺脫痛苦的方法,才能使人從生死輪回中得以解脫,達到走向彼岸的極樂世界。佛教發展成為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之一,逐漸向印度之外的各個地區擴散傳播。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地理上是中國連通世界的陸路通道上的重鎮。在經濟上,它成為中西貿易的貨物集散地;在文化上,它是中西文化薈萃交融之地。由于政治上敦煌也是歷代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重鎮,所以中原文化始終也是敦煌地區的主流文化。因為傳播佛教的僧人、使者都是以敦煌地區作為進入中原的首要補給停歇地,所以佛教在這里作為外來文化和主流中原文化開始碰撞并融合,這個時間約在西漢末期,為隨后敦煌石窟的鑿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礎。
敦煌石窟是古代敦煌地區佛教石窟寺的總稱,它包括今甘肅省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縣的榆林窟、東千佛洞、水峽口下洞子,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五個廟,玉門市昌馬石窟等。其中開鑿最早、規模最大、彩塑和壁畫最精彩者首屬莫高窟。據史料記載,莫高窟首創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是由內地游方僧人樂僔開鑿了第一個石窟,而后經歷了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回鶻、西夏、蒙元千余年不斷地續建和重修。其他石窟則為莫高窟的姊妹窟,營建時間短,規模較小。目前,各處石窟中保存有彩塑和壁畫的洞窟數量分別是:莫高窟492個、西千佛洞22個、榆林窟42個、東千佛洞8個、五個廟5個。莫高窟北區另有僧房窟、禪窟、佛殿窟等243個。
敦煌藝術的載體主要是石窟建筑和其中的彩塑、壁畫,其次是紙、麻、布帛等畫,被稱為敦煌遺畫,還有一些雕版印刷品等。按照造型藝術門類可以分成建筑藝術、雕塑藝術和繪畫藝術。從壁畫的內容和敦煌文獻中包含的曲譜、舞譜等寫本中又可分為音樂藝術和舞蹈藝術,敦煌文獻中的變文、詞、曲、調等可構成文學藝術。這些藝術作品是由古代各類藝術家歷經千余年時間嘔心瀝血、逐步積累創作的,尤其是彩塑和壁畫的藝術精妙絕倫,堪稱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和世界文化遺產,它們以豐富的內容、變化多樣的構圖、獨特的藝術風格、生動的藝術形象、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向世人展示自己非凡的藝術魅力。
敦煌莫高窟已經歷了近1700年的歷史長河,留下了壁畫45000多平方米,如果以2米的高度把它們拼接起來則可長達25千米,可以變成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藝術畫廊。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藝術是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主體。就其壁畫的內容來說,都是佛教經典的圖解,屬于佛教文化藝術的范疇,但它也從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現實情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壁畫中呈現的古代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場景有耕獲、狩獵、捕魚、拉纖、撐船、修建、制陶、駕馭車馬等,為研究古代人類的勞動生產、交通運輸、音樂舞蹈、衣冠裝飾的歷史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壁畫中還有大量的極富裝飾性的圖案花紋,千變萬化,內容豐富,反映了古代人類紡織印染工藝發展的高度水平。一些壁畫表現統治階層窮奢極欲的日常生活,有乘輿、馭馬、宴飲、出行、宮廷娛樂等,以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友好交流和商貿往來的生動形象。
莫高窟內的塑像是從十六國至清代11個朝代1000多年間逐漸塑造起來的。從高達三十幾米的巨像到十幾厘米的小像都有,窟內保存兩千余身彩塑,其中有1400余身基本完好。彩塑的題材和對象是佛教尊奉的諸佛和諸神,是佛門弟子、僧俗大眾敬奉和禮拜的各種偶像。有佛陀、菩薩、天王、力士、供養人像等,有虛構的宗教形式,也有世俗世界的真實人物。
在敦煌藝術寶庫中,佛教題材的藝術盡管占據了絕大部分的篇幅,但是佛教畢竟只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重要的影響力影響著敦煌的方方面面,但面對占據主流的中原文化和藝術,面對許許多多來自其他地域的文明,它卻并不是支配一切的思想。相反,倒是世俗的政治、經濟、生活隨時支配著佛教,不僅支配著它的內容,而且支配著它的形式,使之形成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和藝術形式。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同時留存有很多的地域文化,比如湖北、湖南一帶的楚文化,四川一帶的巴蜀文化,江蘇、浙江一帶的吳越文化,山東一帶的齊魯文化等,這些地域文化相互影響又相對獨立,相互改造又相互融合,形成一種為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統治目的服務的中原文化。這是整個國家或民族的主流文化,相對于敦煌地區,則被稱為漢文化。西漢時期,中央政權加強了對西域的控制,為了消滅日益強大的匈奴民族的南侵,暢通漢王朝和世界各文明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產生活等交流的陸上通道,敦煌成為中原王朝最為重要的邊疆軍事戰略要地之一,成為中西陸路交通最重要的橋梁和紐帶。它以漢文化為主流文化,融合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各民族、各地區的人類文明和文化,迎來了敦煌地區形成和奠定自己今后特有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地位的大發展時期,促進了佛教文化藝術和漢文化藝術的大融合。
漢王朝之后,中原政權在一定時期內沒有形成一個強大集權的政權,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動蕩混戰的時期,暫時放松了對敦煌地區主流文化的影響。這一時期敦煌的政權統治不斷更替,但這種政權更替相對來說并沒有造成該地區整體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藝術的動蕩和破壞,反而在大動蕩的背景下,敦煌地區保持了較小的震蕩。各中小民族繼續大融合,佛教文化藝術有機會快速地吸收眾多民族文化藝術的精華,各種文化藝術風格相互融合,達到了敦煌文化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北周王朝結束了戰亂,統一了中國的北方地區,為隋王朝進一步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隋統一全國,又為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藝術的空前發展準備了充實的條件。敦煌地區平穩地過渡到了中國封建時代最繁榮的發展時期,隨著敦煌地區政治、經濟的再一次強有力的回歸,它的文化藝術的發展掀起了又一個高潮,其所取得的成就也進入了它的最高峰時期。
唐王朝衰落后,敦煌的文化藝術發展進入重要轉折期,從唐中期直到五代,吐蕃和西夏先后統治敦煌,盡管政治制度相對從封建制退后到農奴制,但民族文化藝術的融合卻進一步發展了。唐代以后,海路交通交流的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尤其是遠洋航海能力的不斷加強,通過海路的貿易和政治、經濟、文化與藝術的中外交流日益強大,敦煌地區的歷史地位大為下降,這種情勢,特別是到了明代封閉嘉峪關以后體現得最為明顯。
敦煌藝術的融合和傳承,有著它本身的特殊性,盡管紛繁復雜,卻能水乳交融,最后幻化出嶄新、瑰麗的新的藝術組合和新的藝術形式。敦煌地區主流文化是中原漢文化,漢民族本身是漢王朝統一中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一個混合的民族,它包括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許多少數民族,許多民族最后融合了。而與敦煌地區貿易往來的胡人,也是來自于四面八方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有來自敦煌本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有從歐洲傳來的希臘、羅馬的文化以及從印度或中亞傳來的文化。有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還有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的文化。外來的文化和主流文化并沒有在這里因發生沖突而使某一種文化滅失,相反它們相互認同這種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并且積極地融合,最后繁衍出敦煌文化這樣一個全新的文化表述方式和藝術形式。敦煌飛天的藝術形式優美動人,人們一般認為它源于印度的原始宗教神緊那羅,并非佛教本身的人物。早期的飛天形象呆板,身體姿勢呈直角,在不顯眼的位置上,并沒有飛的感覺。傳到阿富汗巴米揚、巴基斯坦后,它的形象仍無改觀,再進一步傳到新疆和田后,飛天像希臘的愛神一樣,在肩膀上加了兩個很大的羽翅,但依舊沒有飛動感。相反,中國道家的羽人形象卻有強烈的飛動感。等到了北魏時期,莫高窟里的伎樂飛天的身體姿勢都彎折成V字形或U字形。她們沒有羽翅,單純依靠靈動的線描的服飾線條,依靠飛動的飄帶就能凌空飛舞。北朝飛天瘦骨清像,飛動的服飾顯得很飄蕩,而隋代的飛天臉龐豐腴方正,成群結隊,唐代飛天更是雍容華貴,并且已經發展到了不借助很多服飾的線條和飄帶也能扶搖而上出神入化的藝術境界了。所以飛天從一個外來的文化藝術形象,通過融合創新,完全成為中國的敦煌飛天。
從“絲綢之路”的“絲綢”上也能看到這種文化和藝術的差異與融合。雖然在這條舉世的通道上還有茶葉、瓷器和白銀等大量的貨物在流通,但絲綢更具有傳播的代表性。其實到了唐代,“絲綢之路”上已經有了許多“絲都”,不僅是來自于長安的絲綢,還有意大利絲都佛羅倫薩、法國、波斯和吐蕃等地區的胡錦、波斯錦、蕃錦等都在敦煌貿易交換。從考古上看,有的貴族墓地里出土的絲織品多達五六十種,其中一半種類都不是中國的絲綢,許多中國的絲綢上也刺繡了外邦的文字和來自西方的聯珠紋樣。通過絲綢的貿易交換,不同的文化和藝術表現形式相互交融,不斷地傳承和擴散著。
各種宗教意識形態在敦煌地區交匯,除了佛教、道教之外,還有波斯、摩尼、火祆、粟特等教。敦煌文獻《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里就提到西天除佛教之外,還有其他信仰,達96種之巨。這些宗教信仰在敦煌地區匯聚交融,以自由、開放、兼容的姿態并存,許多佛經的翻譯者是漢族人,但更多的是華戎兼通的少數民族。在敦煌的眾多文獻里幾乎看不到宗教信仰之間的扼殺和排擠。佛、道、儒家文化在敦煌壁畫里相互兼容并蓄,甚至演繹出《老子化胡經》等故事。
敦煌文化和藝術是多種文明相互交融、促進和共存的多民族文化,不是單一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單純的佛教文化或儒家文化。它顯示出兼容、寬容、求索、和平、進步、發展的時代精神。它體現了人類保護和積累文明財富,傳承人類文明的美好愿望。這些特點保證了敦煌文化和藝術在1000多年的生成、繁榮和傳承過程中的相對穩定性,最終成為中國的文明,也成為世界的文明。
20世紀初,敦煌及周圍地區歷史、文化與藝術遭到了空前的劫掠。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這批古文獻總數在60000件以上,多為手寫本,也有極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除大部分為漢文外,還有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內容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書為主。敦煌文獻的發現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發現,敦煌文獻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
敦煌藏經洞寶藏先因王道士變賣、送出一部分而流失,而后遭到了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的劫掠,他們掠走了寶藏的大部分,將其中的經卷文書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巴黎國立圖書館,藝術品則藏于大英博物館和吉美博物館。此后,劫余的文獻雖由清政府下令押解回京,入藏京師圖書館,但來自日本、俄國和美國的盜寶者仍紛至沓來,對敦煌寶藏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敦煌文獻和文物的流散,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損失,但它們的發現讓世界認識到敦煌這顆曾經湮沒在沙土之下昔日的無價明珠,推動了世界對敦煌文化與藝術寶藏的研究和保護。張大千曾兩赴敦煌,在敦煌長達兩年的停留時間里,對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為莫高窟和榆林窟編號,并臨摹了莫高窟各時期壁畫的代表作。許多學者也加入敦煌的考察活動,提高了敦煌在學術界的知名度。國內外學者開始爭相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刊布,對敦煌石窟進行考察研究,由此誕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敦煌學至今已有百年歷史,英、法、日、俄、美等國的敦煌學家也為之做出了貢獻。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新中國成立后, 1950年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中國政府對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崖體進行了全面加固。1980年后,對石窟加強了科技保護,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是全人類的寶貴文化財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7年12月把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敦煌藝術既是佛教藝術,也是中華藝術,還是世界藝術,具有宗教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敦煌藝術不僅影響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昨天,也影響著今天和明天。
二敦煌藝術的世博演繹
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邀世界各國聚集上海浦江之畔,共同舉辦了一屆成功、精彩、難忘的世博會。作為上海世博會五個主題館的城市足跡館、城市人館、城市生命館、城市地球館和城市未來館從不同的時空角度出發,詮釋人類與城市、環境的關系。城市足跡館位于世博浦西園區,坐落于盧浦大橋邊的黃浦江畔,館址是利用上海世博園區原江南造船廠老廠房改建而成的,建筑面積約20000平方米。上海博物館承接了世博會課題,率隊營建了城市足跡館和世博會博物館。在籌建城市足跡館之初,我們首先確立了“集世界博物館文物之精華,展世界城市發展足跡之智慧”的理念,經過數年精心籌備,整體規劃,有效推進,形成了深度演繹序廳“理想幻城”、第一廳“城市起源”、第二廳“城市發展”和第三廳“城市智慧”的陳列展覽大綱。城市足跡館放眼世界各大博物館甄選相關文物,在國內外近30家博物館的支持下,300余件珍貴文物璀璨一堂;最后,結合高新科技、虛擬影像與文物互動,成功演繹了世界城市成長過程中留下的足跡所反映的人類的智慧和成就。其中,令上海博物館非常感激的是城市足跡館得到了以樊錦詩為院長的敦煌研究院的鼎力支持,值得驕傲的是一走進城市足跡館序廳,首先映入世人眼簾的文物就是“理想幻覺”展項中的“東方理想幻城——莫高窟”的洞窟壁畫場景、經卷和彩塑,充分演繹了敦煌壁畫中大唐城市的盛世恢弘與開放胸懷。
城市足跡館的精彩亮相使全世界得以共同領略世界城市文明的美學內涵,感受世界文化遺產的視覺震撼。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足跡館的序廳之中,敦煌研究院以數字影像技術提供的素材為基礎,復原了榆林窟第25窟和莫高窟第220窟洞窟樣式及其壁畫(圖1)。神圣的佛國凈土——敦煌,守候著東方的理想,譜寫了城市的華章。敦煌石窟中運用寫實手法創作的虛幻景象的凈土變壁畫,描繪了唐人理想中的世界,其中所展現的唐代城市風貌,勾勒出人們對理想生活的愿景。唐代的城市還對東亞其他地區城市規劃產生了影響,至今日本京都、奈良等地仍然保留著許多唐代風格的建筑與規劃格局。
在敦煌研究院復原的榆林窟第25窟和莫高窟第220窟洞窟一側的文物精品陳列室中,人們可以一睹來自敦煌研究院的10件唐代稀世遺珍:
1. 敦煌文獻《張君義勛告》(圖2),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27.6×155.1厘米,白麻紙。天頭、地腳殘缺,無界欄,行寬2.5厘米。共4紙,總50行。本卷中部因血漬粘連,揭取時,前32行每行缺損1—4字,所幸倒數第5行基本不缺,第15行一字不缺,遂使全卷不至斷裂。原收藏者張大千先生曾將其帶到日本加以裝裱。1941年張大千先生得此件于莫高窟窟前沙堆中,并為《張君義告身》寫了題簽:“景云二年右驍騎尉張君義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勛敕文”。
2. 敦煌文獻《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25.1×158厘米。佛經寫本。硬黃檗紙,無頭有尾,起“時有波羅”,共有經文80行,行17字。卷末有后人書“上元初……琳瑯記”題記。
3. 敦煌文獻《說苑·反質篇》,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28.6×383厘米。漢代雜事小說集,劉向撰。此件首殘尾存,自“秦始皇既兼天下”起,至“欲無窮可得乎”。存185行,每行19—24字,尾題一行“說苑反質第二十”。
4. 《妙法蓮華經》經卷,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22.8×845.3厘米。紺紙銀欄金字佛經寫本,即用金泥為墨書寫于深藍色磁青紙上,金字藍紙銀欄相映奪目。此卷為《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首尾完整,總509行。
5.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經卷,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25.5×195厘米。佛經寫本。首尾俱全,共107行,每行17字,少數18字。烏絲欄線細色淡,題記“天寶十五載八月廿日扈一娘為亡父母寫”,黃皮紙。
6. 木雕六臂觀音像(圖3),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至五代時期,124×36×28厘米。頭和身軀由整塊楊柳木雕刻而成,頭部多半燒毀。戴胸飾,X型瓔珞穿入鎖扣,再從鎖扣兩側穿出,繞成環狀飾物,后又穿回垂至腳下,著裙和帶有鋸齒狀邊飾的腰衣,裙帶在腹前結成大花結然后下垂至腳部。現殘存左二臂、右三臂(其中一臂只存上部)。從其后殘余痕跡判斷,此像為八臂十一面觀音像,是敦煌遺存為數不多的木雕之一,據藏經洞發現之前的兩位探險家的記錄可知,敦煌莫高窟內也曾有木雕佛像。后伯希和盜走了很多,這尊幸免于難。
7. 彩塑供養菩薩像(圖4),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51×18.5厘米。此像面容圓潤清秀,雙臂平舉,惜雙手毀。戴瓔珞、臂釧,胡跪于仰覆蓮臺上。
8. 供養菩薩,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64×29×20厘米。此像束高髻,面廓豐圓,雙眼下視。上身披巾袒露,戴瓔珞,著羊腸裙胡跪于仰覆蓮臺上。表層敷彩脫落,發髻頂和雙手缺毀。
9. 彩塑天王立像(圖5),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79.5×24×21厘米。天王立于泥臺上,身穿鎧甲,頭戴兜鍪,右臂屈肘握拳,圓目怒睜,面向左側。左小臂、左足缺毀。
10. 菩薩立像,敦煌莫高窟出土,時間為唐代時期,71×21厘米。無首菩薩,左臂自然下垂,右臂屈肘,惜雙手毀。上身半裸,披彩帶天衣,下著貼體彩色長裙,腰束裙帶,立于泥臺上。
敦煌藝術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的甘肅館內同樣復原和展示了莫高窟第45窟。敦煌研究院請專家按照1∶1的比例復制了莫高窟第45窟。第45窟受到的破壞較少,保存得較為完整,雕塑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亦堪稱經典。敦煌第45窟的原窟營建時間為盛唐時期,據介紹該窟正壁開一個平頂敞口龕,塑像七身,體態各異,個性明朗。栩栩如生的塑像和壁畫中刻畫精細的各種人物形象,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風貌。
三敦煌藝術的數字傳播
保護、研究和弘揚敦煌石窟是敦煌研究院的神圣職責,以數字敦煌為平臺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是當今網絡時代賦予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使命。敦煌研究院受國家文物局委托,管理保護古代壁畫,成為國家文物局的重點科研基地之一。作為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依托單位,敦煌研究院還設有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工作,敦煌研究院已發展成為國內外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遺址博物館、敦煌學研究基地、壁畫保護科研基地,為敦煌藝術的數字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自然和人為因素的雙重作用下,敦煌的彩塑和壁畫無可避免地在緩慢退化,如何能夠讓后代仍然能夠領略莫高窟的神韻?面對窟內眾多的參觀者,又怎樣破解保護和利用之間的矛盾?對敦煌藝術本身的研究,又該如何推陳出新?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猶如一縷明媚的科技之光,照進古老的莫高窟,為破解這些難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技術手段。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導下,由大學、研究機構、科技企業各方聯手推進的敦煌數字化工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推進的。敦煌學數字化工作在以下幾個方面獲得了突出的成果:
1. 石窟藝術文物本體的數字化方面。石窟藝術文物本體的數字化工作主要是由以敦煌研究院為主的海內外各有關單位組織力量共同進行的,主要包括數據采集、圖像處理、輔助臨摹、復原、修復及演變模擬、虛擬展示(虛擬展示及漫游是數字化成果的重要體現形式)、信息檢索等。而采用大量的三維技術來進行這項工作又是其中突出的特點。文物的三維數字化包括:三維信息獲取、三維建模和紋理綁定等。目前適用的洞窟文物三維數字化技術概括起來有:數字攝影測量、結構光獲取和三維激光掃描等三大類。當然原始數據采集是三維數字化及展示的基礎,它為數據處理和制作提供基本條件。數據處理和制作包括數據的分類與組織,原始圖像色彩的校正和均衡,壁畫圖像的幾何校正,壁畫的拼接,拍攝環境模型的重構,各類實物的三維重建、整體校準與融合等方面。
2. 文獻的數字化方面。文獻數字化在這里除了指敦煌文獻的數字化之外, 還包括文物檔案這一特殊文獻資料的數字化。
3. 綜合信息數字化方面。敦煌學數字化問題的理論探索,為敦煌學的數字化道路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所謂綜合信息的數字化,是指基于石窟藝術文物、敦煌文獻、文物檔案、研究成果, 以及相關人物、機構乃至旅游信息等敦煌學學術資料信息中的多種乃至所有信息的數字化。
近十年來,敦煌研究院已對43個洞窟進行了數字化保存。到2015年,147個洞窟將完成數字化保存。利用這些數字化資料,還制作成了形象逼真的數字電影和球幕電影。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還可對已損壞的壁畫、彩塑進行“還原”處理。通過數字化手段,既可以讓被破壞的壁畫“重生”、已消失的彩塑“復原”,也可以使游客不必大量涌入洞窟,看看球幕電影,即能身臨其境。數字化手段還能檢測洞窟的現狀,敦煌莫高窟已經建立了“四位一體”的監測體系。“四位一體”監測體系包括:敦煌莫高窟大環境監測、敦煌莫高窟洞窟文物本體監測、敦煌莫高窟安全防范監測、敦煌莫高窟游客調查與監測。
敦煌,由此進入虛實結合的數字傳播時代。
“虛擬莫高窟”的建設是“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的重要部分。計劃總投資數億元的這一工程由保護利用設施、崖體加固和棧道改造、風沙防護及安全防護等四個部分組成。用樊院長的話來說,這是“莫高窟文物保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一項綜合性保護工程”。虛擬技術在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包括游客接待大廳、數字陳列廳、數字影院、球幕影院等。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是一座極富想象力、充分考慮環境影響的建筑,不規則的外形“就好像戈壁中自然形成的流沙那樣”。采用大尺寸球幕電影來展現莫高窟洞窟,這在國內博物館中屬于首創。位于314國道南側、太陽村東500米處的服務中心距離莫高窟石窟群約有15公里。建成后將成為未來觀眾造訪莫高窟時的第一個“前進基地”。服務中心最核心的內容,無疑是“虛擬莫高窟”。專家介紹,通過數字展示技術,游客可以“身臨其境、細致入微”地觀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畫,還將“在這個中心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乃至整個敦煌的歷史文化背景”。游客服務中心的建成將使敦煌研究院多年來積累的眾多“數字洞窟”首次在公眾面前得到系統的展示。
“數字洞窟”是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梅隆基金會、美國西北大學共同開展的“數字化敦煌壁畫合作研究”的成果。項目完成了莫高窟及榆林窟22個洞窟的數字圖像,虛擬漫游洞窟5個。在 “數字洞窟”中,動畫片般的生動畫面,使人置身其中,能有真切的感受。特別是由于采用了360°全景式模擬的方式,讓平常游客參觀時無法欣賞到的部位,比如佛像的背部,以及洞窟的后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通過不同方式的操作,還可以選擇將四壁上的壁畫“拉平”,宛如觀看一張平鋪著的古畫,使人能更好地理解這些連續繪制的壁畫的故事結構和藝術布局。當然,建設數字洞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實體洞窟,以及讓游客獲得更多的旅行附加值,并不會影響洞窟本身的開放。未來游客在赴莫高窟參觀時,首先會在游客服務中心的虛擬漫游廳觀看典型洞窟的展示,再由專業導游帶領參觀實體洞窟。在虛擬漫游廳中觀眾能細致入微地觀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畫,還可以利用多媒體展示,滿足多種參觀需求,獲取更多的敦煌文化信息。
傳播知識是博物館的職能所在,數字敦煌的建設為敦煌藝術更廣泛地傳播提供了可能。2013年底,“煌煌大觀——敦煌藝術展”在浙江美術館開幕,由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研發的3D莫高窟(序廳)受到了觀眾的厚愛。這是一次多媒體新技術與文物保護及展示相結合的嘗試。該展覽是由各領域專家歷時6個月,利用虛擬實景技術,以立體動畫輔以數碼音響效果呈現的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參觀者站在跟真跡同尺寸的投影廳內,透過360°環繞屏幕欣賞第220窟內的高大佛像、精巧裝飾和靈動舞者畫像。而藥師佛頭頂的華蓋、壁畫上的舞者及古代樂器也會以三維立體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參觀者還可以通過戴上3D眼鏡及“虛擬手電筒”,模擬感受實地用手電筒參觀洞窟時的過程。出于文物保護考慮,在敦煌原址這一洞窟很少對公眾開放。而數字虛擬技術使這一洞窟成為本次展覽的亮點和熱點。
可以說,敦煌的數字化工程代表了數字化時代敦煌學發展的新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 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 敦煌學數字化工作也在海內外迅速展開, 并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不但涌現出了大量的數字資源, 而且在相關理論的探索方面也成績斐然,它將為敦煌研究再上一個新的臺階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此,真誠祝愿敦煌藝術與敦煌研究院相映生輝,兩者所彰顯的文化力量映照寰宇。
收稿日期:2014-05-20
作者簡介:陳燮君(1952—),男,浙江省寧波市人,上海博物館館長。
Keywords: Dunhuang art; Dunhuang Academy; Cultural inheritance; Expo interpretation; Digital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