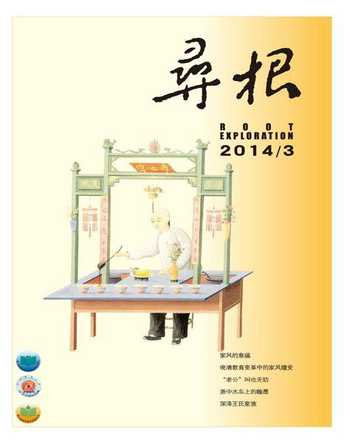18世紀中日家訓比較
楊陽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相通。自從《顏氏家訓》在平安時代傳人日本,日本人就借鑒了家訓這一家庭教育形式。此后,盡管日本與中國在文化上仍有聯系,但由于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家庭結構和家族生存模式的變化,家訓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一
18世紀的中國,正處于康乾盛世。經濟繁榮、人口增多的同時,統治者逐步開始實行閉關鎖國。但是,商人的往來以及城市文化的發展,使得社會分層更加多元。這一時期,傳統家訓的各種形式,例如專著、詩歌、規條、書信等,都被繼承下來,整個社會上至皇室下到平民,都非常重視訓家教子。
如果把歷代家訓的數量用線形圖來表示,18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頂點。與前代相比,特別是與宋以前的家訓相比,這一時期的家訓,對社會大眾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更明顯。在內容上,這一時期的家訓也不只是談理論,而是更注重可操作性。現存資料表明,隋唐及以前的家訓,更多地集中在貴族家庭中。這些家訓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相對較弱。而宋代以后,由于士人家訓的興起,以及家族組織的日漸嚴密,家訓中的思想,影響了千家萬戶。進入明清,連長期不受重視的商賈家訓,都得到了長足發展。到了18世紀,家訓的思想滲透能力更是無孔不入。
18世紀的日本,正處在江戶時代,閉關鎖國政策已實行65年。人口和耕地面積增長很快,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分離。“城下町”遍布全國,以商人和手工業者為主的町人階層日益壯大,商家家訓和農家家訓因此獲得了發展。由于皇室和貴族的衰落,公家家訓走向衰落。而隨著武士對政權影響力的增加,武家家訓日漸繁榮。女訓書的集大成之作《女大學》也在18世紀誕生。從典型性和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主流家訓是武家家訓和商家家訓。
最早的武家家訓是誕生于13世紀的《北條重時家訓》,它的內容抽象,佛家色彩濃重。到室町幕府時期,武家家訓開始注重實用,內容變得簡明扼要。戰國以后,家訓訓誡的對象擴大,雖也強調入倫,但是更注重戰斗,例如《武田信玄家法》里就有不少軍事內容。之后,江戶時代天下統一,社會安定,家訓的風格變化極大。由于朱子學在日本成為官學,家訓中對于品性修為以及身份差異的論述越來越多,同時,家訓中依然保留了普通武士的基本教訓。可以說,18世紀的武家家訓既重視理論,又重視實踐。
商家家訓出現于武家家訓之后。在17世紀,商品流通穩定,商家才在借鑒武家家訓的基礎上,或請學者代筆,或自家總結創作,慢慢發展起來。進入18世紀,大商家由創業時期進入擴大再生產或守成時期,商家家訓開始興盛。到了18世紀后半期,中小商家也開始制定家訓。家訓中包括經營理念、日常用度、教育管理、人力配置等,還出現了《店規》《店則》等附錄文獻。可以說,18世紀的商家家訓,為后世日本企業的家訓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
由于江戶時代的官學是儒學,所以,18世紀的中日家訓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礎。對于治家關鍵的論述,也都有一致的看法。
中日兩國的家訓,都是為了冀望“家”之長久。而組成家的基本元素是人,因此,人的素質培養,也就是家庭或家族成員的“修身”得到了高度重視。健康是修身的基礎,因此,18世紀的中日家訓有很多涉及“養生”的內容。康熙皇帝在《庭訓格言》里不僅有對延醫看病的論述,還有很多對日常保養的經驗總結。他訓示子弟:“人能清心寡欲,不惟少忘,且病亦鮮矣。”張英關于養生的家訓,比康熙帝還要詳盡。他告誡弟子:“臟腑胃腸,常令寬舒有余地。”細川重賢也認為“為人不養生則失天命,鳥畜饑而暴食而亡,人貪享美味則脾無病”。
修身的另一個法門,就是“事事從讀書起”。康熙帝認為讀書當“以經書為要”。《高氏塾鐸》第一則就是“好讀書”。《霜紅龕家訓》則大多是談讀書的。總之,與其留給兒孫十畝田,不如送他們多讀一年書。18世紀的日本家訓,《德川光國教訓》開篇第一句就是“讀書之事,此前亦曾有言,于自身大有益處”,并強調“讀書要下功夫”。室鳩巢則在《明君家訓》中主張“讀書當以古之圣賢言語為要”,他認為“四書”“五經”需要“字字句句深思徹悟……方為真學問”。
在治家方面,中日兩國都首重孝悌治家。幾乎每個家訓都會提到與孝悌相關的內容。清人的《白公家訓》開篇就說:“孝悌通神明,言行動天地。”康熙在《庭訓格言》中說“真孝”就是要“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張英在《聰訓齋語》中以“孟武伯問孝”的例子,來說明大孝的方式是:“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張履祥還在《訓子語》中講了不孝的表現:“私財有無,所系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于親,不欺于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在日本家訓中,《伊勢貞丈家訓》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就通過講“五常之事”和“五倫之事”來詳述“孝行”和“為悌”。日本的《明君家訓》中也明確要求:“對于父母要竭盡孝順,兄弟竭盡友愛。”伊勢家的家訓認為“萬事以父母喜歡為要。縱然父母不良,無端虐待,亦不忿怨憎恨,愈發善事以博其歡心,方為孝行”。家族中的兄弟相處,和姊妹相處的道理是一樣的:“為兄事事行于弟先,引領照應;為弟事事居兄之次,跟隨無悖,尊敬善事。”
中日兩國家訓關于治家方面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勤儉持家。鐘于序在《家規》中專門用“勤本業”和“崇節儉”兩則來告訴子孫“勤儉持身,更可漸漸充裕”。《高氏塾鐸》中講“勤有三益”,“勤則不匱”“勤可以遠淫僻”“勤可以致壽考”;“儉有四益”,“儉可以養德”“儉可以養壽”“儉可以養神”“儉可以養氣”。日本家訓同樣崇尚勤儉。《伊勢貞丈家訓》說:“衣食住之本意,不可奢侈。”家訓中還有名為“儉約之事”的部分來論述治家要“寬緊適度、取其得當,是為儉約”。《肥后侯訓誡書》中則說:“所謂儉約者,無論貴賤,當一意省儉,不使生民艱澀,莫生龐大出費,以致一國運衰遺恨。”《住友長崎店家法書》規定:“店內生活萬事宜行簡素,朝夕食事一菜一湯,不許喝酒。”《本間家家訓》的規定更加詳細:“清晨六時起床。”
此外,中日兩國的家訓,都非常重視交游往來。清人李淦的《燕翼篇》就有“取友”“親戚”二則來專門論述交游原則。張英則訓誡子弟說,“人生以擇友為第一事”。同一時期的日本,對于親族,《明君家訓》要求“親敬和睦”,對于“旁輩”,要“以信為本”。要與“固守節操”“人品貞信”的人交往。《伊勢貞丈家訓》中認為“與朋友交”和“與奉公之同僚交”,都要“真心待人、誠實可靠”。
三
與相同之處相比,18世紀中日家訓的不同之處更多。第一,訓誡對象的不同。清人家訓中,多出現“子弟”“諸祖”“諸父”“兒女”等訓誡對象,均是針對有血緣關系的對象來教訓的。日本的家訓雖然也有“子孫”“親戚”等對象,但“家中之士”“諸士”“全員”的稱呼更常見。訓誡的對象除了嫡系子孫,還有養子、家臣、手代全員等。例如:《宗利家訓》就要求嫡系子弟在聽課時,手代全員也要跟著學習。也許正是這種開放性的特點,使得日本家訓在進入近代社會之后,依然能夠被運用于企業的管理。
第二,在語言上,18世紀的清人家訓,多是文人所作,言語優美、邏輯清晰,甚至可以當美文來閱讀。類似“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是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閑便是主人”這樣的句子不勝枚舉。還有的家訓引經據典、繪景描態,頗有古文之風。而日本的家訓大多言語淺近,注重敘事。在文章邏輯上,前后重復的內容很多。大概是作者考慮到訓誡對象的文化水平,因此語言比較直白簡單。
第三,若以人的“一生”為單位來比較讀書為學的次第,中日家訓的差異也很明顯。清人認為“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一是因為孩童的記憶好,二是為了寫的文章能更有思想內涵。等到二十歲左右,為了作文,才開始接觸一些相對簡單的時文。等到年紀大了,著書立說、教訓兒孫,常看《老子》《莊子》《周易》,又步入了為學的一個新境界。整體而言,是一個“難易難”的過程。也許是因為翻譯的原因,日本人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和清人不同。《明君家訓》中認為追求學問,應當先要熟讀《小學》、“四書”、《近思錄》之類,之后為了修行,求得真學問,就“若有余力,可及于‘五經一。對于四十歲以上的人,“精力鈍減”,只讀前三部書就可。對于六十至八九十歲的人,“僅《大學》《論語》,或擇其一”。大體上,是一個“易難易”的次序。
第四,18世紀的中日家庭,對于子孫就業擇業的觀點,也不相同。雖然這一時期商人的地位上升極快,但是多數家庭還是只提倡“耕讀”。鐘于序在《宗規》中講: “漢設力田之科,與茂才并重。農列四民之次,視工賈為先。”這種情況下,除了教子孫讀書,也會讓他們學習一些“田界”“塘堰”“農夫用力”“林木耗長”的知識。而同一時期的日本,擇業和就業,是已經注定的。 《明君家訓》中說: “天下人分士農工商四色,各司其職。”農、工、商三民“皆致用于天下”,士的職責只是“義理一事”。也就是說,一個人若屬于農家,他的事業就是種田,屬于商家的人,就只能做買賣。《宗利家訓》中甚至直接表明“不得從事本業以外之商賣”。
第五,中日家訓對待神佛的態度,幾乎是大相徑庭。清人家訓中只有不到一成的內容涉及了“神佛”。但是,讀佛經要在“經史正課之暇”,不能“貪信福報之說”,“而矯揉造作,修橋修寺,便是愚昧”,甚至對“賽會迎神,罔念室家懸磬”持強烈的批判態度。這與日本的“虔敬”態度差異極大。在18世紀的日本,《伊勢貞丈家訓》中專門設有“神佛之事”一則,同時告誡子孫:“善守人之操行,來世必能成佛。”為完成祈愿,本間家的《第三代光丘自戒三十條》規定:“念佛二干五百次,每天不可疏漏。”第十條規定:“今后應對神佛勤加禮拜。”在這份家訓的末尾,還強調“上述總三十條,今后應懷佛心而遵守之……早餐之前于佛前禮拜,內外萬事不得隨意。遵守先祖教訓,常思佛恩及國恩之深廣”。本間家兩百多年的傳承,沒有發生一件佃農爭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借“神佛”來理家,確實有有利的一面。
四
中日18世紀的家訓,基本都是為了“不墮家風”,保“家之長久”而存在的。這些家訓,有些是遺言,有些是作者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雖是“老生常談”,但是“其言也善”,為后人良好家風的培養,提供了捷徑和良方。
整體而言,在儒家經典的影響下,中日家訓都首重品德修養。把修德看作是“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便是傳家的法寶。因此,要“崇節儉”“禁賭博”,培養健康環保的財富觀念。又因為“家之不幸,莫如不肯教子弟”,所以中日都重視“勤讀書,嚴教子”,都主張“學無常物,亦無常地”,要求子弟和家臣接受做人做事的教育。此外,對讀書學習的道理還要“身體而力行之”。“不克自立”,只能是“辱其身,以及其親”,更別說“教子孫,傳家風”了。
18世紀中日家訓的差異,主要集中在細節方面。中國的家訓主要針對的是家庭大環境的建設。治家的人,要能夠“和鄉黨”“恤窮困”“行方便”“勤本業”“賞罰分明”。而日本的家訓則更多地針對個人小環境的選擇。比如《宗利家訓》中就要求子弟,“凡游樂場所,四十歲以后方得入”。類似這樣的規定,都是以“條文”的形式呈現,全面而又細致,展現了與中國家訓不同的氣質,也表現了日本家訓嚴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