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者獨難
孫郁
六年前去紐約開會,在哥倫比亞大學討論魯迅的話題,席間許多人的發言很有分量。遺憾的是那天夏志清先生沒有來,失去聽他講演的機會。不過,我印象里,他可能對魯迅有另一番看法,對于大陸魯研界的人,有所隔膜也是自然的。我后來幾次去紐約,都未能見到他,所以,一直是心存遺憾。談起夏先生,只能是文字里的形象,余者,則不甚了然的。
我讀夏先生的著作不多,除了《中國現代小說史》外,還有幾冊新文學作家論的書。不過,我們所常見的他的作品,多有刪節,所以對其思想本意,不能細細究之。他的文章不那么華貴,屬于切實的那一種。但有時句句有力,是直接切入本質的文體。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大陸像他那種治學的人,長時間是看不到的。
自從《中國現代小說史》傳入大陸,學界的看法一直不一,贊許與批評的都有。至今都糾纏著學界的神經。他最大的價值,是引入了另類的理念和治學視角,先前單一的文學批評觀與史學意識顯出自己的問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其思考恢復了文學的生態,把遮蔽的存在,一一還原出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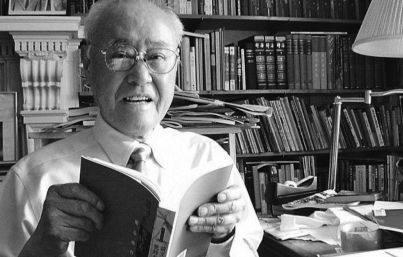
中國的現代文學史,過去以左翼的邏輯為之,意識形態的因素濃濃,一些作家便不能浮出水面。夏志清把錢鍾書、張愛玲等人寫進文學史,且給以相當的位置,不僅是見識不凡,也有與左翼對立的用意。因為是冷戰的產物,也難免不輻射出自己的偏見,這是談論文學史的人,都注意到的問題。現在大陸文學史寫作的進步,與吸收夏氏的思想有關,他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投射在相應的領域。
我最早看他的書,覺得視角很有意思。他不是從外在的流行的觀念去判斷問題,喜歡以差異性眼光看世。加之有西方文學史的維度在,處處對比,時時照應的意識潛在于文本里,這是大陸研究新文學者最少有的。50年代治現代文學史的,左翼的學者較多,王瑤、唐弢都有左翼情結,且不太懂西學,他們的書遺漏了一些自由文人也在所難免。曹聚仁后來在香港寫《文壇五十年》,精神是自由主義的,底色不同于王瑤諸人,而依然是在漢語的圈子里盤旋,缺少對西學的吸收。夏志清寫小說史,一是在遠離故土的地方,有超時空的味道,可以細細品味其間味道。另一方面,對總體的情況,有得失之辨,尊重的是個體的印象,批評的銳氣總是有的。
在夏志清的潛意識里,文學史家應是批評家。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那核心的元素就是文本的鑒賞。因了這個思路,就從意識形態和一般史學的框子里游離出來,表現出文學鑒賞的趣味。這樣,他的研究體例,就和傳統的史學有些差異,眼光是現代的靜觀式的。又因為自己有遠離左翼的自覺,其文學史的格局,以肯定個性為主,私人的空間里的獨白頗多,自然有諸多的發現。他對一些作家的描述,精準、深切,不動聲色的地方頗多。能從文本看出內在玄機,以舊筆法寫新感覺,審美的基調是有趣的。他看重作家文本中的力量感,于肅殺里悟出玄機,暗里時常三致意焉。夏氏的小說史發現了幾位大陸學界忽略的人物,對他們的介紹都心平氣和,在論述上自稱一路,有規有矩。這里看出他的興趣,筆墨有酣暢之處,對學問與智慧籠罩下的審美趣味的把握,令人眼界大開。比如他談作家的文體感,就頗有眼力,能夠從學問的角度得其妙意。現代小說家有政治上的焦慮,現實的態度明確,一面也失去精神的靜觀,在審美上少了含蓄與博雅。他認為好的作家的作品,完全沒有這些,視野是人類學家般超然。夏志清對此大為贊許,以西洋小說史為參照,細陳其內在隱喻,史家態度與美的體味飄動于書中,這對后來大陸的沖擊是超出他自己的預料的。
從他的視角里,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對現代文學的平視的態度,在穿梭中有驚奇,也多失望。不是從敬仰的角度為之,而是近于挑剔地看人看事。他認為現代文學缺少西洋文學的境界和情懷,都不是胡言,歸納里的沉思給我們些許多思考的空間。在談及小說史的寫作時說:
20世紀西洋小說大師——普魯斯特、托瑪斯曼、喬伊斯、福克納等——我都已每人讀過一些,再讀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挖掘。這不僅是心理描寫細致不細致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小說家在描繪一個人間現象時,沒有提供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
這個批評未嘗沒有道理。我們治現代文學史的人,多是王婆賣瓜,不太說研究對象的問題,這可能帶來一定的偏狹。他最為可貴的地方是,在面對研究對象時,有種從容的感覺,仿佛是俯視一般,知道自己該說什么,分寸在哪里。小說史開篇講《新青年》的辦刊理念,對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人的描述都很精準。看出新文化理論的內在矛盾和蘊含的問題。他對陳獨秀理論缺失的把握和對胡適審美盲點的批評,都有力度,且頗為中肯。夏志清是帶著問題意識來審視文學史的,其間也含著一種文化的痛心。一個遠離故土的學者在清理與自己生命相關的歷史時,看的出苦樂參半的感覺。我們在其著述里,不斷與這類感覺相遇,已經不再是知識的獲得,而是經歷著思考的焦慮。小說史能夠讓人產生獨立思考的沖動,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就治學而言,夏先生的勞作可謂功莫大焉。
因為要竭力與大陸的文學史表現出不同的色調,他的體例與章節間的內容銜接似乎不及王瑤、唐弢系統與豐富,一些材料也相對稀少。他對通俗文學與大眾寫作的遺漏,也使全書缺失了什么。左翼小說固然缺乏精致的審美意味,但何以如此有影響力,以及其演進的內在邏輯何在,他都沒有細細關顧,這都是被后來的學界詬病的所在。但他的出色的地方在于審美判斷。在言及老舍、巴金、沈從文、張天翼時,顯示了良好的感覺,一些基本的判斷都未出格,且有鮮活之感。我們在其字里行間有時能夠感受到他的苛刻和嚴明,而每當有新的發現則筆墨縱橫,興致不減。在對錢鍾書的描述里,整體顯得獨到、深入,文筆流出愜意,有對學問與審美的雙重的尊敬。夏志清判斷小說的標準是智性的有無,并不被外在的觀念所囿。談及《人·獸·鬼》時,作者寫道:
閱讀這篇有趣的諷刺幻想,我們察覺到錢鍾書與他所模仿的詩人的確相似。像德萊敦、蒲伯和拜倫一樣,在故事中他對充塞當代文壇及樹立批判標準的愚昧文人顯露出一種表示貴族氣骨的輕蔑。他很像是英國十八世紀早期蒲伯這一派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為反浮夸、疾虛妄的理智與精確明晰的風格作以身作則的辯護。
錢鍾書的文本一定是在根本的層面上喚起了他的共鳴。這在對《圍城》的解析中表現得更為充分。他說這部作品是“浪蕩漢”(Sophia Western)的戲劇旅程路,令人想起《包法利夫人》的象征。小說的游戲筆墨是頗為精彩之所在,一般人不太會如此智慧的運用此法,錢氏的嘗試給了他諸多刺激,感受到雙關語(puns)與明喻(similes)的內在價值。這恰是夏志清要尋覓的所在,他因為這一發現而歡欣鼓舞,以致給了錢氏很大的篇幅,全書的結構也因之不那么均衡了。
夏志清對許多人的評價很是得體,知人論世的幽思閃現在不動聲色的陳述里。最精彩的還是對張愛玲的評論。他從張愛玲“蒼涼”的意象里讀出中國戲曲里的隱喻,也感悟到《紅樓夢》里的余韻。但他不是僅僅糾纏著其背后的歷史之影,看重的是她創造性的一面,即她與傳統和現代人不同的獨一性。張愛玲寫出了現代人的荒涼感,這一點與魯迅頗為接近。但那荒涼背后又有誘人的美質在,何以如此?夏志清覺得乃是作者對環境的敏感。聲音、色彩包裹著可憐的人們。灰蒙蒙的街市,冰涼的月亮,以及幽暗里的惆悵,都在那畫面里流動出來。這一切與曹雪芹筆下的世界很是接近,但又有《紅樓夢》里所沒有的元素。夏志清的解釋是:“《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個靜止的社會,道德標準和女人服飾從卷首到卷尾,都沒有變遷。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僅強調優美和丑惡對比,也讓人看到在顯然不斷變更的物質環境中,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持續性。她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現在——這種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高度贊美張愛玲,其實在襯托左翼作家的表面化的淺薄。他沒有看到積極參與社會改造的作家的另一種價值,這固然有一個自己不易變動的尺子有關,但把審美的標準固定化也給他的研究帶來局限。《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文學格局的感覺不及文本感覺好。后者不都獲得譽詞,批評的話頗多。這都是閱讀的原始感覺,鮮活得帶有溫度。他譏諷郭沫若、郁達夫,未嘗沒有道理,而面對巴金、老舍,內覺的分寸是顯然的。夏志清在大陸被詬病最多的是對魯迅、茅盾的態度,批評他的文字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這是他的價值觀的流露,和王瑤的立場恰好相反。如此說來,他們各自在一個方陣,要跳將出來,的確大難。我覺得他對魯迅的感覺,還停留在初步閱讀的基礎上,他在小說史里對魯迅的創作的總結,缺少許多環節,對晚期的《故事新編》竟然草草描之,且不耐心,沒有談論錢鍾書、張愛玲那么投入。不過,他概括魯迅的偏激思想,多少有自己的道理,乃那時候知識界的另一種聲音,對校正大陸的極左的表達,亦有價值。先生后來對魯迅的判斷,顯然還是有些變化的。
我想,他對魯迅的態度,大概與其知識背景及自我的價值觀有關。魯迅的復雜性以及其翻譯實踐、整理國故的歷史,他了解有限。未能從更為廣闊的時空里審視魯迅,也恰恰證明了普實克對其批評的合理性的一面。夏志清對自由主義作家有理解的同情,到了左派那里則有些內心不平,不能冷靜為之,這是他那時候信念的外化。所以我一直覺得,研究現代文學史,要把他和王瑤、曹聚仁的作品對讀,才可以看清一些問題。顯然,魯迅文本提供的空間,遠遠大于錢鍾書、張愛玲等人。左翼文學史家先前的判斷雖然有武斷之處,而在這一點上,乃不刊之論。
現代小說史的寫作,難度很大,至今人們依然在苦苦摸索表達的路徑。我們的學者要面對許多自己不熟悉的文本,保持中立的態度不太易做到。要深入解析作家的世界,需要耐心和寬容的態度。夏志清對左翼作家的描述,有精彩的地方,也有簡化的地方。那些評論有的原于細讀的偶得,有的受到別的批評家的暗示。比如他談趙樹理,對《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評價不高,而喜歡《李家莊的變遷》。這個看法與周揚恰好相反,他是因為看到周揚的論述后生出反感而得出結論的。其實趙樹理在小說里植入了諸多社會元素,對社會關系、文化遺存與革命活動,有比較復雜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說,他還是一個高人。夏志清因為不滿周揚等人的理論而簡化了對趙樹理的認識,這很是可惜。類似的問題在對其他作家的描述上也有,他后來大概也意識到了。
《中國現代小說史》問世后,評價不一。贊之者以為頗見功力,批評者則視其存在嚴重的偏見。典型的是普實克對他的批評。在普實克看來,夏志清的史學觀存在盲點,主要是對中國的革命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同情。夏志清后來有一篇長文作過自辯。他的回答似乎也勾勒出文學史的基本觀念。夏氏以為,中國文學的研究不能被史學家的信仰所左右,使命感與社會功能不及文本閱讀的結論更為重要。文學史與小說史首要做的是對文學文本的梳理,而不是看作家的傾向如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審美判斷的合理性。從這兩個人的爭論里,看出20世紀文學史研究的不同路向。夏志清代表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性,在后來的歲月得到的呼應一直沒有中斷。
小說史研究要面對文本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考慮作家的立場與輿論環境,可能會把歷史的描繪瘦身化。即便是面對失敗的文本,也要點綴出其失敗的原因。20世紀的文學,意識形態的因素破壞了審美的純粹性,但也不能漠視這一意識形態本身也成了文學史的一部分。許多意識形態也有其學理性,如果史學研究以學理的眼光看待擁有學理因素的存在體,它的學術性可能更濃厚些吧。
我自己覺得,小說史乃讀書人個人偏好的產物,客觀的描述不易做到。其實現代中國的文學,談起來很難。再過百年,后人的看法亦會有所變化,這是難免的。問題不在于對錯,而是提供了一種方法和視角。王德威說,夏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使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變;后來者必須在充分吸收、辯駁夏氏的觀點后,才能推陳出新,另創不同的典范”。其實,王德威所說的,今天的學界已經在慢慢實踐著。
夏志清去世,帶走了一代人的故事,而他給我們的記憶卻久存于世間。他的文字生涯看似平靜,卻因了與無數思想者與作家的對話,而有了流動的光澤。思想是寂寞者的果實,人們所發現的美還不是很多。我現在授課的時候,常常提起這個老人,不因別的,乃是告誡自己,在眾人喧嘩之際,靜者獨難。百年中國,趨同者甚眾,“大獨者”寥寥。先生治學與為人,其路相近。學術亦是人生,年輕的時候不太理解此話,于今想想,還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