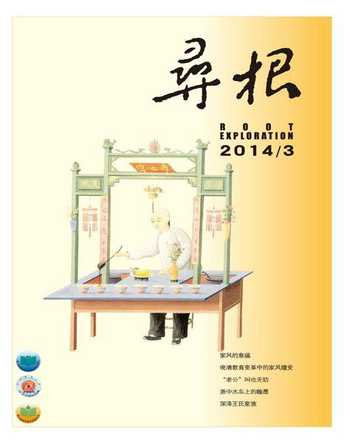略談客家婦女
陳海斌
提到客家婦女,有的人會想到身著藍衫、頭戴竹笠、扎著雙辮的小姑娘,或是扎著頭巾、圍著圍裙的老婦人,有的人會想到客家女人的那雙天生的大腳板,也有的人則會想到她們會耕田把犁。自古至今,夸贊客家婦女的溢美之詞常見諸文人墨客的筆端,人們不免好奇,甚至覺得有些神秘。客家婦女與其他民系的婦女到底有什么區別?為什么會被大書特寫?筆者研究客家文化,特撰此文,為您揭開客家婦女那神秘的面紗。
說客家婦女神秘,其實并不神秘。從外表上看,客家婦女與我們身邊的婦女不存在什么差別;而客家婦女長相差別也不是很大。如果要說區別的話,筆者以為客家婦女和其他婦女的最大區別恐怕在于客家婦女更為勤勞、簡樸、天勁健放。
客家婦女的大腳板。客家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是歷史上中原漢民為躲避戰亂漸次遷入贛閩粵三角區,經過長期與土著和畬、瑤等少數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人數上、經濟上占優勢的客家民系。客家婦女與其他的婦女相比有一雙天生的大腳板。客家婦女不纏足,如北宋詩人徐積就注意到了客家婦女不纏足,“但知勤四肢,不知裹兩足”(徐積:《詠泰家婦女詩》)。美國傳教士肯貝爾也記載了客家婦女的不纏足, “婦女不纏足,通常體健而軒昂,唯其如此,故能過其戶外生活”(肯貝爾:《客家源流與遷徙》)。在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眼中,纏足是女性審美的標準,那么客家婦女為什么不纏足呢?
首先,客家人基本上居住在山區,吃山住山,因此有“無山不住客,無客不住山”之說。客家人生活的環境為山區,天高皇帝遠,遠離中原王朝的控制,這可以說是客家婦女不纏足的政治因素。其次,客家地區生活著畬、瑤等少數民族,他們就保持著不纏足的習俗,在經過長期與畬、瑤等族經濟、文化交流,甚至是互通婚姻后受其影響,也開始不纏足。再者,客家地區男人外出謀生,婦女獨自在家侍奉公婆,為了生計,必須里里外外一把手,耕田把犁,承擔一切家務活動,這就要求客家婦女們必須要有良好的勞動能力,而纏足則是一個很大的束縛,這應該是客家婦女不纏足最主要的原因。
勤勞的客家婦女。客家婦女的勤勞,恐怕其他民系的婦女無法望其項背。客家婦女的勤勞歷來備受夸贊,如在方志中就有記載“婦女裝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針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論貧富皆然”(乾隆《大埔縣志·風俗》)。《清稗類鈔》對客家婦女的勤勞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黃遵憲也有專門贊美客家婦女勤勞的言辭:“吾行天下者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行省歷其九,未見其有婦女者如此。”(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甚至連外國傳教士也極力贊美客家婦女,如愛德爾寫道:“客家人是剛柔相濟,既剛毅又仁愛的民族,而客家婦女更是中國最優秀的勞動婦女的典型……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這輝煌,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屬于客家婦女的。”(愛德爾:《客家歷史綱要》)這雖然有點夸大,但也說明了客家婦女的勤勞。客家婦女的勤勞讓世人贊嘆,那么她們為什么會如此勤勞,是什么原因造就她們的勤勞?
這與客家地區山多田少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客家地區自古就有“八分山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的說法。正是這種山多田少的自然環境,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生存要求,生存空間狹窄,生存資源缺乏,使得男子不得不出外謀生,下南洋、過番、經商、打工等。客家婦女留在家中,必須全力承擔起里里外外的所有事情,不得不下地干活,耕田種地,劈柴挑水,撫育子女,侍奉公婆。
客家婦女的勤勞還與客家地區久已形成的社會風習及輿論有關。在客家地區流傳甚廣的《客家婦女歌》就道出了婦女的艱辛,成為客家婦女學習的典范:
生女莫在古程鄉(今梅縣),
程鄉女子苦難當,別處女子深閨
寶,程鄉婦女耕田莊。赤腳落田播
種秧,潑糞施肥又脫秧,三月蒔田
挑秧把,中耕除草耘田忙。若遇老
天唔打幫,一夜戽水到天光,一直
忙到造禾熟,收割農事又緊張。早
造剛完秋季忙,又把番禾趕插上,
若遇高田水唔足,改種番薯唔丟
荒。十月立冬稻谷黃,晚造收割又
登場,程鄉婦女如六月,再把谷粒
屯中藏。兩造收完冬種忙,播下小
麥一行行,唯有小冬稍自在,等待
明春小麥黃。一年四季農事忙,程
鄉婦女非尋常,女子如同男子漢,
勤勞美德堪贊揚。
社會的風習和輿論要求客家婦女必須像《客家婦女歌》中說的一樣,勤勞能干,如有違反便會被社會所鄙視,這同時也是客家婦女的不幸和悲哀。在客家地區也有取笑偷懶的婦女的詩歌,如《懶尸婦道》:
懶尸婦道,講起好笑。半晝起
床,喊三四到。日高半天,冷鍋死
灶。水也懶挑,地也懶掃。發披髻
禿,過家去嬲。講三道四,呵呵大
笑。田又唔耕,又偷谷糶。家務不
管,養豬成貓。上圩出入,一日三
到。煎堆扎粽,樣樣都好。有錢來
買,偷米去教。老公打倨,開聲大
叫。去投妹家,目汁象尿。妹家伯
叔,又罵又教。爺罵無用,哀罵不
肖。轉不敢轉,嬲不敢嬲。送回男
家,人人恥笑。假話投塘,瓜棚下
嬲。當年娶她,用銀用轎。早知如
此,貼錢唔愛。
會唱山歌的客家婦女。客家地區遠離中原王朝的藩籬,受禮教文化的約束較淺,也造就了客家人天勁健放的品格和精神氣質。客家婦女也不例外,唱山歌就是很好的明證。客家山歌形式多樣,內容主要表達男歡女愛的主題,為士大夫所不齒,但就是這種草根文化孕育著客家的人文精神。客家婦女唱山歌,唱出的是對生活的期盼,是愛情的追求,是生命的贊歌。
節婦與烈婦。宋明理學在客家地區傳播,理學家所提倡的倫理觀念深深地印透在客家人的文化中,尤其是婦女的守節方面。學術界一般認為客家民系在南宋時即已形成(謝重光:《客家文化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受理學思想直接影響的客家地區受這種思想極為嚴重,方志中專門辟有“節婦”“節烈”“烈女”便是明證。據筆者統計,僅同治《贛州府志》“節婦”就記載200多位節婦,這些節婦產生的途徑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因為年輕時丈夫早逝,然后侍奉公婆,撫養子女,守寡幾十年,最后熬成祖母。也有的是因為丈夫早逝,自己被奸人凌辱而不從最后成為烈婦,縣志將其記載以旌其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