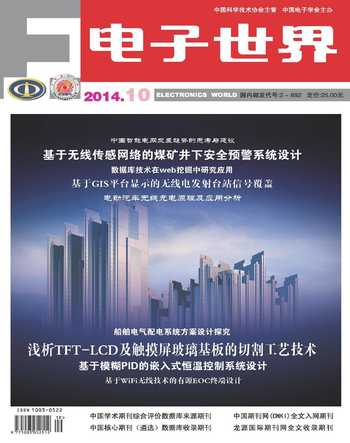淺談大數據時代的三大悖論
【摘要】大數據時代正在來臨,它深刻改變著我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樣態。大數據的支持者們用最美好的言辭描述著大數據時代的光明圖景。但對大數據的狂熱進行冷靜和批判性反思非常有助于大數據美好藍圖的實現,同時堅守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其中大數據時代的三大悖論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因為任何科技的進步都是一把雙刃劍。
【關鍵詞】大數據;透明化悖論;身份悖論;權力悖論
一、引言
早在1980年,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將大數據熱情地贊頌為“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最早提出“大數據”時代到來的是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麥肯錫稱:“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人們對于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① 大數據作為云計算、物聯網之后信息技術行業又一大顛覆性的技術革命。
大數據的熱情支持者們認為,大數據分析能力強大,可以為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提供全新路徑;而且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決策過程能夠給我們做出更準確的預測,如大學招生、企業用工,甚至于情人約會。它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保護珍貴資源、文化遺產和幫助治療致命性疾病,從而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安全高效。在他們看來,大數據的用途不僅局限于大型機構,隨著智能手機普及,手機和可攜帶傳感器能夠收集個人信息,讓“數據化自我”成為可能,為改善睡眠質量和提高健康水平提供保證。最新研究表明,對于個人信息的搜集,如在美國進行的大規模電話竊聽計劃,這些大數據還可以使我們預防恐怖主義襲擊。
瑞克·斯莫倫在《大數據時代的人類面孔》一書中開宗明義,非常肯定的指出:“大數據是一場非同尋常的知識革命,它悄無聲息、范圍廣大,涉及商業、學術、管理、醫療和日常生活等領域。……地球上每一個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物體不久都將數字化,包括我們的家園、汽車還有我們的身體。”②從這個信誓旦旦的宣言中,讓我們不僅看到了大數據的光明前景,還讓我們隱約感受到了它的潛在危險。然而,迄今為止,對于大數據的論述耽于溢美之詞,然而對它的潛在危險并沒有太多有意義的分析。所以,讓我們靜下心來以更加理性的批判思維來考察一下大數據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尤其想在當下對大數據溢美之詞甚囂塵上的氣氛中去強調大數據的三大悖論,以便幫助我們更徹底的理解大數據的未來景觀。首先是大數據時代,信息透明化要求與搜集信息秘密進行之間的悖論,我們稱之為“透明化悖論”;其次,大數據需要識別個人身份,而識別個人身份需要犧牲個人或者群體的身份隱私,我們稱之為“身份悖論”;第三,大數據是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的發揮是以犧牲個人權利,而讓社會中各大權力實體獨享特權,我們稱之為“權力悖論”。認清大數據時代危險與潛力相隨的悖論,將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這一偉大的信息化社會變革。它也能夠使我們去構思解決這些悖論的最佳方案,使得大數據擁護者們所預言的美好的未來真正成為現實。
二、大數據時代的三大悖論
(一)透明化悖論
大數據分析是建立在小數據輸入基礎之上的,它們可以為傳感器、手機、甚至于電腦鍵盤的點擊模式所搜集。這些小的數據聚集起來就組成了大的數據組,分析技術可從中尋求洞見和啟迪。然而數據搜集是在悄悄進行的,而且在不斷加劇。在未來從“物聯網”到“萬物互聯”,思科公司預計:截至2020年將有370億智能設備與互聯網連接。這些設備和傳感器驅動著指數級增長的移動數據流;2012年的數據流量和2000年相比,幾乎翻了12倍。高度安全的數據中心將這些數據集存放在高效能、低成本的設備中,能夠實時或近于實時的數據分析。
然而,這里就出現了透明化悖論。大數據承諾應用數據將使世界變得更加透明,但數據的搜集卻是在悄悄進行的,而且數據搜集技術和工具也是不見光的,隱藏在物理的、法律的和秘密技術的層層保護之下。如果大數據招致了個人隱私的終結,那么,大數據革命還有什么必要再秘密中進行呢!
(二)身份悖論
大數據的目標是致力于身份識別,但它也威脅著個體身份。這就是身份悖論。我們都本能的渴望對我們的個體身份進行控制。然而,隱私的重要權利來自于個人的獨處權,身份的權利來源自由選擇我們是誰的權利,也就是界定“我是誰”的權利。我就是我,我無名無姓,我就在那兒或這兒存在著,我觀看、我購物、我是個支持者、我是個評論家、我在投票、我在放棄、我反對、我贊成、我喜歡、我不喜歡、我是來自國外的永久性居民、我是個中國市民等。
那么,我們的身份權利即我們說“我是我自己”的權利在大數據時代的狀況會是如何呢?即使對大數據庫的基本接入,如電話記錄、上網記錄、上網史、購物史、網絡社交網貼等,諸如“我是”和“我喜歡”恐怕也會成為“你是”和“你喜歡”。每一個百度用戶已經被來自于百度定制的搜索結果數據庫“輸入—反饋”系統所影響。安德魯·雷納德在他的文章“奈飛公司是如何把觀眾變成木偶的?”一文中,做了如下闡釋:“知道如何從數據中產生情報的企業了解我們勝過我們自己了解自己。而且,如果我們無依無靠的話,將會精巧地使用工具推動我們向他們所期望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向我們想要去的地方。”③由于現在并沒有發展大數據的身份保護,“你是”和“你喜歡”恐怕要變成“你不能”和“你不會喜歡”。大數據因此是運用信息去推動、去勸說、去影響個人,甚至去限制我們的身份。
對個人和集體身份的如此影響是冒著腐蝕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活力的風險。如果我們缺乏每個人都能說“我是誰”的權利,如果非人格化的建議暗中破壞著我們的智力選擇,我們將被識別,但卻失去了我們的身份,這種身份是我們過去所界定和珍視的。
(三)權力悖論
權力塑造著我們的身份,這就產生了大數據的第三個悖論。大數據常被奉為力量強大的工具,能夠使它的使用者把這個世界圖景看得更清晰、更透徹。例如,許多阿拉伯春天抗議者和評論員贊頌社交媒體,因為它的幫助下抗議者組織起了。但是,大數據的傳感器和大數據庫主要掌握在強力的機構手中,而不是在不同的個人手中。這就是權力悖論。大數據將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大數據利益的天平傾向于擁有對個體擁有控制權的機構,他們被發掘、被分析、被分類。如果不了解什么是恰當的法律邊界和技術邊界,每一方都將處在被猜測的狀態中。一方面個體會因屈服而否認;另一方面會因政府和公司機構違約而僥幸成功,但一旦丑聞曝露于眾,他們就會搖搖欲墜,自食其果。其結果不但讓人心神不定,而且會帶來社會混亂,對任何方面都不利:個人的權利受到侵蝕,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受到削弱。
如果我們不在一開始就把個人隱私、信息透明化、個人權利自治和身份保護等因素一同構建到大數據中來,那么權力的悖論將弱化大數據的崇高使命。我們需要在那些產生數據的一方和那些進行參考并據此做出決定的一方取得有益的平衡,以便人們不會濫用反抗的旗幟,也不會隨便的控制他人。
三、結論
幾乎就在二十年前,互聯網的福音傳播者約翰·佩里·巴洛就寫過一本名為《互聯網的獨立宣言》的書,他在書中宣稱,互聯網將會成為“思想的新家園”,在這個家園中,政府的裁判權將會消失。巴洛是“網絡例外主義者”中的一員,他們認為網絡將會改變一切。他幾乎完全正確,互聯網的確改變了很多事物,而且也的確為思想開創了新家園。但是,網絡例外主義的言辭太過于樂觀了,太過于輕視人類的網絡現實和它所帶來的問題以及無法避免的權力管制,其中包括強力機構的潛在用途。
我們認為在對大數據的描述中發生著同樣事情。網絡烏托邦主義者過分夸大了它的潛力而低估了天平另一邊的價值,尤其是個人隱私、個人身份以及對權力的監督。本篇文章的目的有兩層意思:
首先,我們想去提醒對大數據烏托邦圖景的描繪經常被過分夸大了,對大數據進行嚴肅的和更加務實的討論將十分有幫助。對于是否以大數據為依據做決策,有時僅僅從以大數據為根據的答案中尋找答案是遠遠不夠的。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大數據不僅具有巨大的潛力,而且還要清楚功能強大的大數據分析給社會釋放的一些潛在危險。網絡空間烏托邦理想需要屈從于人類現實,尤其當它被揭示出有身份泄露、垃圾郵件和網絡威脅等問題時。為了實現利益的實質性突破,減少網絡的無節制行為無疑是必要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如此。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取其所長,避其所短。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認為答案必須在于形成“大數據倫理”的理念,不管大數據分析是否合理,一種對時代和背景環境的社會化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大數據將會是革命性的,但我們應當保證這是一場我們想要的革命,與我們堅持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相一致的革命。這些價值有對隱私、身份和個人權利的關照。只要我們做到這一點,大數據的潛能就會開始接近我們從大數據福音傳播者那里所聽到的美好圖景。
注釋:
①大數據時代下的大數據到底有多大?[OL].http://www.thebigdata.cn/QiTa/8608.html.
②Rick Smolan &Jennifer Erwitt,The Human Face of Big Data(2012):3.
③Andrew Leonard,How Netfix is Turning Viewers into Puppets,http://www.salon.com/2013.
參考文獻
[1]大數據時代下的大數據到底有多大?[OL].http://www.thebigdata.cn/QiTa/8608.html.
[2][美]維克托·邁爾.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3]Andrew Leonard,How Netfix is Turning Viewers into Puppets,http://www.salon.com/2013.
[4]Rick Smolan &Jennifer Erwitt,The Human Face of Big Data(2012).3.
作者簡介:張道坤(1974—),男,安徽宿州人,碩士研究生,中共甘肅省委黨校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網絡文化、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