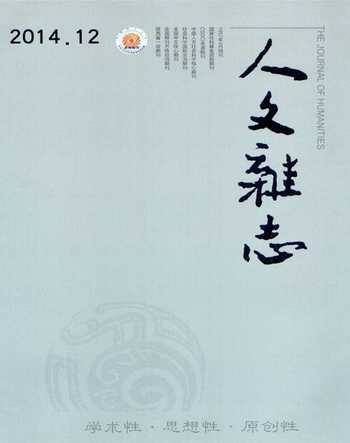社會基礎、制度環境和行政化陷阱
徐道穩
內容提要 經過多年的改革,深圳社區治理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其行政化趨勢一直沒有變化,甚至還逐步加強。社區治理體制陷入理念上去行政化、實踐中卻趨于高度行政化的陷阱。深圳獨特的人口結構給社會管理造成巨大壓力,客觀上需要行政權力強勢介入社區治理,而城市居民在社會治安和公共服務方面對政府的期待是社區治理行政化的合法性基礎。政府行為的自利性、路徑依賴和地方政府的壓力型體制是造成社區治理行政化的制度原因。為超越陷入行政化陷阱,必須通過社會體制創新,改革社區權力運作模式,減少行政干預因素,增加社會自治因素,逐步實現社區參與治理和合作治理。
關鍵詞 社區治理 社會基礎 制度環境 行政化陷阱
〔中圖分類號〕C912.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4)12-0117-08
學術界對社區治理結構轉型的研究可謂觀點紛呈。早期研究者多從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角度研究,如朱健剛認為,在街道辦權力擴張的同時,社會自治領域也得以延展,在街區內部,國家與社會之間可能處于一種共生共長、良性互動的關系,從而形成強國家、強社會的態勢。①近年來關于社區治理結構的研究視角逐漸多元。劉鐸基于治理理論認為,中國的社區治理必然要從封閉式治理走向開放式治理,即謀求在開放空間內多主體的合作治理。②張瑞、柳紅霞從權力配置角度認為,應在社區層面對行政權與自治權進行有效劃分,從而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治的有機銜接與良性互動。③束錦通過個案研究認為,社區協商民主有利于以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為聯結紐帶、以合作與共識為目標導向,實現小區治理的有益互動與整合,從而構建和諧的社區治理模式。④鄭杭生在總結地方創新經驗后認為,社區治理的明顯趨勢就是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單一部門的碎片化治理轉向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與復合治理。⑤上述學者的觀點雖然表述不同,但是基本都同意多元治理、合作治理是中國社區治理轉型的理想方向和現實趨勢。本文認為,社區治理結構轉型在不同規模的城市或者不同規模的街區可能有不同的表現,某些街道或居委會層面的改革嘗試可能有合作治理的元素,但是總體上作出合作治理的判斷可能為時尚早。合作的前提是主體獨立、法律地位平等,合作治理的實質在于,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本文基于對深圳的個案研究,發現其社區治理體制仍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點,而且這一特點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制度環境,旨在說明社區治理結構轉型具有高度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一、深圳社區治理體制的改革和發展
中國社區治理體制改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民政部提出的社區服務。那時的深圳與其說是一個城市還不如說是一個大型建設工地,經濟剛剛起步,社區組織還很不健全,人員流動性強,各項社會事業百廢待舉,各級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社區服務工作只有少數居委會進行了嘗試和探索。進入1990年代,深圳的城市功能逐步健全,整個城市也逐步從“就業集散地”向“生活共同體”轉變。同時,大量的社會管理和服務事項涌向街道和居委會,形成“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但是在社區層面,各部門條塊分割嚴重,事權錢分離,許多事情社區工作人員“看得見、摸得著、管不了”。于是,以做實做強街道辦和居委會為主要內容的社區治理體制改革就顯得尤為迫切。1990年代中期,深圳學習上海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模式,進行以權力下沉為方向的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改革的要點是“一個確立、兩個賦予、三個分開”。即確立街道辦對轄區管理負總責的地位,以塊為主、融條于塊;賦予街道辦對職能部門派出機構的領導權或統籌協調權,對綜合執法的指揮調度權,對管理機構的監督權;賦予相應的財權;實行政企分開、政社分開、社企分開。
1990年代,社區改革的直接成果是街道辦的組織體系迅速膨脹,權力急劇擴張,居委會的管理和服務職能大大增強,但是居委會承擔大量的行政職能、居委會成員由上級委派等科層特點倍受社會各界詬病,因此,對居委會進行改革成為2000年以后深圳社區治理改革的新目標。2002年,深圳市試點“議行分設”的社區治理體制,“議行分設”的特點是實行“一會兩站”,即在社區居委會下面設立社區工作站和社區服務站。居委會作為議事組織對社區重大事務和社區治理行使決策權、監督權;社區工作站、社區服務站作為居委會的執行機構,分別完成政府委托的行政工作、辦理社區自治事務和為民服務。但這一體制很快被“居站分設”體制所替代。“居站分設”是指在基層社區同時設立社區工作站和居民委員會,前者承擔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工作,后者從事居民自治事務。根據《深圳市社區工作站管理試行辦法》,社區工作站在街道黨工委、街道辦事處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并接受市、區民政部門及其他政府工作部門的業務指導,其工作人員的管理原則上參照深圳市機關事業單位普通雇員管理的有關規定執行。社區工作站與社區居委會之間的關系是政府工作機構和群眾自治組織的關系,兩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實行“居站分設”改革后,深圳部分區又試點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網格化管理的具體做法是:根據人口分布、產業分布和建筑形態將社區劃分為若干網格,每個網格配備3名工作人員,即網格協管員、網格管理員和網格督導員,分別由社區綜合協管員、社區工作站專職人員和街道掛點社區干部擔任,其中網格管理員為網格負責人。網格協管員和管理員的主要任務是采集各類信息,并通過網格信息化管理平臺將基礎信息和矛盾隱患分類上傳到社會管理系統,由街道綜治信訪維穩中心統籌實施信息情況的預警、分流、處理、監控、反饋、結案等各個環節的操作,對社區事務進行精細化管理。2013年,在網格化管理的基礎上,深圳在全市推行以“一庫一隊伍,兩網兩系統”為基本架構的織網工程,“一庫”是指整合各級各部門信息,建立縱向橫向互通共享的信息資源庫。“一隊伍”是指整合各類協管員隊伍,組建獨立專業的網格信息采集員隊伍。“兩網”包括處理矛盾糾紛和問題隱患的社會管理工作網,和提供網上社區服務的社區家園網。“兩系統”是指綜合信息采集系統和決策分析支持系統,分別發揮信息采集功能和決策支持功能。旨在建立覆蓋市、區、街道、社區四級服務管理綜合信息系統。該系統實現了市、區、街道、社區四級信息系統聯通,管理信息覆蓋48類矛盾糾紛和136類問題隱患,同時還能運用“大數據”挖掘技術,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數據之間隱藏的關系,分析各類事件的發生概率和發展趨勢,為領導和各部門有效、科學、準確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據。
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的行政化陷阱
經過多年的改革,深圳社區治理體制經歷了從“議行合一”到“議行分設”再到“居站分設”、網格化管理的巨大變化。首先,社區組織體系更加健全。社區黨組織、社區政府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業主組織、社區社會組織、駐區單位等各類組織在社區治理結構中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次,社區在社會管理中的地位和角色更加凸顯。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有“兩張網”(單位制和街居制)發揮社會管理的功能。改革開放后,單位制逐步解體,街居制發展為社區制,初步實現了社區制這一張網對兩張網的功能替代。再次,社區工作人員的文化素質和業務能力明顯提高。據筆者調查,資歷較深的工作人員普遍具有高中以上學歷,新招聘的工作人員普遍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此外,規范的培訓制度也大大提高了社區工作人員的文化素質和業務能力。
縱觀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歷程,我們發現,雖然社區治理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其行政化特點一直沒有變化,甚至還有所加強。1990年代社區改革的重點是權力和事務向基層下沉,街居的規模和權力逐漸增大,特別是街道辦事處的權力急劇擴大,儼然成為一級政府,規模從《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規定的3~7人擴大到幾百人,深圳有的街道辦甚至有上千人;居委會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也是行政化的,例如,深圳市曾規定,居委會主任享受副科級待遇,居委會的辦公用房和大部分辦公經費都由政府解決。
議行分設模式是對傳統的議行合一模式的改造。在議行合一模式中,城市社區的自治職能、管理職能和服務職能是三位一體的。在議行分設模式中,管理職能和服務職能相對分離,但是仍然接受居委會的領導。議行分設體制并沒有改變議行合一體制中居委會行政化的特點,只是為了完成社區越來越多的行政事務,而在居委會內部增設了機構和人員,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還加重了居委會的行政化色彩。居委會行政化在中國學界頗受詬病,因為自治組織的行政化既有背基層民主化潮流,也面臨法理困境,但是居委會行政化在中國有長達60年的歷史,而且也符合憲法和居委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地方政府要改變它必然面臨法律上的障礙和操作上的困難。從這個角度看,議行分設模式對地方來說是一個穩妥的選擇。
“居站分設”改革實質性地改變了社區的組織結構,無疑在行政化的路上走得最遠。如果說居委會行政化使政府行政權力隱蔽地進入社區,那么居站分設改革則是政府“明目張膽”地在社區設置據點,使行政權力直接下沉到社區。居站分設改革的初衷是恢復居委會的本來面目,還居委會以自治職能,使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那么,改革的初衷能否實現呢?據筆者了解,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的關系在不同的區呈現不同的特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分離式,即社區工作站與社區居委會各自單獨設立,人員完全分離,不交叉任職,這種形式比較少;二是交叉式,即社區工作站與社區居委會人員部分交叉任職,如社區工作站站長通過法定程序被選為社區居委會主任,這種形式在市中心區多見;三是重合式,即社區工作站和社區居委會人員完全一致,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目前這種形式占多數。在“分離式”社區,由于社區工作站承接了原來由居委會承擔的行政事務,從理論上說居委會可以專心自治了,但是居委會手中一無所有,無法自治,也無事可治,居委會處于清閑化或邊緣化的狀態。在其他兩種社區,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基本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從“兩塊牌子”的角度看,社區工作站的設立變相取代了居委會,至少把居委會架空了;從“一套人馬”的角度看,社區工作站的設立又把居委會做實了,把徒有其名的自治組織做實為一個行政化組織。綜上,居站分設改革并沒有實現恢復居委會本來面目的初衷,反而使社區陷入更深的行政化陷阱。
網格化管理的基本做法是把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基礎網格,使網格成為社區治理和社區服務的基本單元。這樣原來的市、區、街道、社區四級社會管理網絡變成五級網絡,行政權力進一步下沉。從表面看,社區網格化管理主要是方便信息采集,但是實際上它是行政權力和網絡技術的完美結合,是技術統治在社區的極致表現。網格化管理通過網絡技術采集信息發揮社會管理或社會控制功能、社區服務功能和決策支持功能,核心是社會控制功能,這從它覆蓋48類矛盾糾紛和136類問題隱患就可見一斑。網格化管理模式編織了一張“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巨型之網,將社區內所有的人、物、事一網打盡,可謂“天下信息,盡入彀中”,徹底實現了社區制對單位制的功能替代。網格化管理使行政權力下沉到社區下面的網格,這意味著以行政權力下沉為方向的社區改革已經走到盡頭,標志著社區治理的行政化達到頂峰。
回顧社區改革的歷程,每一次改革都聲稱轉變政府職能,擴大社區參與,拓展社區自治,但是每一次改革又似乎走向反面,特別是“居站分設”改革,設計者從理論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使改革的結果完全背離了改革的初衷。筆者把這種現象概括為“行政化陷阱”。那么,為什么社區治理改革理念上越是“去行政化”、實踐中卻越是陷入深度行政化,即行政化陷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三、行政化陷阱的社會基礎和制度環境
社區治理的價值理念和制度設計是隨著現代化和都市化的進程而產生和發展的,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所改革和創新。早在1903年,齊美爾在其《都市與精神生活》一文中提出,規模、分工和貨幣經濟是解釋大都市社會關系及精神生活的三個社會學變量。這三個變量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疏離、孤獨、冷漠和充滿理性算計,成為大都市區別于傳統鄉村的典型社會特點。其后,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沃思在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一文中也提出解釋都市社會關系的三個解釋變量,即規模、人口密度和異質性。沃思認為,在這些變量的作用下,現代都市形成了許多異質性的社會圈,這些社會圈之間的關系是部分相關乃至毫不相干的,個人有機會參與許多不同的社會圈,但沒有一個社會圈能完全支配他的忠誠,因此,個人同社會疏離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個人的不穩定和不安全感亦隨之增長。葉中強:《齊美爾、沃思的都市社會學及其在當代中國的影響》,《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現代社區治理必須對上述都市社會關系特點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作出有效回應,但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社區治理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也呈現不同的特點。作為現代化都市,深圳不僅具有現代都市共有的社會關系特征,而且還具有獨特的人口結構特點,其社區治理也和這一特點相適應。深圳的人口結構非常獨特,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獨一無二的。以下人口數據除特別說明外均來自《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http://www.sztj.gov.cn/xxgk/tjsj/pcgb/201105/t20110512_2061597.htm,2014年5月6日訪問。第一,人口普遍年輕。深圳市常住人口1035.79萬人,其中,0~14歲人口為101.87萬人,占9.84%;15~64歲人口為915.64萬人,占88.40%;65歲及以上人口為18.28萬人,占1.76%。平均年齡在30歲左右。第二,性別比例失衡。在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為561.4萬人,占54.2%;女性為474.39萬人,占45.8%。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97.74上升為118.34。第三,低學歷人口占較大比例。在全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為177.9萬人,占17.2%;具有高中(含中專)程度的為248.23萬人,占24.0%;具有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的為609.7萬人,占58.8%。第四,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比例嚴重倒掛。2010年,深圳戶籍人口237.8萬人,非戶籍人口798萬人。根據公安部門的估計,非戶籍管理人口實際達到1200萬人,非戶籍與戶籍人口之比高達5∶1。2013年全市這一比例降到4∶1,但是部分區仍高達20∶1。第五,近一半人口不過家庭生活。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戶350.3萬戶,家庭戶人口為740.2萬人,按實際管理人口1400萬計并假定家庭戶人口均過家庭生活,那么深圳也有近一半的人口不過家庭生活。第六,人口密度較大。按常住人口計,全市人口密度為5201人/平方公里,最高的福田區達到16756人/平方公里。
上述任何一個特點的單獨存在都會給城市的社區治理帶來壓力,何況這些特點同時具備并相互作用,極大地增加了社區治理的復雜性,給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沖擊。近年來,經嚴格整治,深圳社會治安狀況持續好轉,但總體狀況仍不容樂觀。以深圳某區為例,2011年,全區接報刑事警情19581起,刑事案件立案11749宗,其中立“兩搶”案件2741宗,“兩盜”案件2905宗,平均每天刑事立案32宗,“兩搶”案件立案7.5宗,“兩盜”案件立案8宗。“兩搶”案件是指搶劫和搶奪案件,“兩盜”案件是指入室盜竊和盜竊機動車案件。相關數據由筆者在調研中獲得。多年來,深圳市勞動糾紛案件居高不下,群體性勞資糾紛時有發生。2013年,全市各類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共處理案件40528件,各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共受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28497件,處理群體性勞資糾紛突發事件404件。《深圳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統計公報(2013)》,http://www.szhrss.gov.cn/tjsj/zxtjxx/201405/t20140506_2367665_14940.htm,2014年5月6日訪問。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現實狀況客觀上需要行政權力的強勢介入,網絡化管理和織網工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實施的。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深受社會治安混亂之苦,非戶籍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戶籍區隔深感不滿,居民對政府用行政手段解決這些問題充滿期待,因此,社區治理的行政化趨勢也有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基礎。
社區治理的行政化除受社會因素影響外,還與政府行為和政府自身的制度環境密切相關。經過多年改革,政府行為與計劃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相對的、有限的,政府行為必然殘留過去的痕跡。經濟學家諾思在解釋“低效的經濟制度為什么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持續存在”時引入路徑依賴的概念,他認為“路徑依賴性是分析理解長期經濟變遷的關鍵”。[美]道格拉斯·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150頁。實際上,政府行為也會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具有路徑依賴特點的政府行為包括:高度動員,追求一致,政府習慣于運用行政權力調動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去實現預定的工作目標;差別待遇,以示傾斜,即政府根據自己的意愿分配資源、區別對待;廣泛控制,強化歸屬,政府通過廣泛的控制,使個人和社會組織對政府產生依賴。李強:《社會管理創新視角下的政府行為路徑依賴》,《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10期。除上述行為外,筆者認為還有一種普遍存在的行為是“試點先行,檢查驗收”。中國的許多改革走的是“基層出經驗,上級出文件”的路徑,一旦某一基層經驗受到上級重視,即有機會試點推廣,然后層層檢查驗收,檢查的結果作為政績的依據。上述路徑依賴行為得以存在的基礎是政府對權力的壟斷和對大部分社會資源的控制,只要這個基礎還存在,社會管理的行政化就很難避免。
除了路徑依賴,政府行為還有自利化的傾向。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認為,公益性是政府存在的依據,政府行為的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公共目的。公共選擇理論把“經濟人”假設引入公共行政領域,認為政府行為既有公益性特征也有自利性特征。有學者把政府自利性分為合理的自利性和不合理的自利性,王桂云、李濤:《政府自利性與合法性危機——一種基于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社會科學家》2010年第8期。也有學者認為,政府自利性主要是指政府的不合理利益及其實現,可分為政府官員自利、政府部門自利和政府整體自利三個層面,主要表現為公共政策失效、公共物品供應低效和政府擴張諸方面,最終導致政府失靈的結果。周建國、靳亮亮:《基于公共選擇理論視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江海學刊》2007年第4期。本文在后一種意義上使用政府自利性。社區治理的行政化符合政府擴張的自利性傾向,從而成為部分政府官員和政府部門的理性選擇,這一點在“居站分設”改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街道辦下面再設社區工作站作為一級行政管理層級,擴大了基層行政管理隊伍,強化了街道辦、民政等部門在基層的影響力,實際上這一改革也是在民政部門、街道辦的推動下實施的。
社區治理的行政化還與中國地方政府的“壓力型”運作體制有密切關系。早在1997年,就有學者把縣、鄉政府的運作體制總結為“壓力型體制”,并將其定義為“一級政治組織(縣、鄉)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8頁。該概念提出后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并逐步從經濟發展領域擴展到社會管理領域,從而具有越來越強的理論解釋力。社區治理改革中的許多現象可以運用壓力型體制加以解釋。壓力型體制包括三個結構性要素:數量化的任務分解機制;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問題解決機制;物質化的多層次評價體系。楊雪冬:《壓力型體制:一個概念的簡明史》,《社會科學》2012 年第11期。在任務分解機制作用下,基層社區必須準備幾十個牌子、花費大量的精力作出光鮮的“臺賬”,以應付各級各部門的檢查。基層社區疲于應付上級檢查,疏于回應居民的真實需求,導致“可計量的任務驅逐不可計量的任務”現象,即所謂“選擇性關注”現象。[美]詹姆斯·威爾遜:《官僚機構: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孫艷等譯,三聯書店,2006年。多部門共同參與的問題解決機制注重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其基本理念是“目的證明手段”,這就是基層流行“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的原因。在物質化的刺激機制作用下,地方政府有強烈的改革沖動,為創造政績往往不惜成本。但是囿于立法權限,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改革的空間其實很小,因此,基層政府的許多“創新”與其說是改革還不如說是折騰。總之,社區治理行政化有效地適應了壓力型體制中的各種機制,是這種體制中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從而成為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另一方面,壓力型體制得以存在,也是因有強大的行政權力作支撐,社區治理行政化也是壓力型體制的自然延伸。
四、超越行政化陷阱
客觀地說,社區治理行政化既有正功能,如維護社會穩定,提供社區服務,也有負功能,如壓縮了居民的自治空間,抑制了社區參與;既有顯功能,如社會治安好轉,公共服務改善,也有隱功能,如行政成本上升,面臨巨大的信息濫用風險。之所以要超越行政化陷阱,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行政化的正功能和顯功能被廣泛宣傳,而負功能和隱功能被有意無意忽視;第二,行政化與“小政府、大社會”的社區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社區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回歸自治;第三,社區治理網絡化標志著以行政權力下沉為方向的改革已經走到盡頭,社區治理體制改革必須尋找新的突破口。社區治理的行政化自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和制度環境,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區治理體制無法超越行政化陷阱。新制度主義把制度變遷分為自下而上的誘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型制度變遷。還有學者提出“路徑創造”的思想以彌補路徑依賴理論的不足,認為有三種“構造理想路徑”的方式:通過蠻橫的力量來構造路徑,也就是通過設計新的系統和克服實現理想路徑的障礙來構造理想路徑;通過使用經濟獎勵和懲罰來影響路徑發展過程,以使一些路徑更有吸引力和更可行;通過共同演化的過程和調整來構造理想路徑。劉漢民等:《國外路徑依賴理論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4期。這說明通過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社區治理體制完全有可能逐步超越行政化陷阱。這里所說的“超越”是指對行政化的揚棄,即通過社會體制創新,改革社區權力運作模式,減少行政干預的因素,增加社會自治的因素,逐步實現社區參與治理和合作治理。
超越行政化陷阱可從三個層面著手。第一個層面是政府,即改革街道辦體制。現行的街道辦體制確立于20世紀50年代,其法律依據是《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該條例全文僅7條502字,早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對街道辦的運作已失去規范作用,因此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9年6月廢止。廢止《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被認為是高層釋放取消街道辦的改革信號,實踐中也確實有少數城市(如銅陵市)取消了街道辦。那么,街道辦能否取消呢?顯然,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銅陵市可以取消,但是像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卻未必能取消。銅陵市總面積1113平方公里,全市人口約74萬,該市銅官山區政府需要對接的社區僅為18個。深圳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各街道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遠比中小城市復雜,具體情況見表1。根據表1,寶安、光明、坪山、龍華四區非戶籍人口是戶籍人口的10倍以上,各街道平均GDP最高的達到300億元,最低的也近100億元,街道平均管理人口最高的達60多萬人。在這種情況下,街道辦的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職能在短期內難以被替代,因此,在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取消街道辦并不現實。
廢止《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并不意味著要取消街道辦,就如同廢止《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并不是要取消公安派出所一樣。在筆者看來,廢止《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的意義在于,為改革街道辦體制消除法律障礙并提供創新空間。目前,街道辦體制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第一,街道辦職能過多而且混亂,越位和缺位并存。例如企業欠薪,發包單位拖欠工程款等事項,街道辦為了維穩也不得不介入,而對業主要求成立業委會的合法訴求則不積極,甚至暗中阻撓。第二,街道辦的運作缺乏法律依據。街道辦事權較多,但由于管理權和執法權缺乏法律依據在實踐中捉襟見肘。例如,街道執法隊就依法無據。第三,街道辦科層化現象嚴重,管理效率不高。隨著社區改革行政化的推進,街道辦機構龐大、文山會海、上傳下達、迎來送住的作風被許多基層社區人員所詬病。第四,對街道辦的監督機制不健全。街道辦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只對上級政府負責,缺乏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立法重新界定街道辦的性質、職能、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立法的基本方向是,淡化街道辦的經濟職能,強化其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的規劃和監督職能,最大限度吸納社會組織承擔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工作。
第二個層面是社區自治。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基層民主”。從“完善”到“發展”,表明基層民主需要突破傳統的民主方式。實際上,許多城市正在把傳統的居民自治發展為社區自治。例如,深圳市南山區花果山社區取消社區工作站,成立社區綜合黨委、社區居委會、社區社會組織聯合會以及由居民、社會組織和駐區單位代表組成社區共建共享理事會;建立社區服務中心和社區家園網兩個服務平臺,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聘請社會組織管理和運營社區服務平臺,承接原社區工作站的管理和服務工作,形成社區黨委領導,居民、業主、社會組織、駐區單位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新格局。新的治理模式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社會組織能否承接政府的管理職能,即使能承接,像安全生產、計劃生育等專業性較強的工作社會組織也未必能做得了;再如,社區成立的所謂自治組織,其法律地位不明,行為方式和行為后果也需要進一步厘清。另外,深圳人口戶籍結構嚴重倒掛,社會融合的任務非常繁重,如何吸納非戶籍人口參與社區自治也是一項緊迫的課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首先還是要靠立法。社區治理改革不能總是走“基層出經驗、上級出文件”的路子,是到了需要頂層設計的時候了。
在社區治理體系中,業主委員會是社區自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業主委員會是傳統體制外的新生組織,是以財產關系為紐帶的“財合”組織,而非基于地緣和情感的“人合”組織;它的產生對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對社區內部的組織關系和社區治理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目前業主自治面臨業主委員會成立難、成立以后運行難的尷尬境地,個中原因主要是政府對業主維權活動有戒備和防范心理,認為業主維權是社區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在制度設計時對業主委員會設置諸多限制。其實,業主維權是以財產權為基礎的利益訴求,具有經濟性,不具備提出政治訴求的依據。從實踐看,深圳市景洲大廈、長城花園、南天一花園、天然居等小區通過業主維權成為小有名氣的和諧小區。事實證明,業主委員會的成功運作有利于理順社區組織之間以及社區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業主維權不是給政府添亂,而是在幫助政府建設和諧社區。因此,政府應該改變對業主維權的態度,放松對業主組織的管制,賦予業主組織法人地位,充分發揮業主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個層面是社會組織。近年來,中國社會組織發展很快,但社會組織總數仍然偏少,而且結構不合理。截至2013年9月,全國共有社會團體27.4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23.4萬個,基金會3300個,數據參見http://files2.mca.gov.cn/cws/201310/20131022180855268.htm,2014年5月17日訪問。每萬人社會組織不到4個,三類社會組織分別占53.59%、45.76%、0.65%,基金會數量明顯偏少。深圳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截至2013年底,深圳共有社會團體2235個,民辦非企業單位3318個,基金會76個,數據參見http://www.szmz.sz.gov.cn/xxgk/tjsj/zxtjbg/201405/t20140513_2393896.htm,2014年5月17日訪問。每萬人社會組織5個,三類社會組織比例分別是39.7%、58.9%、1.4%。為了增加社會組織數量,許多地方對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實行直接登記政策,對社區社會組織實行備案管理,但是政策的實施情況主要依賴于政府部門的偏好,即上述社會組織能否獲準登記取決于自上而下的選擇,而不是社會組織是否滿足登記的條件。因此,社會組織登記政策必須制度化,應向社會組織發起人提供救濟途徑,變政府自上而下的選擇為社會組織自下而上的選擇。此外,政府有必要進一步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特別要降低社會行動類、政策倡導類社會組織的準入門檻。發展社會行動類和政策倡導類社會組織對調整社區權力運作方式、完善社區治理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除降低準入門檻外,發展社會組織還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成立了社會組織孵化基地,采取“政府資金資助、民間力量運作、民政部門管理、政府公眾監督、社會民眾受益”的運營模式,對處在成長過程中的社會組織進行系統地培育和扶持,促進其實現持續健康發展。這種方式有利于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也符合國際潮流,問題是,實踐中有些地方的孵化基地成立時領導出席,媒體云集,好不熱鬧,但是其可持續性令人擔憂。據《羊城晚報》報道:《佛山社會組織孵化基地開張兩月為何大門緊鎖》,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12/27/content_54280.htm?div=-1,2014年5月6日訪問。為防止孵化基地成為新的“面子工程”,可以與社會企業或基金會合作,引入民間資金和專業人才參與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建設。此外,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并不限于建立孵化基地,還可以在稅收、培訓和政府購買服務等方面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
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中固然能發揮重要作用,但是與政府、市場一樣,社會組織也有失靈的時候,因此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非常重要和必要。監管的目的不是要社會組織對政府“俯首稱臣”,而是為了增強社會組織內部治理能力、籌資能力和服務能力。在內部治理方面,建立以章程為核心的獨立自主、權責明確、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社會組織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理事會、監事會制度,明確理事和監事的權利和職責,改變目前理事“不理事”的虛置狀況。還要建立社會組織信息披露制度。社會組織應當在網站等媒體或服務場所公布其服務程序、業務規程、服務項目、收費標準、賬務收支和年檢情況等信息。在籌資能力方面,要拓展社會組織與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合作渠道,為社會組織和金融機構牽線搭橋,允許社會組織在社區范圍內募捐,通過項目購買、項目獎勵、項目補貼、公益創投等方式,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和社區治理。在服務能力方面,要把社會組織人才隊伍建設納入政府人才發展規劃,讓社會組織人才在住房、社保、職稱等方面享受與其他專業人才同等待遇。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規范評估制度和流程,真正發揮評估對社會組織的引導、約束和促進作用。
五、結語
本文主要分析了深圳社區治理改革的行政化特點,對深圳在社區自治方面的探索涉及較少,實際上深圳在社區自治方面也有不少舉措,如設立社區理事會、社區議事會、社區聽證會、社區論壇、社區樓棟長等。從表面上看,在行政權力擴張的同時,社區自治空間也在擴大,形成所謂“強國家-強社會”的格局。但是實際上社區中的行政權力和自治權利是不對稱的,行政權力占支配地位。政府占有大量資源,通過招標、評估、評獎等手段對社區進行全面控制;社區也有資源,但是社區資源是分散的、有限的和多形態的,很難被有效利用。“強國家-強社會”模式是國家和社會關系的理想類型之一,但是只有在行政權力和社區自治界限分明的背景下才有意義,否則,強國家和強社會在同一社區空間內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在許多城市(包括深圳),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逐步退出服務領域,促進了社會組織的發展,同時又在每個社區建立綜合黨委,統一領導社區工作,從而形成“一元領導,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格局。在這一格局中,政府的身影可能少了,干預的手段也不那么剛性了,但是政府在社區的角色就像一個“千手觀音”,各種社區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只是觀音的手而已,而手是無法獨立存在的。因此,“一元領導,多元參與”的治理格局與學者們心中的合作治理還相去甚遠。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
責任編輯:秦開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