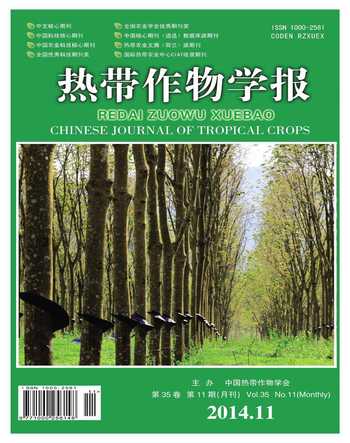胡椒園間作檳榔優(yōu)勢及適宜種植密度研究
楊建峰等
摘 要 為探明胡椒園間作檳榔的優(yōu)勢,并篩選出適宜種植密度,對比了單作與間作以及不同間作種植密度之間的產(chǎn)量及純收入。結(jié)果表明,胡椒園間作檳榔具有明顯產(chǎn)量優(yōu)勢,平均間作優(yōu)勢達(dá)2 466 kg/hm2,土地利用率平均提高78%;間作體系優(yōu)勢主要來自胡椒;間作體系中檳榔密度對間作優(yōu)勢具有顯著影響;常規(guī)種植密度胡椒園間作檳榔以833~1 000株/hm2為宜,其中檳榔密度為833株/hm2時效益最高。
關(guān)鍵詞 胡椒;檳榔;間作;種植密度;效益
中圖分類號 S344.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Abstract To determin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cropping system of areca with black pepper and the suitable planting density, yield and net income were contrasted between the monoculture and intercropping, and among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d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cropping system had obvious yield advantage, about 2 466 kg/hm2 on average,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 increased by 78% averagely. The intercropping advantage mainly came from black pepper. The areca densit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tercropping advantage. The appropriate intercropping density of areca was 833-1 000 plants/hm2, and the benefit was the highest with 833 plants/hm2.
Key words Black pepper; Areca; Intercrop; Density; Benefit
doi 10.3969/j.issn.1000-2561.2014.11.005
間作可充分利用水土光熱等資源提高單位面積土地產(chǎn)量,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占據(jù)舉足輕重的地位[1-4]。胡椒園間作檳榔種植模式被認(rèn)為是較為理想的種植模式,該模式符合間作種植的單雙子葉、高矮作物搭配原則;檳榔植株高,葉片少,與胡椒地上部彼此干擾少,有利于通風(fēng)透光;胡椒須在一定的蔭蔽條件下才能生長良好[5],檳榔葉片可為胡椒正常生長提供適度遮蔭,因此,被認(rèn)為是既可解決檳榔非生產(chǎn)期長造成的土地利用率低,達(dá)到以短養(yǎng)長目的,也是提高產(chǎn)能,全面提升胡椒和檳榔產(chǎn)業(yè)的有效措施。該模式起步晚,盡管目前已成為海南胡椒復(fù)合種植主要模式。但由于生產(chǎn)上尚無相關(guān)配套技術(shù),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不同間作密度間經(jīng)濟(jì)效益差異大,整體種植水平仍較低。研究表明,復(fù)合群體間存在促進(jìn)和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大于促進(jìn)作用時可導(dǎo)致作物生長發(fā)育逐漸受阻,阻礙產(chǎn)業(yè)發(fā)展[6-8]。胡椒園間作檳榔是否具有間作優(yōu)勢,間作后的相互作用是否阻礙兩種作物的生長,繼而影響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目前尚無相關(guān)報道。本研究以產(chǎn)量和經(jīng)濟(jì)效益為依據(jù),揭示胡椒園間作檳榔種植模式是否具有間作優(yōu)勢,并篩選適宜種植密度,以期為該模式生產(chǎn)應(yīng)用提供依據(jù)。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間作優(yōu)勢分析
胡椒園間作檳榔產(chǎn)量及土地當(dāng)量比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本試驗條件下,胡椒園間作檳榔具有明顯產(chǎn)量優(yōu)勢,平均間作優(yōu)勢為2 466 kg/hm2;各處理土地當(dāng)量比為1.15~2.38,均大于1,平均值為1.78,說明間作使得土地利用率平均提高了78%。
間作優(yōu)勢I隨著間作體系中檳榔密度增加呈先增后減的趨勢,檳榔密度為833株/hm2(T4)間作產(chǎn)量優(yōu)勢最大,為4 173 kg/hm2,間作總產(chǎn)量為9 945 kg/hm2,說明胡椒園間作高密度或低密度檳榔間作優(yōu)勢均不會達(dá)到最大化。從帶型配置來看,胡椒 ∶ 檳榔=1 ∶ 1的各處理間作優(yōu)勢均大于2 ∶ 1、3 ∶ 1處理,但1 ∶ 1的3個處理間、2 ∶ 1的2個處理間的間作優(yōu)勢差異顯著。說明,相對帶型配置來說,間作體系中檳榔密度對間作優(yōu)勢的影響更大。
2.2 間作對胡椒產(chǎn)量的影響
由于間作優(yōu)勢明顯,為獲知間作優(yōu)勢產(chǎn)生的原因,仍需進(jìn)一步分析。由于不同間作模式對應(yīng)的單作產(chǎn)量存在差異,這可能是由地力等因素造成的,為了排除這些因素的影響,采用協(xié)方差分析法分析間作對胡椒和檳榔產(chǎn)量的影響。
通過對各處理與單作胡椒、單作檳榔產(chǎn)量交互作用的檢驗,P值分別為0.459和0.965,均大于0.05,說明各處理與單作胡椒產(chǎn)量、單作檳榔產(chǎn)量的交互作用不顯著,各處理與間作胡椒產(chǎn)量、間作檳榔產(chǎn)量協(xié)方差分析是可行的。
從表3的主體間效應(yīng)的檢驗可以看出,處理與間作胡椒產(chǎn)量交互作用檢驗中P(0.013)<0.05,說明各處理與間作胡椒產(chǎn)量交互作用顯著。
為了解間作對胡椒產(chǎn)量影響,對各處理協(xié)方差分析得出的間作胡椒產(chǎn)量修正值進(jìn)行了方差分析(圖1)。各處理間作胡椒產(chǎn)量修正值比單作胡椒產(chǎn)量估計值(1 916 kg/hm2)提高了10%~62%,平均提高了40%;從圖1還可看出,各處理間作胡椒產(chǎn)量間存在顯著差異,隨間作體系檳榔密度增加呈先增后減的趨勢,檳榔密度為833株/hm2(T4)時間作胡椒產(chǎn)量最大,說明此時間作胡椒產(chǎn)量最高。
2.3 間作對檳榔產(chǎn)量的影響
從表4主體間效應(yīng)的檢驗可以看出,各處理與間作檳榔產(chǎn)量交互作用檢驗中P(0.000)<0.05,說明,各處理與間作檳榔產(chǎn)量交互作用顯著。
為了解間作對檳榔產(chǎn)量影響,對各處理協(xié)方差分析得出的間作檳榔產(chǎn)量修正值進(jìn)行了方差分析。從圖2可以看出,各處理間作檳榔產(chǎn)量修正值比單作檳榔產(chǎn)量估計值(17 007 kg/hm2)降低40%~74%,平均降低了60%;間作體系中T6處理的檳榔密度與單作檳榔密度一致,但T6的檳榔產(chǎn)量低于單作檳榔產(chǎn)量,說明間作降低了檳榔產(chǎn)量。由于間作體系中除T6處理外,其余處理的檳榔密度均小于單作檳榔密度,且從圖2可以看出,各處理間作檳榔產(chǎn)量隨間作體系檳榔密度增加而增加,說明間作體系中檳榔產(chǎn)量下降也與檳榔密度有關(guān),因此,間作對檳榔產(chǎn)量下降有多大影響尚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2.4 間作相對競爭力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間作增加了胡椒產(chǎn)量,對檳榔產(chǎn)量降低有一定影響。利用種間相對競爭能力分析可進(jìn)一步明確間作體系中胡椒與檳榔競爭力強(qiáng)弱(表5)。從表中可以看出,各處理種間相對競爭能力Apa為0.21~2.24,均大于0,平均為0.94,說明間作體系中胡椒競爭能力強(qiáng)于檳榔,胡椒園間作檳榔的間作優(yōu)勢主要來自于胡椒。
2.5 間作純收入分析
為篩選出較為適宜的間作種植密度,進(jìn)行了不同處理純收入分析。從圖3可以看出,不同間作模式的間作純收入差異顯著,隨間作體系中檳榔密度增加呈先增后降的趨勢,這與間作優(yōu)勢Ⅰ變化趨勢一致,間作體系純收入從大到小依次為T4>T5>T2>T3>T1>T6,說明,胡椒園間作高密度檳榔或低密度檳榔均不會獲得最大收益,不會使土地利用率達(dá)到最大化,這是由于間作高密度檳榔導(dǎo)致成本增加,純收入反而降低,間作低密度檳榔導(dǎo)致土地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雖然成本不高,但收入低,所以間作優(yōu)勢不明顯。
以間作純收入為適宜種植密度篩選指標(biāo),分析得出,T2、T3、T4和T5處理間作體系純收入較高,且差別不大,T4處理間作體系純收入最高,說明,正常種植密度胡椒園間作檳榔以檳榔密度833~1 000株/hm2為宜,以檳榔密度833株/hm2經(jīng)濟(jì)效益最高,純收入可達(dá)116 028元/hm2。
3 討論與結(jié)論
本研究表明,目前生產(chǎn)上的胡椒園間作檳榔體系存在間作優(yōu)勢。熱帶地區(qū)多種間作體系已被證明存在間作優(yōu)勢[12-14],間作于幼齡椰園的牧草年產(chǎn)值可達(dá)1.0~3.0萬元/hm2,間作于成齡椰園的牧草年產(chǎn)值可達(dá)0.5~2.0萬元/hm2[15];可可/糯米香茶間作體系土地當(dāng)量比達(dá)1.46[16]。本研究中,胡椒園間作檳榔的平均間作優(yōu)勢為2 466 kg/hm2,土地當(dāng)量比為1.78,這說明胡椒園間作檳榔是一種推廣前景較好的間作模式。
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胡椒園間作檳榔的間作優(yōu)勢主要來自胡椒,與單作相比,間作體系中胡椒產(chǎn)量平均提高40%,這說明兩種作物相互作用對胡椒生長有促進(jìn)作用。間作體系種間促進(jìn)作用的原因與根系形態(tài)變化、根系分泌物及微生物等有關(guān),而本研究中胡椒與檳榔種間促進(jìn)的機(jī)理尚不清楚,目前本研究團(tuán)隊正在開展相關(guān)工作。
本研究中間作檳榔產(chǎn)量與單作相比減少,還表明種間競爭作用在胡椒園間作檳榔體系的存在。種間競爭主要表現(xiàn)為地上部對光資源的競爭和地下部對空間、水分和養(yǎng)分等資源的競爭。由于胡椒園間作檳榔體系屬于高矮作物搭配,而且胡椒也需要少量遮蔭的環(huán)境,因此二者地上部競爭較小,種間競爭作用可能主要來自地下部競爭。檳榔屬于棕櫚科植物,相對于胡椒來說,根系更加發(fā)達(dá),但在本研究中卻表現(xiàn)為競爭弱勢,原因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本研究表明,胡椒園間作檳榔密度過高或過低均不能獲得最大整體收益,從而使土地利用率最大化,這是由于間作檳榔密度過高不僅導(dǎo)致成本增加,而且作物之間相互競爭增強(qiáng),二者產(chǎn)量下降,造成綜合效益降低;而間作檳榔密度過低土地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雖然成本不高,但總體收益降低,間作優(yōu)勢不明顯。根據(jù)本文結(jié)果,正常種植密度胡椒園間作檳榔時以檳榔密度833~1 000株/hm2為宜,以檳榔密度833株/hm2效益最高。
參考文獻(xiàn)
[1] Vandermeer J H. The ecology of intercropping[M]. Cambridge: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89: 13-56.
[2] Li L, Yang S C, Li X L, et al. Interspecific complementary and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cropped maizeand faba bean[J]. Plant Soil, 1999, 212: 105-114.
[3] Li L, Sun JH, Zhang FS, et al. Wheat/ maize or wheat/ soybean strip intercropping. I. Yield advantage and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 on nutrients[J]. Field Crops Res, 2001, 71: 123-137.
[4] Zhang FS, Li L. Using competitive and facilitative interactions in intercropping systems enhances crop productivity and nutrient-use eff-iciency[J]. Plant Soil, 2003, 248: 305-312.
[5] 鄔華松. 胡椒光合作用特性研究[J]. 熱帶農(nóng)業(yè)科學(xué), 1999, (3): 7-12.
[6] Steffens D, Mengle K. Das Aneignungsverm gen vonLolium perenne im Vergleich zuTrifolium pratense für Zwischicht-Kalium der Tonminerale[J]. Landwirtsch Forsch, SoHe, 1979, 36: 120-127.
[7] Willey R W. Intercropping-Its importance and research needs. Part Ⅱ[J]. Agronomy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Field Crops Abstract, 1979, 32: 73-85.
[8] 王 剛, 蔣文蘭. 人工草地種群生態(tài)學(xué)研究[M]. 甘肅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1998.
[9] 鄭 毅, 湯 利. 間作作物的養(yǎng)分吸收利用與病蟲害控制關(guān)系研究[M].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8.
[10] 焦念元, 陳明燦, 付國占, 等. 玉米花生間作復(fù)合群體的光合物質(zhì)積累與葉面積指數(shù)變化[J]. 作物雜志, 2007, (1): 34-35.
[11] Willey R W, Rao M R. A competitive ratio for quantifying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rcrops[J].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1980, 16: 117-125.
[12] 易小平, 余雪標(biāo), 唐樹梅. 海南雅星林場芒果間作生態(tài)系統(tǒng)養(yǎng)分循環(huán)研究初報[J]. 熱帶作物學(xué)報, 2003, 24(1): 21-27.
[13] 周曉舟, 李楊瑞, 楊麗濤. 甘蔗/木薯間作系統(tǒng)中氮素的固定與轉(zhuǎn)移[J]. 熱帶作物學(xué)報, 2012, 33(2): 199-206.
[14] 白昌軍, 虞道耿, 陳志權(quán), 等. 桉樹林草間作系統(tǒng)根層結(jié)構(gòu)的研究[J]. 熱帶作物學(xué)報, 2013, 34(9): 1 844-1 851.
[15] 唐龍祥, 馬子龍, 吳多揚(yáng), 等. 椰園/牧草間作: 牧草的適應(yīng)性研究[J]. 熱帶作物學(xué)報, 2004, 25(2): 75-80.
[16] 張翠玲, 徐 飛, 譚樂和, 等. 間作模式下不同肥料對糯米香茶農(nóng)藝性狀和礦物質(zhì)元素的影響[J]. 熱帶作物學(xué)報, 2012, 33(11): 1 949-1 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