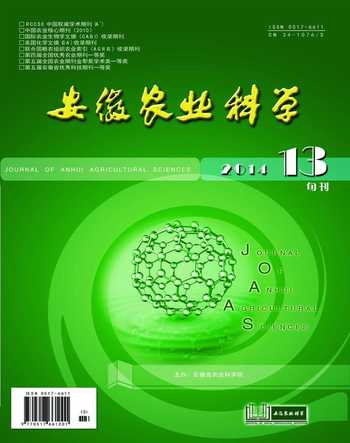河洛先民基于農耕授時需要天象歷法思想探究
郭新建 任科碩
摘要 上古及夏商周時期,河洛先民開創了燦爛的河洛文化,天象歷法文明則是其重要組成元素。先民基于農耕實踐授時需要長期觀測天象,逐漸形成樸素的天文認知,測定季節變化和農事節氣轉換,確定回歸年長度,編纂歷法典籍,從而使得中華天文歷法文明歷史不斷延續發展至今。艱苦的天文實踐成就了卓越的歷法文明,卓越的文明成就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動力量。
關鍵詞 河洛;天象歷法;陰陽合歷;周公測影;回歸年
中圖分類號 S-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4)13-04165-02
1 遠古時期樸素的天象授時思想
天象對古人而言極其神秘,河洛先民通過長期觀察和思考,逐漸形成并不斷修正對天象的獨特理解,將天象變化與農時結合起來以“觀象授時”,將天象變化與人事變化結合起來,便形成樸素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天文和歷法密不可分,先民天象觀測目地,首先是授時,或曰授農時,特別是春秋兩季播種和收獲時間;其次是紀日,通過觀測天象確定年月長短日期;再者是占卜,通過占星術為統治者服務。而授時和紀日便構成“歷法”。
傳說遠古時期黃帝“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1]。“大堯作甲子,容成作歷”[2]。黃帝命令羲和觀測日月星辰,大堯編制甲子紀日的方法,容成編制歷法。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天文工作記載。
在對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5 000年前)考古發掘中,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一批帶有太陽紋、日暈紋、月牙紋、星座紋等的彩陶片,其中一件陶缽經復原后發現,缽體的肩部一周繪12個太陽紋。考古學家認為,這12個太陽紋象征一年12個月,而星座紋應該代表北斗星尾部。也有考古學家認為,這可能與星座紀年有一定關系。學者們均認為這些圖案是河洛先民為發展農業長期觀察天象的結果或記錄,也是目前歷史上發現最早的天文觀測記錄。從這些天象紋彩陶圖案上推斷,早在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河洛先民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識。
對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的考古發現,可以認定河洛先民最早對宇宙有了自己的解讀。墓主人的右側是由蚌殼擺砌的龍,左側由蚌殼擺砌成虎,龍虎皆背向墓主人,頭的方向與墓主人相反,在墓主人足端有一對人脛骨旁擺三角形蚌圖一處,墓穴形狀呈人頭型。考古學家認為,蚌殼塑的龍和虎分別代表東西二陸,墓室中央的三角形蚌塑和二個脛骨代表北斗,以上三者合為三宮,并推斷中國的28宿理論體系應源于仰韶時代。對人頭型墓穴的天文學論證,認為符合中國古代天文理論中的“蓋天宇宙論”,“墓穴形狀,選取了蓋天圖中的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和陽光照射界限,再加之方形大地,一幅完整的宇宙圖形便構成了。它向人們說明了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寒暑季節變化、晝夜長短的更替、春秋分日的標準天象以及太陽周日和周年視運動軌跡等一整套古老的宇宙理論”,并且相信“仰韶先民對宇宙模式的初步認識是具備的,古人對于天象的觀測可能也遠非現代人想象中所能接受的水平”[3]。
2 夏朝《夏小正》[4]的出現標志天文學學科取得重大進展
《夏小正》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文學書籍,夏朝人作成,后世稱作四時之書。該書問世,標志我國古代最早形成的學科之一天文學取得了重大進展。該書是現存最古老的天文、歷法、物候文獻。由書中可見,早在夏代河洛地區的先民就對一些天文現象有了較為準確的認識,如書中提及的星座或恒星有:鞠、參、昂、南門、大火、織女、北斗和銀河等。書中明確指出一年內各月的早晨或黃昏時北斗斗柄的指向及這些星座所處的方位、出沒、見伏或中天的狀況等。如“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中天)”;七月“漢案戶(銀河正對這著南邊的門戶)”,“初昏織女正東鄉(向)”,“斗柄縣(懸)在下則旦”等等。
關于夏朝時奇異天象的觀測,史籍中也有記載,《左傳·昭公十七年》就有“辰不集于房”之說,指某年某月朔日發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這次日食,也寫在現存《尚書》仲康時期的《胤征》篇中,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但確切日期尚不能確定。《竹書紀年》中還載有夏桀十年“夜中星隕如雨”,就是說至遲在公元前16世紀初,我國就有了流星雨的觀測記錄。
3 商代“陰陽合歷”更加準確確定季節變化以授農時
夏朝觀測天象的成果和經驗在商代獲得繼承并進一步有所發展。從商代所用的“陰陽合歷”可以推斷,當時人們已經對太陽運轉周期和月亮圓缺(朔望)周期有了比較深入和準確的觀測。“陰陽合歷”是以太陽的回歸年長度紀年,以月亮朔望變化紀月。由于月亮圓缺變化周期約是29天半,太陽的變化周期約為365天多一點,因此二者無法在一年內求得一致,這就需要用至閏月的方法調整年與月之間的矛盾。有一組甲骨卜辭算出來2個月共59天,那么這2個月必然分為30和29天,即大月和小月之分。甲骨卜辭中有一年的12個月名和多次的“十三月”記載,說明已經開始用“年終置閏法”來調整朔望月和回歸年的吻合。置閏應根據實際觀測,在需要的時候設置閏月,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地球在遠日點師公轉運動比在近日點慢,于是就把閏月放在一年的中間,現在使用的“農歷”中的閏月大多如此。甲骨卜辭中也曾出現過2個七月或八月,則說明當時可能出現了更加科學的“年中置閏法”。置閏法是“陰陽合歷”的最大特點。這種陰陽合歷在我國一直沿用了幾千年,形成獨具特色的歷日制度體系,是河洛先民長期觀察天體運行規律的結果。
《尚書·堯典》中也記載了人們觀察天象以確定季節的成果。如“四仲之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用四組恒星黃昏時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現確定季節的方法。當黃昏時見到鳥星(星宿一)升至中天,就是仲春,這時晝夜時間相等;當大火星(心宿二)升至正南方中天時,就是仲夏,這時白晝時間最長;當虛宿一出現于中天時就是仲秋,此時晝夜時間又相等;當昴星團出現在中天時,就是仲冬,白晝時間最短。而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是現在所說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個節氣。天文學家研究認為,“四仲之星”至晚是商末周初時的實際天象,這是“觀象授時”的重要成果。
甲骨文中有不少天象的記錄,也說明商代非常重視天象觀測,如除常見的雨、風、啟、日、月外,還有日食、月食和恒星、行星的記錄。每當看到日月食時,均要占卜吉兇,如:
日食:“貞:日□(有)食。”“癸酉貞:日夕又(有)食,隹若;”“癸酉貞:日夕又(有)食,非若。” [5]
月食:“之(茲)月(夕)月□(有)食。” [6]這次月食的記錄,比埃及最早的月食記錄要早600年。
新星:“七日已己夕□,□(有)新星大星并火” [7],即七日(已己)這一天晚上有一顆新星靠近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這一新星的出現約在公元前14世紀,是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觀測記錄。
從卜辭的記事來看,殷商時期已對一些重要的星座有了長期的觀察,時人不但熟悉如“大火”、“鳥”等星座,而且對“北斗”、“畢”、“尾”等星宿以及彗星、新星等有較多認識和記錄,并根據這些觀察更加準確確定季節變化,以授農時。從卜辭中還可以看出,當時還不能準確確定太陽回歸年長度,季節變化還只是依據觀測昏旦時恒星出沒時間,稍欠精細。
4 西周星象定季節與測影定節氣
西周時期,人們更加注重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天文學也在商代基礎上進入一個全新發展階段。此時人們通過恒星的觀測,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28個星座作為標志,稱為28宿,分別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依據這些星座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發生的位置等。由太陽在28宿中的位置,便可知一年的季節,這比商代觀測昏旦星象確定季節的方法更為精確。這是古代天文學的一大進步,也初步形成了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特色。《詩經》中一些篇章記有不少星座的名稱,如火(星),箕、斗、室(定、壁)、昴、畢、參、牽牛、織女等星宿的名稱,甚至已有天漢(銀河)的記載,足見西周時期觀測天象的知識極為豐富,這為后來《甘石經書》編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星象確定季節的變化之外,西周初期已能用圭表測日影的方法來確定節氣,并進步到能確定“朔日”。圭表觀測臺最早裝置在陽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是一根直立于圭圓心的柱子,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僅有一尺五寸,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能比較準確地確定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測定出太陽回歸年的長度,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周公測影”。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這是我國古籍中“朔日”兩字的最早出現,也是我國最早明確記載有確切日期的一次日食(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這次的日食記載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日食記錄,巴比倫最早的日食記錄比此晚3年,希臘要晚190多年。如果與甲骨文的記載相比,國外就更晚了。
5 春秋戰國異常天象觀測和回歸年長度測算
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現為對異常天象的觀測,并留下許多珍貴記錄。僅《春秋》一書對日月食的記錄就非常翔實,在242年間,記載日食37次,其中至少30次已證明可靠。在魯隱公三年二月已巳日(公元前720年2月22日)發生的日全食,比西方的記錄早135年。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發生的一次異常天象記載于《春秋左·魯文公十四年》之中,“秋七月,有星孛入與北斗”,天文學家公認的“哈雷彗星”是世界上最早的記錄,比歐洲的記載早了670多年。戰國時期對天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研究,出現了諸如甘德的《天文星占》八卷和石申的《天文》八卷等天文學典籍,后人將二者合為《甘石星經》。他們觀測了金、木、水、火、土5個行星的運行,發現了它們的運行規律。據后來天文學家證實,甘德已發現木星的3號衛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國麥依耳的同一發現早了近兩千年。甘德和石申所測定的恒星記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歐洲第一個恒星代表希臘伊巴谷星表早約200年。由于這些天文學成就,使得戰國時期的歷法更加精確,出現了后來的所謂“四分歷”,即十九年七閏法,采用的回歸年長度只比真正的數值多11 min,古四分歷的發現比歐洲早約500年,比希臘早約百年。
6 天象歷法從神秘與壟斷走向科學與大眾
早期的天文學由于對天象的觀察尚未深入,或多出于臆斷和附會,除了“觀象授時”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外,統治者還利用人們對天象的神秘感,將原始天象觀察與統治者意志結合起來。統治者多利用占卜或巫術的形式,利用天象的變化為其政治統治服務,這也是帶有宗教和迷信色彩的“占星術”得以流傳的原因。古時各個朝代為天文觀測均設有專門官員,天文被統治者所壟斷,并禁止民間天文研究與觀測。古代天文學研究是政府“學術官守”的典型代表。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在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天文學壟斷與反壟斷過程中,產生了很多關于詮釋宇宙的理論,對諸如“天、地、神、鬼”有了逐步清醒的認識,引導著人們的世界觀朝著科學的方向發展,也涌現諸多天文學理論,“渾天說”、“蓋天說”和“宣夜說”等,而“渾天說”相對更加科學。
東漢時期的張衡是“渾天說”的代表人物,他的《渾天儀圖注》便是渾天說的代表性著作。“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這里他明確指出大地是一個圓球,并形象說明了天與地的關系。在他另一名著《靈憲》中則指,“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從而表達了宇宙無限的觀點。張衡的渾天思想得以在他制造的渾天儀——水運混象中體現。渾天儀是張衡在前人工作基礎上制成的,對他的渾天思想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起了重要作用。張衡還于公元132年首創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儀——地動儀,并成功地記錄了公元138年在甘肅發生的一次強烈地震。
7 結語
河洛先民樸素的天象歷法思想,其智慧的光芒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奕奕閃爍,從未褪去耀眼的光輝,也恰如一把文明的鑰匙,開啟著中華民族走向光明未來的大門。如今在河洛先民天才思想的啟迪下,農業氣象工作者應創造出更為燦爛的天文歷法文明以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清)王先謙,何晉.尚書孔傳參正[M].北京:中華書局,2011:18.
[2] (清)孫馮翼.世本八種·孫馮翼集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5.
[3] 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J].文物,1990(3):52-60,69.
[4] 春秋時期杞國(今河南杞縣)國君是夏代宗室后裔,那里較多地保存了夏朝人的文化習俗,孔子為尋訪夏朝文化到了當時杞國,在那里發現流傳至今的《夏小正》(作者注)。
[5] 高承祚.殷契佚存[M].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3:374.
[6] 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M].北京: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社,1972:56.
[7] 羅振玉.殷墟書契后編.下[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