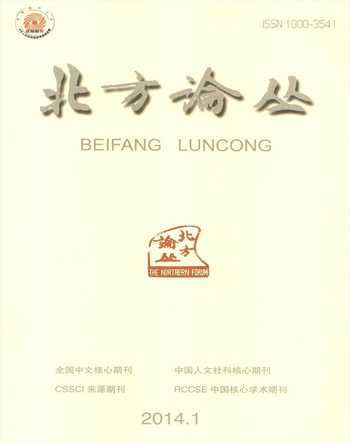真實的懷疑:韓東
柯雷 張曉紅
[摘 要]文革后中國迎來一場文學復興運動,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以“朦朧詩”為代表的藝術風格,誕生很多“朦朧詩”和“朦朧”詩人,以北島、舒婷等為代表。作為詩人、編輯和元文本作者的韓東一直是先鋒詩歌的重要聲音。曾有很多批評家將其詩歌與“朦朧詩”、“后朦朧詩”等相提并論。然而,韓詩卻是以抵制和否棄“朦朧詩”而著稱,并提倡“真實地寫作”。選取了韓東《山民》等詩作分析其詩學觀,認為韓東式懷疑帶有一種存在主義意味,相信真實性和個體經驗,并以此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
[關鍵詞]韓東;真實寫作;詩學觀;朦朧詩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1-0000-09
我們看到,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往往從先鋒與正統的疏離入手對之進行反面定義(negative definition)。回首往事,作為中國詩歌史上早期分水嶺的1917年文學革命也被從反面定義,當時是以古典傳統為參照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即為人熟知的“八不”,引人注目。
反面定義有一定的道理。文藝是一項累積性事業,并且我們對文藝的期望是由陳年往事塑造的,這也許恰恰是新事物無法給予我們的。當文藝專注于一首詩或一幅畫不是什么之時,聚焦于它所不具備的特征,例如,押韻,或者它與自然世界隱含的相似性,文藝運作就不僅僅停留在潮流、運動和流派等層面上,也發生在個人詩作,甚而單部作品層面上。一個反面定義,比如說,“這種詩歌不押韻”,并不排斥同時存在的正面定義;比如說,“這種詩歌凸顯文學的表演方面”。然而,如果一首詩的顯著特征僅限于否棄另一特征,其功能相當于評論,而非原文,即使這是一種相對的區別。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降,作為詩人、編輯和元文本作者的韓東一直是先鋒圈內一個卓爾不群、富有影響力的聲音。除了兩部個人選集,他的詩歌出現在許多重要的多人合集中;他是《他們》雜志的創刊編輯,創辦大手筆的《年代詩叢》,長年來為詩歌論爭作出了貢獻。他的作品成為眾多期刊文章和當代詩歌研究專著的重頭戲。至于奚密、蘇煒、文棣和藍詩玲觸及韓東詩歌,將之與朦朧詩、后朦朧詩、新時代和第三代詩歌等詩歌類別進行比較。杰弗里(Jeffrey Twitchell-Waas)和黃梵在一篇關于南京詩壇的文章中濃墨重彩地描寫韓東。由西敏翻譯的韓東作品見于詩歌國際網,附有一篇靈動敏銳的介紹性文章。
自從非官方刊物《今天》開創先鋒詩先河以來,所有先鋒詩繼續多多少少站在正統詩歌的對立面,其中包括韓東的詩歌,但這是白費口舌,因為先鋒詩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使體制黯然失色。重要的是,在先鋒詩壇內部,韓東的詩歌常常因否棄朦朧詩而被從反面定義。原因在于:韓東某些最出名的早期作品反寫了著名的朦朧詩人和朦朧詩,他的一些詩學命題同樣如此。
一、拒絕“朦朧詩”
從1978年12月到1980年,《今天》創刊號問世不到兩年時間,雜志就被取消。雖然《今天》曇花一現,但是,在年輕的城市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在校大學生來說尤其意義非凡。大學生詩歌經由非官方渠道流傳至全國,被集體命名為“校園詩歌”,他們當中許多人推動了校園詩歌的大發展。韓東就讀于山東大學哲學系,已是小有名氣的校園詩人。吳開晉注意到,韓東的一首組詩于1981年獲得官方刊物《青春》頒發的獎項,他依舊體現了《今天》(特別是早期北島)所開創的悲劇英雄朦朧詩傳統。獲獎之后不久,韓東徹底改變了自己的風格。新詩潮從80年代中期開始僭越朦朧詩。韓東的《山民》被公奉為開山之作[1](p.214)。
小時候,他問父親
“山那邊是什么”
父親說“是山”
“那邊的那邊呢”
“山,還是山”
他不作聲了,看著遠處
山第一次使他這樣疲倦
他想,這輩子是走不出這里的群山了
海是有的,但十分遙遠
他只能活幾十年
所以沒有等他走到那里
就已死在半路上了
死在山中
他覺得應該帶著老婆一起上路
老婆會給他生個兒子
到他死的時候
兒子就長大了
兒子也會有老婆
兒子也會有兒子
兒子的兒子也還會有兒子
他不再想了
兒子也使他很疲倦
他只是遺憾
他的祖先沒有像他一樣想過
不然,見到大海的該是他了
盡管1982年發表的《山民》影射《愚公移山》的寓言及其在紅色年代的接受情況,但是,當主角愚公對大山和子孫感到疲倦時,詩歌就發生了具有反諷意味的轉折,與矢志不移、持之以恒的愚公精神形成鮮明的對照。[2](p.290)此處,我們的興趣點在于《山民》偏離朦朧詩急轉直下,而后者曾以高談闊論的語氣和新穎大膽的隱喻而著稱。
較之后期作品,《山民》這首詩盡管稚嫩,但確實預示了韓東最著名的兩首詩——《有關大雁塔》和《你見過大海》,它們見于眾多詩選集和中國當代詩歌文學史研究著作。它們有著懷疑主義和反諷的特點,用同樣故作簡單的風格寫成。引人注目的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奇缺這些文學表達方式,在先鋒詩歌第一階段也十分罕見,亦即朦朧詩階段[4](p.10)。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從遠方趕來
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還來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們
那些發福的人們
統統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來
走進這條大街
轉眼不見了
也有有種的往下跳
在臺階上開一朵紅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當代英雄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什么
我們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風景
然后再下來
此乃經典版《大雁塔》,它與一個鮮為人知的早期版本并存于世,后者發表在蘭州非官方刊物《同代》上。該詩遠離說教和解說,轉向有效的沉默,表明了韓東個人風格的轉變。
聚焦韓東作品中被從正面定義的特征。追隨先前的學術研究,首先記住《有關大雁塔》反寫了朦朧詩歌,尤其是楊煉的《大雁塔》(1980年)[5](pp.30-31)。韓東解構楊煉的傳統觀念,顛覆了楊煉關于大雁塔的浮夸式文學演示。朦朧詩中雄偉壯麗的中華文明地標,以及普通中國游客對這些個事物所謂的期望,統統被韓東消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中,包括正統文學作品和早期朦朧詩在內,浮現出眾多不同凡響的英雄人物。“當代英雄”讓人聯想到其中的一個,而非萊蒙托夫小說中的英雄。
韓東重寫將近二十年,蔡克霖步后塵挪用了大雁塔,《大雁塔》的持久影響可見一斑。蔡詩的標題《大雁塔》(2004)和楊煉詩歌同名。蔡的文本回應了韓詩開頭兩句(有關大雁塔,我們又能知道些什么),也回應了自殺場景,節選如下:
再不懷疑什么
前面就是大雁塔了
……
我已攀上了塔頂
如果展翅
也青空里騰飛
該是件幸福的事了
我壓根兒不想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
充當什么英雄
只想撣去世間浮塵
心,平靜下來
聽佛說話
……
因此,互文性繼續并延展,相當重要的原因是蔡采用楊詩的標題,并重寫韓詩中的重要場景,之后還影射北島紅得發紫的早期文本,而韓東的“有種的”由此再度扭轉意義。北島創作《宣告》,以紀念文革期間紅衛兵暴力下的犧牲品遇羅克。見下面段落: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6](pp.73-74)
最后,拋下民族驕傲(楊煉)、民族驕傲的解構(韓東)和文革期間的不白之冤(北島),蔡克霖把讀者重新導向其他久遠的領域,突出大雁塔最初作為藏經閣的功能,用于收藏從印度取回的佛經:“聽佛說話”。
早在80年代初,正如韓東在《有關大雁塔》中反寫楊煉,他在《你見過大海》(1983年)中回應舒婷,尤其是舒婷激越高昂的《致大海》(1973年)和《海濱晨曲》(1975年)[7](pp.1-6)。有趣的是,《你見過大海》,也可說是韓東自己那首《山民》的續篇,看海是詩中主人公一直未了的心愿。放到一起看,這些互文性關系有助于消解“大海的文學神話”[8](p.239),以及大海“想象的文化意義”[3](p.216)。
你見過大海
你想像過
大海
你想像過大海
然后見到它
就是這樣
你見過了大海
并想像過它
可你不是
一個水手
就是這樣
你想像過大海
你見過大海
也許你還喜歡大海
最多是這樣
你見過大海
你也想像過大海
你不情愿
讓海水給淹死
就是這樣
人人都這樣
毋庸置疑,批判性地回應朦朧詩,并與之斷絕關系,是早期韓東部分動機所在。在近些年的訪談中,韓東承認,由北島掛帥的朦朧詩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聲言自己這一代人掙脫束縛的嘗試可說是一種弒父行為。此言契合了80年代中期年輕作者和批評家間或使用的“打倒北島!”標語。順便提一句,韓東追述道,在北島的力薦下,《中國》才刊發了《有關大雁塔》[9](pp.396-397)。該刊第三期設有一個專欄,且有老資格詩人牛漢的親筆簽名。另類詩歌,實為先鋒詩歌門面的朦朧詩繼承者,在形式上獲得了官方認可。不久以后,年輕一代對朦朧詩人的拒絕,從程蔚東發表在《文匯報》上的短文中體現出來,文章題為《別了,舒婷北島》(1987)[10](p.3)。
斷絕關系之舉,不僅從韓東的詩歌中得以彰顯,從他自1985年以來發表的早期詩學言論中也可見一斑。其“詩到語言為止”的格言,使人聯想到馬拉美的論斷,詩歌是由語詞而非思想所構成的(即使這只是馬拉美詩學觀的簡寫版),其他現代作者也發表過相關的言論。韓東的話表達了一種相似的愿望,要對詩歌去神秘化,或者最低限度地強調語言作為詩歌媒介的本體首要性,而不是把詩歌呈現為對其他任何事物的一種延展或轉體。在本土語境中,韓東的一番言論也反映了對文學正統和早期“朦朧詩”所作出的意識形態聲明的拒絕。
韓東的警示名言,是中國當代詩歌中最常被引用的詩學立場之一,且催生了多種變體和解讀。蘇煒和文棣將其譯為“詩歌止于語言”[11](p.299)。這意味著,詩歌在“抵達”或“到達”語言之前“停止”,但原意為:詩歌在抵達語言之后才停止。杰弗里和黃帆把韓東的話擴展為“詩歌始于并終于語言”[5](p.34),這似乎合并了尚仲敏的“詩歌從語言開始”的主張[12](pp.299-232)。于堅寫下“詩‘從語言開始到‘語言為止”時,有意把尚仲敏和韓東的話整合起來[13](p.310)。韓東最初的命題,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起源不甚明了。他一如既往,稱自己的話從來無意成為理論公式,也不應被轉化成某種“真理”,借此淡化其重要性[14](p.475)。
假如與韓東的詩歌和詩學主張相提并論,后者因其嚴肅、嚴苛、嚴重的語氣及其對抽象的青睞而格外醒目。同時,他針對諸如詩人、讀者和批評家角色、靈感、詩歌形式和技巧、詩歌的社會地位等問題的評述具有敏銳的眼光和洞察力。
從1984年到1995年,南京詩刊《他們》是閱讀面最廣、辦刊時間最久的非官方詩歌刊物之一,該刊有助于今日先鋒詩歌面貌的形成,韓東是《他們》背后的推手。《他們》并未得到國外學界的充分關注。刊物中文名稱的靈感源于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的小說《他們》(Them),但刊物第五期封面上被回譯成主格They。刊物的核心作者早在1984年就開始了溝通和合作,包括韓東、丁當和于堅,還有陸憶敏、呂德安、普珉、王寅、小海、肖軍和于小偉。共九期紙質版《他們》先后面世:1—5期發行于1985—1989年間,6—9期出現在1993—1995年間。1989—1992年間,刊物處于蟄伏期。2002年以降,作為“他們文學網”的一部分發表于網絡。
盡管標新立異不是《他們》的全部意義所在,但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有別于《今天》,由此確立自己的身份。而且我們將很快發現,《他們》與另一份吸引眼球的非官方刊物,后者發端于當時活躍的詩歌省份——四川。《他們》的重要意義在于: 它是從形式和內容上由宏大升華轉向簡單庸常的一種早期表現,因而推動了從“崇高”到“世俗”的發展趨勢。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和《你見過大海》均見于南京刊物的創刊號,在這方面是代表性文本。
韓東發表于《他們》第三、五期的編者按,確認與《今天》脫離關系。第三期(1986)封面列舉了十位撰稿人的名字,并在名字下面寫了這么一段話:
創辦《他們》時,我們并沒有一個理論的發言,現在仍然如此。但有一些問題變得越來越明確了,我們有必要總結一下。
我們關心的是詩歌本身,是詩歌成其為詩歌,是這種由語言和語言的運動所產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們關心的是作為個人深入到這個世界中去的感受、體會和經驗,是流淌在他(詩人)血液中的命運的力量。我們是在完全無依靠的情況下面對世界和詩歌的,雖然在我們的身上投射著各種各樣觀念的光輝。但是,我們不想,也不可能用這些觀念去代替我們和世界(包括詩歌)的關系。世界就在我們的面前,觸手可及。我們不會因為某種理論的認可而自信起來,認為這個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不在我們手中,即使有千萬條理由我們也不會相信它。相反,如果這個世界已經在我們的手中,又有什么理由讓我們覺得這是不真實的呢?
在今天,沉默也成了一種風度。我們不會因為一種風度而沉默,我們始終認為我們的詩歌就是我們最好的發言。我們不藐視任何理論或哲學的思考,只是我們不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此。
即便詩歌似乎有可能終究比語言走得更遠,第二段尤其流露出對與《今天》有瓜葛的詩歌類型和文壇演練的拒絕。1988年,《他們》重印了徐敬亞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編者按,以一句話段落結尾,曰:“我們要求自己更加真實地寫作”,相信韓東就是此文作者[15](pp.52-53)。
《他們》第五期發表于1988年底或1989年初,封面上印有韓東的一幀肖像,卷首刊有其詩選(期刊封面上寫著大號字“一九八九”,但其封底版本記錄頁上所引用的出版日期卻為1988年11月)。 封二上包含韓東的評論文章,題為《寫給〈他們〉》:
……為《他們》寫作是我們這些人的寫作方式,它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可能。可以為一張光潔的紙而寫作,可以為好用的筆,我們為《他們》,是同一個意思。
有別于理想主義者,不必在目的性上大做文章。我們知道干一件好事,還要知道怎樣才能干好。怎樣才能干好是干好的保證。普遍缺乏的是前者。
……我們是同志,也是同路人。同路人的情意要大于同志。不能相信的是不擇手段的純正目的。目的的偏差肯定出現在起步之始。……
“他們”不是一個文學流派,僅是一種寫作可能。
“為《他們》寫作”也是一個象征性的說法。《他們》即是一個象征。在目前的中國它是唯一的、純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對寫詩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
“為《他們》寫作”,僅此而已。
盡管韓的小短文不乏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者”和“汗牛充棟”讓人聯想到《今天》催生的詩人們和大量詩歌批評、理論和策略性話語。當韓東寫下《“他們”的寫作》時,也讓我們聯想到四川詩刊《非非》詩人和話語。自1986年創刊以來,《非非》就廣為人知。類似地,強調帶引號的“他們”并非指刊物名稱,而是指撰稿人,不成其為一個文學流派,與常用的“今天派”、“非非派”形成了對照,后兩者是對在《今天》和《非非》上發表詩歌的作者的集體命名[16](p.86)。是否存在著一個“他們派”有待商榷,但它與“今天派”、“非非派”的一個不同點在于:后兩者集中在北京和四川地區,及其相伴而生的地域身份,而全國各地詩人常常通過信件往來而非身體旅行,自由散漫地相遇在“他們”,情況截然相反。“光潔的紙”和“好用的筆”充當簡單的舞臺支柱。當時的中國讀者或許會與詩歌掛鉤的其他一些事物,而且確實連同《今天》扉頁上的詩歌演示,莫不遭到否棄:真、美、正義、先見之明、倍受折磨的靈魂、個人象征等等。編者按的結語是:“‘為《他們》寫作,僅此而已”,乃韓式言論。他力勸讀者正確看待事物,尤其是要意識到,有些事物實際上并沒有看上去那么多:沒那么深入或神秘,沒那么復雜甚至是特別。
概而言之,中國詩歌從完全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來以后,“朦朧詩”和“朦朧”詩人無疑具有最廣泛的影響力,而早期韓東的詩歌和詩學對其作出了強勁有力的評述。就其本身而論,韓東的作品預示了我們此后一直以來所見證的多樣性。
二、 一種原創的詩學觀
沒有傳統的中華文明或自然奇跡經驗,沒有高談闊論或歌功頌德,沒有遠大理想,無須汗牛充棟,也沒有文學流派,“僅此而已”。韓東對朦朧詩的拒絕一目了然,但所有這些反駁別有深意。它們顯現了一種原創的詩學觀,超出了其所在地的文學歷史語境。
涉及主題,學界傾向于關注韓東對傳統主題的解構,及其對庸常和都市日常生活的青睞。我們將要討論的《甲乙》最后四首詩,是后一種傾向的范例。打破機械單調或平鋪直敘,由此制造一種沖擊效應;當節律或其他形式特征未發生任何變化的時候,詩歌作品的語義出現突變,沖擊力來得尤其強大,此乃韓東詩歌少有人問津的一大特點。在《山民》中,韓東初次嘗試發現自己的聲音,不存在震撼效應,詩歌的聲音逐漸低落。而在《有關大雁塔》中,韓東隨興所至,提及個別人跳樓自殺,我們從中確實發現了震撼效應。成群結隊的旅行者熱切地分享某個公共地標之光榮,對照之下他們的自殺行為憑添了一種令人惶恐不安的重要性。除卻最初帶有諷刺意味的解讀,“時代英雄”詞組的意思變得模棱兩可。說者或許根本就是把“有種的人”看成真心英雄,原因是他們有勇氣在大雁塔自絕,從而譴責和消解人們對華夏文明的盲目膜拜。
在《你見過大海》中,重復和近似重復手法一以貫之,幾乎整首詩都是為了專門制造一種催眠式的低音效果。于是乎,在未發生聽覺或視覺上小波動的情況下,根據言說者的描繪,“你”成了溺水者,被“你”浪漫化的大海成了兇手,從而粉碎了乏味單調。我們再次意識到,詩歌進行了一半時,“可你不是/一個水手”的觀察是一次警告。韓東聯系到大海,而大海是一種喜聞樂見的跨文學傳統詩歌意象,借此暗示詩人和水手的對立:說起大海的詩人不享有權力,享有權力的水手不說大海。我們還將在《甲乙》里目睹另一種相似的震撼效應。
此外,韓東呈現詩歌主題,往往因如言說者刻意為之的表面性(willed superficiality)而強化。蘇煒和文棣在討論第三代詩歌時援引了詹明信的概念[11](pp.291-292),筆者的用法不盡相同。蘇煒和文棣專注于作為一種后現代標志的表面性,而筆者用到的概念表示一種機制,它遮擋傳統套路的推理和聯系,導致了一種較為開門見山的陌生化。陳仲義注意到,普遍存在于韓東和其他第三代作者當中的一種“客觀主義”傾向[17](pp.26,45)。上述陌生化機制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有關大雁塔》中的扁平觀察,并未導致靈魂追尋或者價值判斷,從而顛覆了看似不言而喻的假設:像大雁塔這樣的地標建筑,使個體體驗到自身的文化遺產,詩歌是表達那種經驗的合適載體;抑或,參照中國古典傳統,登高望遠是一個合宜的詩歌主題。說者僅僅觀察到,形形色色的人來到大雁塔,爬上高塔,環顧四周,或許享受著成為英雄的幻覺,然后又爬下來,配有關于自殺的畫外音,留待讀者扣問。壓抑常識和傳統推理,產生了陌生化效果,這可以概括為詩歌開篇和結尾處的問題:我們又能知道些什么。至關重要的是,上述客觀主義并非意味著,作者或說者能夠或確實想實現任何程度的表征客觀性,而又可以說沒有設計讀者。
詩評家習慣把韓東的語言運用稱作口語化。此乃韓東藝術被援引最多的特征之一,也是其他《他們》撰稿人頻頻為人稱道的特征。韓東的風格有著巨大影響,因為自從《他們》最初問世以來,口語化寫作一直是許多中國詩人求名之道,并繼續成為詩歌評論的重中之重。現有學術研究和詩人自身已經點明,這種所謂口語詩的語言與日常生活用語不是一碼事,但口語標簽有足夠的道理,在當下文學—歷史語境中確實如此。在這一方面,口語標簽再次強調,韓東詩歌的力量不僅在于對一種或另一種書面語的抵制。從正面進行界定,他的用法顯得字斟句酌、聚焦清晰、收斂克制。這使得韓東詩歌具有一種寧靜的信心和恒心,在對(近似)重復手法的運用上尤其如此。韓東的遣詞造句和詩歌形式,即詩行較短的自由體,非常匹配。
韓東為數不多的早期詩歌,主要作為擺脫朦朧詩的口語詩開山之作成為經典。其收入多人合集和載入文學史的作品的其他方面因此受到忽略,這或許在所難免。《爸爸在天上看我》(2002年)是一部內容豐富的詩集,時間跨度為1982—2001年,表明他的全部作品具有很多側面。經典化描述簡化了事實上復雜的文學文本。我們將重點討論三首風格迥異的詩歌,經典話語對其中任何一首都無所斬獲。韓東藝術的若干特征,匯聚于本章末尾評論的第四首詩《甲乙》中。
首先讓我們看看《一堆亂石中的一個人》(1988年):
一堆亂石中的一個人。一個
這樣的人,這樣的一堆亂石
爬行者,緊貼地面的人
緩慢移動甚至不動的蜥蜴
亂石間時而跳躍的運動員,或是
石塊上面降落的石頭
不是一面圍墻下的那個人
整齊而規則的磚縫前面的那個人
當我們看時停止在那里
把一塊石頭的溫度 傳遞給另一塊石頭
它的形狀是六塊相互重疊的石頭
現在,渴求雨水似地爬到了
畫面的上方[4](p.63)
這首詩所反映的,誠然不是城市生活瑣事。相反,根據一種可能的解讀,通過一種否定聯系法發揮想象力,想象人先變為爬行動物,再變成運動員和石頭,繼而又變回人:“不是……”,接下來,從第五節開始,再度變成冷血的爬行動物。詩歌并未展現任何一種客觀主義。它在句法上模糊不清,比如,第四五六節之間的銜接。它高深莫測,更別說高不可攀了:什么圍墻?是磚縫里面還是外面的墻腳下?“我們”是誰?“六塊相互重疊的石頭”是誰的形狀?接下來發生了什么?雖然如此,此文本引人入勝,邀請讀者作出多種解讀。它也邀請讀者把意象歸為隱喻,與韓東本人及其早年文學知己于堅公開宣稱的“所見即所得”詩學主張形成對照。最為重要的是,詩歌聲音表現了張力、完全介入,且絕無反諷意味。《一個人》在諸多方面有別于韓東最著名的作品,它和《有關大雁塔》、《你見過大海》,以及將要討論的三首詩的共同點在于:一種可感可知的專注。比起許多早期“朦朧詩”和其他傾向“崇高”的文本,該詩更好地處理了隱喻。《一個人》中的隱喻數量有限,它們沒有制造一團亂麻,而是彼此豐富。
《一種黑暗》(1988年)是寫于同一年的另一首詩: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
有差別的黑暗
廣場一樣的黑暗在樹林中
四個人向四個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
在樹木中間但不是樹木內部的黑暗
向上升起擴展到整個天空的黑暗
不是地下的巖石不分彼此的黑暗
使千里之外的燈光分散平均
減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
經過一萬棵樹的轉折沒有消失的黑暗
有一種黑暗在任何時間中禁止陌生人入內
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攬動它就是
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雖然我不在林中[4](p.69)
正如《一堆亂石中的一個人》,《一種黑暗》蘊含神秘莫測、超現實的場景和文學技巧,它們通常不與韓東詩歌標志性的去神秘化發生聯系:四個人向四個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在樹木中間但不是樹木內部的黑暗、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還有地下的巖石的擬人化,在“不分彼此”的句子里。“黑暗”在14行詩中出現12次,在原文結尾詩行和譯文前后照應部分獲得了咒語般特性。這首詩的語言不難,但也不怎么口語化:“使千里之外的燈光分散平均/減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
詩中一個重要的場景是,四個人向四個方向走去。他們分開,彼此漸行漸遠,外形黑黝黝的,詩歌標題取自黑暗。隨后,這些事物被投射在林中樹木上:他們之間有一種黑暗。然而,這并非因為他們像不分彼此的地下巖石那樣緊緊地站立在一起。樹與樹之間的黑暗,互相疏遠,彼此排斥。黑暗阻止陌生人進入,這樣的觀察把來自樹木的黑暗投射到人身上,以及“四個人向四個方向走去”的場景上。最后,存在著一種雙重疏遠,不僅存在于詩中人們當中,而且存在于人、樹和說者之間。在詩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中,最重要是在詩的結尾:“我不在林中”,亦即“我既不在那些人中間,也不在那些樹之間”,出現了冷漠的客觀化公式“我注意到”,雙重疏遠由此一目了然。因此,《一種黑暗》置疑了人們建立并保持協同和聯系的能力。
通觀韓東詩作,別處也發生著這樣的情況,先以《看》(1990年)為例:
既看見你
也看見他
但你們二人
不能相互看見
中間是一面墻
一棵樹
或一陣煙霧
我在墻的縱面
樹的上面
我就是云霧本身
但你們可以
同時看見我
可以看見我
看著這一個
轉向另一個
我是墻
樹
云霧本身
任何可以看見
又用來遮擋的
事物
一只鳥的
兩個側面
分別用我的左眼
和右眼
既看見你
也看見他
惟獨你們二人
不能相互看見[4](pp.126-127)
英語中“look”比“see”隱含更強大的作用力,盡管在漢語中沒有英語詞來得那么明顯。我把“看”翻譯成“see”,是為了保持與結果詞“看見”的聯系,后者在本詩中是更加重要的表達法。
比起《一種黑暗》,《看》更加執意于展現人類接觸的不可能性。橫亙在“我”和“你”之間的障礙,形式不一。其中,墻和樹頻頻出現在韓東的詩歌中,比如,在《墻壁下的人》(1988年)和《街頭小景》(1999年)中,這兩首詩強調了互相感知和互相理解的局限性[4](pp.67,260)。有趣的是,在《看》中,說者在墻邊和樹上方站位之后,從一個旁白式旁觀者變成一個設障者,同時扮演著旁白和主人公角色。第一節最后一行幾乎是得意洋洋的:“我就是云霧本身”(很明顯,第七行的“煙霧”和第十和十八行中的“云霧”相接應。在第三節中,說話者兼設障者化作鳥,其左眼和右眼互相獨立運作。詩末尾幾行語帶譏誚:“[我]既看見你/[我]也看見他/惟獨你們二人/不能相互看見”,雖然這并不是唯一的解讀。另一種解讀可能性不大,但理論上說得通,其間最后四行可被解讀為一種中立看法,甚至表露出悔意。無論如何,《看》,連同韓東的其他詩作,拒絕合群、接觸和溝通,甚至也包括通過詩歌進行溝通。這讓人想起,詩歌被看成阻礙溝通的一種語言。詩歌的阻礙作用是后結構主義思潮以降理論家、批評家和詩人經常苦思冥想的一個主題,讓人心馳神往而又令人困惑不安[18](p.126)。再者,在韓東的幾首詩作中,言說者明顯注意到語言妨礙溝通的悖論,而又積極參與其中,《看》即為其中一例。
韓東的《甲乙》(1991年)是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文本,它標明韓東全部的創作比他早期“代表作”更加意蘊深遠。洪子誠在《在北大課堂讀詩》里回顧了這首詩。這本書記錄了研究生和教授們針對中國著名詩人作品的討論,課程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主持。就其本身而論,作為領軍高等教育機構的成果,《讀詩》是文學經典化進行過程中的一門實物教學課。書中章節涵蓋張棗、王家新、臧棣、歐陽江河、翟永明、呂德安、孫文波、蕭開愚、西川、韓東、柏樺、張曙光、于堅和陳東東等,展現了先鋒陣容在文學史上的卓越地位。
作為韓東專題的主講人,張夏放介紹了詩人的經歷和作品。關于《甲乙》。他注意到,這首詩拆解了傳統詩意,引起聽者關注他所謂的韓東散文體用法、一些中心意象,以及詩歌具有滑稽可笑和觸目驚心特性的事實。隨后的討論記錄了課堂交流情況,多少有點散亂隨意的印象派意味。這無損于發言人冷霜和胡續冬言論的相關性,以及韓東所采用的去人格化技巧。臧棣說,韓東知道如何“進行有力的破壞”。他同時表示,《甲乙》在創作之際,尤其堪稱強有力的詩作,韓東在《甲乙》中的所做所為,詩人們后來在20世紀90年代更勝一籌,例如,肖開愚的作品。 這里似乎參照使用了90年代詩歌概念,它作為批評類別而非年代類別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成為1998—2000年間民間—知識分子論爭的導火索之一。根據前些年支持者的見解,亦包括臧棣,《讀詩》中所研討的詩人大部分被歸為90年代詩歌,除了韓東、呂德安和于堅。《讀詩》結尾部分,承認了90年代詩歌這一概念有待商榷的本質[19]。
下面的分析與臧棣的看法相左,顯示出《甲乙》的文學價值絕不僅限于其曾經的離經叛道,傳統成規也罷,先鋒內部成規也罷[4](pp.137-138)。
甲乙二人分別從床的兩邊下床
甲在系鞋帶。背對著他的乙也在系鞋帶
甲的前面是一扇窗戶,因此他看見了街景
和一根橫過來的樹枝。樹身被墻擋住了
因此他只好從剛要被擋住的地方往回看
樹枝,越來越細,知道末梢
離另一邊的墻,還有好大一截
空著,什么也沒有,沒有樹枝、街景
也許僅僅是天空。甲再(第二次)往回看
頭向左移了五厘米,或向前
也移了五厘米,或向左的同時也向前
不止五厘米,總之是為了看得更多
更多的樹枝,更少的空白。左眼比右眼
看得更多。它們之間的距離是三厘米
但多看見的樹枝都不止三厘米
他(甲)以這樣的差距再看街景
閉上左眼,然后閉上右眼睜開左眼
然后再閉上左眼。到目前為止兩只眼睛
都已閉上。甲什么也不看。甲系鞋帶的時候
不用看,不用看自己的腳,先左后右
兩只都已系好了。四歲時就已學會
五歲受到表揚,六歲已很熟練
這是甲七歲以后的某一天,三十歲的某一天或
六十歲的某一天,他仍能彎腰系自己的鞋帶
只是把乙忽略得太久了。這是我們
(首先是作者)與甲一起犯下的錯誤
她(乙)從另一邊下床,面對一只碗柜
隔著玻璃或紗窗看見了甲所沒有看見的餐具
為敘述的完整起見還必須指出
當乙系好鞋帶起立,留下了本屬于甲的精液
與《看》不同,我在《甲乙》中把“看”翻譯成“look”,有時甚至把“看見”翻譯為“look” 。“看”在此是更加重要的表達。
在漢語中,韓東稱詩中主人公為“甲乙”(天干之首兩位),其用法相當于虛數,比起代詞,“甲乙”更加有效地將主人公去人格化。選用簡單而稍顯正式的技術詞,強化了去人格化效果。本質主義意義上散文和詩歌的區別,在此不甚相關,但是否應該像張夏放那樣,把韓東的用語冠名為散文式,有待商榷。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異議,指出詩中著重重復的詞語和短語,例如第三、五行的“因此”和貫穿全詩的“看”。再者,詩意的用法,在這種情況下最低限度的意思指韓東濃縮的語言,并不排除張夏放所留意的詩中敘事感[19](p.250)。
且回到去人格化問題上。“有意的表面性”即為一例,言說者不滿足于記述甲彎腰系鞋帶后看一小會兒窗外,而是詳細地描述了其一舉一動。例如,為了編造不同的情節,運用高科技儀器為搶銀行做準備,這種描述興許能制造張力,把詩歌推向高潮。然而,在此,甲的行為,或者說確實是他這種人的存在本身,初次被感知,且無法激活意義建構的現成框架。這就解釋了言說者何以無力選擇,而沉迷于記錄細節,似乎漫無目的。在一門語言中所發生的一切,與科學觀察語言無異:甲幾何式多看看樹的嘗試,量化的身體移位,諸如“差距”和“目前為止”的表達法。言說者陳述人們日常經驗中顯而易見的東西,借以從去人格化轉向去人類化,換而言之,轉向更加強烈的陌生化。在這方面,韓東和于堅之間的文學親緣關系格外凸顯。
正如在韓東的許多詩作中,“看”是中心意象之一。《甲乙》大部分文本著眼于準確描述看這一行為,從中透露出來的信息關乎感知的局限性。這種情況發生在多個層面上。首先是字面意義:甲看樹的視線被圍墻遮擋,而如果他接受圍墻的限制,就分享著墻內的空虛,他試圖避開圍墻,不僅是為了多看看樹,也是為了少看看空虛。再者,“也許僅僅是天空”(第9行)中的“也許”和“隔著玻璃或紗窗看見了甲所沒有看見的餐具”(第28行)中的“或”,強調我們無從知曉別人的感知。在詩中,這種不可能性不僅適用于主人公甲的同伴乙這樣的凡夫俗子,而且適用于除此之外全知全能的說話者。
甲向窗外望去、閉上眼睛、完成系鞋帶等行為的過渡,又是陌生化的運作機制,推理思路由此而生,它“本身”不合邏輯,是沒有推理者的推理(假如存在這樣的事物),但我們知道它虛假不實,不知為何又覺得想想蠻好玩的。我們不能確定甲為何閉上、睜開、最后再次閉上眼睛。他在測試視力嗎?直至我們意識到,這對言說者來說完全合情合理。甲完成了看窗外的動作,系鞋帶時中無須看腳。他閉上眼睛,停止觀看,就像食物被吞咽后從嘴里消失,某人停止咀嚼一樣。系鞋帶的動作,漫不經心地把我們拉回到甲的童年,其作用相當于社會經驗的縮影。個人學會這樣或那樣,做得好就受到表揚,變得擅長起來——而且在修訂版《爸爸在天上看我》中,他對自己擅長的事情感到厭倦,不改初衷。
《甲乙》表明,韓東操控日常生活瑣事,將之處理成詩歌素材,在這方面最為老道。如果我們決定對所見所聞進行表層解讀,整個世界或許存在于最細微處,在詩歌中,也可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此乃所獲信息的一個重要部分。與以上評述的詩歌保持一致,這種表層解讀的另一個關鍵點在于:玩世不恭地看待人類共處和互動。在開頭幾行詩中,甲和乙被描繪成背靠背坐著。乙從視野中消失,直到結尾場景才復現。在結尾處,說話者注意到,甲忽視了乙,甲和乙看到不同的事物,卻互相視而不見。甲看到窗外的世界,乙看見體現在櫥柜里餐具上的家務活。此景語帶譏誚,調動了關于異性婚姻陳詞濫調、極端保守的想入非非,繼而引出第27行詩,對乙的女性身份進行遲到的辨認。
乙站起來,甲的精子離開了她的身體,也就是說,疏離了他的精子,證實其根本性分離。在這種情況下,關于性交和繁殖機制的常識遭受陌生化局外人觀點的壓制,根本性分離同樣適用。身體交媾和受孕的可能性,均根本無法改變這樣的觀點,據此人類接觸與無力進行真正互動的萊布尼茨式單子偶遇毫無二致。相反地,性生活和浪漫愛情之類事物任何“天真的”聯系,有可能致使言說者如此描述甲和乙:兩人極其痛苦地性交之后,形同陌路,且使詩歌的結尾(天真得)可恥。就其本身而論,根據張夏放在北大課堂上所做的報告,精子似乎是韓東的噱頭之一。為了闡明該詩如何拆解了傳統詩意,張說:“它很可能給讀者造成一種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潔感。”[19](p.253)有人也許把它看成是張道貌岸然的標志,或者是公開記錄享有盛譽的中國高校課堂活動的假道學。無論如何,詩歌最后一行(“留下了本屬于甲的精液”)不僅僅意味著不潔或可恥。有人也可能這樣解讀道,言說者用反諷的方式滿足了某種特殊的讀者期待:那好吧,此乃你的線索,或者說是你的妙語,雖然它毫無意義。
這使筆者做出最后的觀察,應該再度審視說話者,由于第26行中提及詩歌作者,所以,我將其當做男性。言說者無法分享主人公的感知,還質疑和貶低自己語詞的相關性。他突然概括了自己對甲頭部動作的仔細報導(如第12行中的“總之”),且發出無動于衷的議論——甲可能30歲,而他完全有可能60歲。在詩歌末尾,說話者使人更加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在場。他明明白白地貶低主人公,說他是牽線木偶,凸顯了詩歌作為文本建構物的人造性。甲未注意到乙“是作者所造成的第一個錯誤”。再者,稱其為“我們的”錯誤,言說者使讀者成為從犯。如果我們接受言說者的說法,未注意到乙,對她視而不見,抑或避而不見(忽略),這表明了對創作過程的一種看法,其間作者沒有或不想有完全的控制權。如果我們拒絕,反而能發現一種深思熟慮的作者策略。最后,詩中倒數第二行(“為敘述的完整起見還必須指出”)運用了一種文學元意識(meta-consciousness)和正式的、近乎官腔的語言,以徹底區分說話者和詩歌其余部分,以及兩者之間的反諷距離(韓東在2002年再版時,重新修改了1993年《他們》中的版本,并且重新加入了這句話)。三、結語
韓東最著名的一些早期作品否棄了朦朧詩,當前的文學史和批評予以其莫大的關注。這可以理解,但導致了以下風險:千面的詩作遭到貶低,成為其他文本的評論,被從反面進行定義。以韓東為例,早期經典化導致簡單化的危險,且確實存在嚴重曲解。
若干特征共同構建了韓東獨樹一幟、富有影響力的聲音:庸常主題、刻意的淺顯描寫、口語、文學元意識。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在處理這些事情上所表現的個性和老練。或者,反過來說,解構英雄主題,壓制成規性解讀,拒絕文學語言,把陌生化當作一種基本的文本態度。
第一組特征,將使韓東的詩歌成其這樣一種詩歌:相信真實性,相信個體經驗,以此衡量一切事物,有時甚至達到荒誕程度。第二組特征,則使之成為這樣一種詩歌:不相信感情,不相信個體經驗之外的任何事物。雖然兩者均大有裨益,但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主題,它難以契合第一組特征,而輕而易舉地加入第二組, 即為這種詩歌針對人類接觸和交流(包括通過詩歌進行交流)的懷疑主義。韓東的詩學觀本身就是懷疑詩學。
韓東的懷疑是存在主義式的懷疑,反襯早年北島在《回答》中過度曝光的“我—不—相—信!”它本身就是一種“真實的”懷疑[20](p.1)。北島實為“我—真的—相—信”人文主義價值觀,例如個人尊嚴,而個人作為社會正義支配下的團體一員[21](pp.67-68)。《回答》是北島早期代表作,原因在于它根本就是一種信仰表達。“我—不—相—信”是一種反抗宣言,但同時本質上表達兩層肯定。其一,它在一種宏大敘事內部運作,體現了毛澤東時代話語余波繚繞的影響;其二,北島相信的范圍超出一句獨立俏皮話短語的表層語義,遠遠大于他懷疑的范圍。相比之下,韓東存在主義式的懷疑自始至終貫穿于他的創作之中。
我們從正面定義了韓東的懷疑,在詩歌作品中得以體現,它們不僅僅是對其他詩歌的次要評論,而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復雜的主要文本。
[參 考 文 獻]
[1]吳開晉編.新時代詩潮論[C].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
[2]金漢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3]劉樹元編.中國現當代詩歌賞析[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4]韓東.爸爸在天上看我[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Twitchell-Waas & Huang Fan. Avant-Garde Poetry in China: The Nanjing Scene,1981-1992[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1, No.1 (1997).
[6]北島.北島詩選[M].廣州:新世紀出版社,1987.
[7]舒婷.雙桅船[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8]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1985至1995年文學新潮闡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9]Michell Yeh. Light a Lamp in a Rock: Experimental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Modern China 18, No.4 (1992).
[10]程蔚東.別了,舒婷北島[N].文匯報,1987-01-14.
[11]Su & Larson.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oetic “Berlin Wall”.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C],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12]尚仲敏. 反對現代派[A].吳思敬編.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C].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13]于堅.拒絕隱喻[A].吳思敬編.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C].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14]韓東和常立.關于“他們”及其它:韓東訪談錄.他們論壇,2003-08-26,斑駁文學網.
[15]徐敬亞,等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
[16]吳思敬.走向哲學的詩[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17]陳仲義.詩的嘩變:第三代詩面面觀[M].廈門:鷺江出版社,1994.
[18]Bertens.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M], London etc: Routledge Press,2001.
[19]洪子誠.在北大課堂讀詩[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20]閆月君,等編.朦朧詩選[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21]張閎.聲音的詩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柯雷 (Maghiel van Crevel):荷蘭萊頓大學教授;張曉紅:深圳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