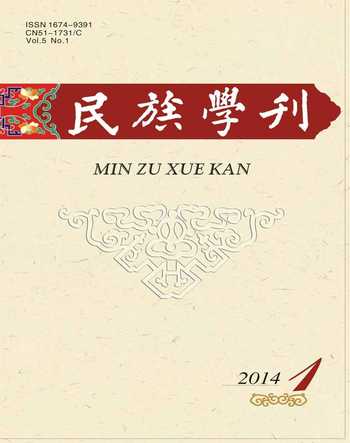基于文化適應理論的人口較少民族文化變遷與社會發展
郗春嬡
[摘要]全球化現代化的浪潮使得世界各民族處于急劇的社會文化變遷之中,發展中國家及其少數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民族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文化適應是應對這一挑戰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布朗族為個案探討社會變遷背景下人口較少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路向。在對文化適應理論進行回顧之后,結合實證調查分析,本文認為,貝瑞所提出的文化適應理論能夠較好解釋及指引布朗族社會變遷及文化傳承,在調適中尋求發展應是人口較少民族當前社會發展的最佳路徑。
[關鍵詞]社會變遷;人口較少民族;文化傳承;文化適應;布朗族
中圖分類號:C9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91(2014)01-0009-07
人類總是處在動態發展的狀態之中, 這種動態發展著的社會過程, 則是社會變遷的歷程。“社會變遷主要是文化的變遷”[1](P.2)。社會變遷的過程就是一個文化調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大環境中各種文化現象裂變、分離、聚合、再生, 社會關系發生重組、社會群體發生演變、社會生活發生轉向、社會制度結構和功能發生改變等,這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也是文化不斷適應的過程。一、文化適應理論回顧在全球化現代化形勢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國家的各文化群體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要面臨文化適應的問題。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 其文化適應和認同問題尤為凸顯。文化適應研究成為當今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 學者們從不同學科視角出發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適應理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般集中于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研究, 關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組織以及文化習俗的改變。心理學家則更加注重個體層次, 強調文化適應對各種心理過程的影響, 以認同、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改變的研究為主。不同學者雖然研究取向及進入路徑有異,但在理論的包容面及解釋力上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現在英文文獻中,美國民族事務局的鮑威爾(Powell)將“acculturation”界定為“來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為所導致的心理變化”[2](P.24-31)。隨著文化適應研究的不斷深入,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經典定義是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林頓(Linton)和赫斯科維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適應研究備忘錄》這一研究報告中給出的界定:“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 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 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3](P.11)。該定義首次系統地明確了文化適應的內涵及外延,為隨后的文化適應研究奠定了基礎。西格爾(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個比較簡潔的定義, 認為文化適應“是由兩個或多個自立的文化系統相連結而發生的文化變遷”[4](P.3-37)。文化適應理論提出后,關于文化適應的研究不斷從各個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適應最初是作為一個群體層面的現象得到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者的關注。后來, 它越來越多地被心理學者當作一個個體層面的變量來進行研究。到目前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個不同的文化適應理論和模型,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沖擊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線假說;Adler 提出的文化適應五階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適應過程模型;Danckwortt的對陌生文化的適應理論; Berry的跨文化適應模型等。與前面幾種相比,后三種理論對文化適應的類型、過程和影響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細致的分析, 影響也更為深遠,它們基本上涵蓋了國際上有關文化適應問題的核心性理論思考和模型建構[5](P.45-52)。在后三者中,前兩者更偏向于個體層面的心理學研究范疇,最后一種理論不僅對個體心理研究有較強的針對性,對社會學人類學的群體研究也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因而本文主要著重對貝瑞( Berry)的理論進行介紹。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學家貝瑞( Berry)借鑒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 根據自己對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調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適應模型”。在他看來: 完整的文化適應概念應該包括兩個層面, 一是在文化層面或群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政治組織、風俗習慣等方面發生的變遷; 另一個層面是指心理或個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 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個體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態度以及認同等方面發生的變化。[6](P.201-234)貝瑞( Berry)指出,少數民族文化認同過程中將面臨兩個主要問題: 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認同。②是否愿意發展與主流文化成員密切的關系, 并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對這兩個維度的肯定與否,將會產生4 種文化認同策略: ①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 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離: 個體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認同, 限制自己與新文化發展緊密的關系,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邊緣化: 個體既不能認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認同本民族文化, 處于兩種文化邊緣地帶。在這四種策略中“, 邊緣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適應過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適應策略被認為是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一種最佳模式,它能夠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間構建起一種平衡關系。Berry 的文化適應模式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并用于分析各種民族群體的文化適應現象。隨著實踐與研究的深入,貝瑞逐漸意識到該二維模型忽視了主流文化群體對民族文化群體文化適應取向的態度。此后,貝瑞在雙維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三個維度, 即主流文化群體在相互文化適應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當主流文化群體通過種種手段來促進少數民族的同化時, 采取的就是“熔爐”策略; 當主流文化群體追求并加強與非主流群體的“分離”時, 其采用的就是“種族隔離”的策略; 當“邊緣化”這種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體強加于文化適應中的群體時, 就是一種“排斥”的策略; 當主流文化群體承認其他文化的對等重要性, 追求國家的文化多樣性時, 就出現了與“整合”相對應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如圖1所示:圖1民族文化群體和主流文化群體使用的文化適應策略①文化適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個伴隨著社會文化變遷歷程不斷凸顯的過程。國外相關理論為國內少數民族的適應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但它們畢竟是根植于西方社會、衍生于西方文化的產物,在國內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研究中,我們在借鑒其合理性的同時,應當立足本土實際辯證地看待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過程。 二、布朗族社會變遷中的文化適應“文化適應過程,在特定意義上就是文化的特殊進化過程。文化的特殊進化是指文化在控馭能量的總能力不作實質性改變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導向作用,為更好地利用生境條件而進行的發展,目的在于使該種文化更加適應其生境。”[8](P.96)民族生境不僅包括了該文化所處的自然環境,而且還包括該文化所處的社會環境,這二者的統一體才構成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歷史——環境條件下,一種文化就是一種與自然界和其他文化發生相互聯系的開放系統。它的地域特征會影響它的技術成份,并通過技術成份再影響到它的社會成分和觀念成分。[10](P.38)
布朗族的形成發展的歷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在自然與社會的變遷中尋找適應生存契機的過程。為了生存,他們形成了一套適應自然環境的生計方式;為了發展,他們吸收兼容了傣族漢族彝族的文化精華。他們從采摘狩獵走到了農耕,從大山走向都市。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斷調適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斷適應中尋求發展。
布朗族的文化適應,是在與自然的調適及與周邊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和相互吸收的過程中進行的。隨著社會變遷與調適, 布朗族本土文化會失去原來的一些特質, 獲得一些新的特質。就是在這個周而復始的變遷—調適—變遷的過程中,布朗族社區逐步改變著本土文化并向前發展。
(一)對自然環境的適應
布朗族居住地多為山區。雙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縣城東南小黑江沿岸山區地帶,這里地處北回歸線,擁有優越的氣候條件,自古就是多種生物繁衍生長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蒼山與碧霞山一帶的山區和半山半壩地區的木老元、擺榔一帶。木老元鄉地形大致為三山兩凹,地勢西高東低,區域內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2895.5m,最低海拔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體型氣候,年平均氣溫18℃,年降雨量1292.15mm,森林覆蓋率53%。生活在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與之適應的本土文化。從生計方式看,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來源,解放前很長一段時期,狩獵和采集是雙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謀生手段,同時,一些布朗族區依然是刀耕火種、輪歇耕作的山地農業文化。解放后,隨著與漢族互動的增加而逐漸進入鋤耕和犁耕階段。此外,這些地區氣候適宜,土地資源豐富,自古盛產茶葉,茶在當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時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從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飾材質厚重,形制基本為了適應山間勞作的需要,男女多為寬褲裝,且還備有綁腿,以防山間荊棘刮劃及蟲蛇叮咬,婦女的圍腰較大,不僅是美觀飾品,更多是作為一種功能性用品用來裝兜東西及照顧小孩。雙江由于地處溫熱帶之間,氣候相對炎熱,所以這里的服飾以筒裙為主。布朗族的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亞熱帶地區,氣候相對炎熱,所以他們的菜肴以酸性為多。味道酸辣、涼拌腌漬為主的烹飪方式較好地反映了他們居住的地域特色。傳統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種自然生境的直觀反映,雙江布朗族傳統住房為“雞罩籠”,這種民居結構布局簡單,以木、竹、茅草為建筑材料;建筑藝術也相當簡潔,多以捆、綁、扎為主。多以椿樹、麻栗樹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長5米左右,出水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頂多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墻壁。門多以竹片編制而成,這種房屋較好的適應了當地氣候特征,既防熱又透氣,冬暖夏涼。施甸布朗人傳統居住的是一種依山勢而建的木結構的干欄式的房屋建筑,稱之為“一步樓”。這種民居較好適應了當地山區地勢,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齊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馱,富裕人家靠馬馱。現在,隨著道路狀況的逐漸好轉,許多人擁有了摩托車、拖拉機,但卻絕少見到輕便實惠的自行車。在宗教習俗上,布朗族也發展出一套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信仰體系,萬物有靈及竜神崇拜,均較好體現了布朗族對自身生存環境的依賴及敬畏。
(二)對社會環境的適應
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布朗族的傳統文化也相應地發生了變遷。社會制度的變革首先對布朗族的生計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國家民族政策的不斷推陳出新,國家行政力量的不斷參與,布朗族由原來的刀耕火種及狩獵采集逐漸變成與主流民族同步的農耕生產方式,近幾年更形成舍棄農耕、走向城市謀生的熱潮,生計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物質文化發生了巨大變遷,衣食住行越來越呈現現代化的特點。首先,服裝已經由傳統民族服裝逐漸過渡成漢裝甚至洋裝,男性的變遷更為明顯,如今走進布朗族社區,除了見到幾位年老的女性還身著民族服飾,年輕人及男性幾乎全部是漢裝或西裝夾克裝扮,從服飾上已經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跡。食品也已經呈現多元化特色,鄉村小賣部里可以輕易買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調設施及方式已經逐漸現代化,幾乎見不到在傳統的火塘及大鐵鍋上烹制食品,同時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些城市餐館的成分,我們在木老元調查時,李祖芹家寬敞明亮的廚房正熱火朝天的在做紅燒魚,以備明天鄰居結婚宴請之用,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館里的廚藝。住所的變遷更為明顯,無論是施甸還是雙江,走進布朗族村寨,幾乎見不到傳統的“雞罩籠”或“一步樓”,漢家房已成為普遍的民居,更有幾棟充滿現代特色的鋼筋混泥土“洋樓”矗立期間,顯得分外醒目。馬馱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幾乎絕跡,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見到大多是滿載的摩托車或農用機動車,木老元鄉甚至已經開通了農村公交車。非物質文化變遷相對平緩一點,也就是奧格布所說的“文化慣性”,它們往往滯后于物質文化的變遷,它們的變遷往往是為了調適于物質文化的變遷,“大部分非物質文化本質上是調適于物質文化或自然環境,或者是調適于二者的方法。行為方式概括了大多數非物質文化的特征。社會組織、風俗、道德都是對自然環境和物質文化的集體行為方式……如果自然環境或物質文化發生變遷,這些行為方式也要變遷。”[1](P.140)隨著社會的發展,布朗族社區家庭結構、婚喪習俗、傳統倫理道德等正在發生悄悄變化,計劃生育的實施使得傳統家庭規模日益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幾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見;新生代女性在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推進中逐漸取得了與男性同等重要的社會地位。隨著對外交往輻射半徑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沖擊著傳統婚俗的復雜規矩及禮儀,原來禁忌及禮儀繁多的婚喪習俗逐漸簡化;傳統禮儀習俗也隨著年輕人大批出外打工而變得日益模糊而淡化,這些見過“世面”的人已經更喜歡“不拘小節”“直奔主題”的生活。在雙江邦協,每年的祭竜儀式依然莊重地按期舉行,人們對竜神依然頂禮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蔥蔥較好地調節著當地的生態。有所不同的是,隨著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國家話語逐漸涉入這一神秘領域,祭竜儀式較往昔少了幾許封閉性,多了幾分開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識在文革后沉寂了一段時間,隨著近年來當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帶動經濟發展的政策取向的倡導,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各種習俗傳承人被挖掘和調動起來,傳統節慶在當地政府的推導下開展得紅紅火火,傳統文化事項在活動主旨的規范下重組及創新,雖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幾分表演,然這不失為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環境的一種積極調適。正如吉登斯所說:“一種類型的人圍繞一組固定的承諾來建構他自己的認同,這就像一個過濾器,在通過它的時候,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釋。”[11](P.244) 三、變遷與適應的現實差異:一個比較分析在社會的變遷中, 在不同的條件下, 文化適應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即便在相同的條件下,不同文化現象變遷速度也會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現象之間的比較
同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與雙江邦協的布朗族文化現象表現出明顯差異,我們以幾個顯著文化事項為例來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項的文化變遷速度的差異。語言是一個民族最顯著的符號特征,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兩地的布朗族語言面臨著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困境,然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二者之間還是有不少區別,總體而言,兩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語都已出現漢化傾向,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逐漸不會講本民族語言,漢語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語言。然而兩相比較就會發現: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變遷的速度快于邦協布朗族,或者說邦協布朗族對本民族的語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齡較長的老年人之外,60歲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漢語,與我們交流沒有任何障礙,在入戶走訪時發現,他們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也用漢語,沒有出現用本族語的情況;而在邦協,雖然大多能講漢語,但即便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表達時也會出現磕磕碰碰我難以聽懂的情況,村支書及俸老師均對此作出解釋:“我們講漢話還是覺得有些別扭,好像舌頭不那么好使”,無論在俸老師家村支書家還是入戶走訪的幾家,只要他們家人之間一交流,幾乎全換成本民族語。因而,這里能講漢話的人,幾乎都是學齡以上進過學堂的人,像俸老師還沒有上學的侄孫那樣的小孩,幾乎聽不懂我的問話,無怪乎在小學訪談時,一些教師表示低年級的學生很多不能聽懂授課。
另一顯著文化事項是傳統生計方式的變遷,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市場經濟大潮也波及到地處邊疆的布朗族山寨,兩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棄傳統農耕、走向城市謀生。兩地比較之后發現,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況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勞力,村里幾乎只留下老人與小孩,出現大量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而邦協村近年打工者雖然越來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還不是太大,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對學校問卷調查也看出,邦協小學全校160名學生中大約只有3名留守兒童,而木老元小學的比例則大得多。
出現以上狀況的原因主要是邦協的布朗族對外交流尤其是與漢族交流相對晚且少,他們受傣文化的影響更大些。而施甸布朗族地處南方第二絲綢之路附近,很早就有對外交流歷史,與漢族互動頻繁,這應該是二者差異的主要原因。
(二)同一地域不同文化現象之間的比較
在文化的變遷中,物質文化變化得更頻繁一些,而非物質文化則相對緩慢一些,有時如果文化的兩部分變化不一致,不能保持原有關系,產生失調,這時就發生了文化滯后。[1](P.205)奧格布所提及的這種情況在布朗族社區也時有發現。
在邦協村,布朗族的傳統服飾與語言均已經或快或慢逐漸退出日常生活,生計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宗教信仰如祭竜、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相關節日依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這一現象有力地印證了奧格布的提法“物質文化變遷快于非物質文化的變遷”。與此同時,布朗族社區也存在文化滯后現象,這在紡織工藝、寺院教育等文化事項變遷中能夠找到印證,一直以來,紡織在布朗族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全家人的衣著全靠婦女手工織布縫制,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尤其年輕人對衣著的數量及樣式要求與日俱增,傳統織機的及手工縫制的效率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這一要求,于是傳統服裝日益淡出人們視野,紡織技藝也慢慢后繼乏人。現代學校教育引入布朗族社區之前,寺院教育一直是邦協布朗族社區比較重要的教育形式,是布朗族男性提高社會地位向上流動唯一途徑,寺院教育在這一時期發揮了較好的選撥、篩選、教化功能,隨著現代教育的介入,寺院教育這一功能逐漸弱化,尤其是教育法的頒布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邦協寺院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要想像從前一樣在寺院接受長時期的教育已經不太現實,然邦協布朗族男性并沒有徹底放棄寺院教育,因為傳統觀念中如果一個男性沒有當和尚的經歷意味著今后將低人一等,在這種失調狀態下,他們想出種種方式來巧妙地協調這二者的沖突,比如通過縮短在寺廟學習的時間來完成人生這一重要歷程,文化慣性的張力在這里得到較好詮釋。
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文化傳統、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質都具有持續性、‘生存力或‘慣性,這就是文化的穩定性原則,即當一種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變時,這種變化也只會達到不改變其基本結構和特征的程度與效果。” [10](P.44)四、傳承與發展:在文化調適中尋求社會發展我們所處的世界正處在一個不斷推陳出新、不斷調適與前進的過程之中,各國各民族都無一避免面臨著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的挑戰。隨著人類社會的高速發展,文化變遷的速度越來越快,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少數民族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文化適應是應對這一挑戰的必由之路,盡管這條路變得日益困難。理論上講,文化適應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也就是接觸的兩個群體的文化模式都要發生變化。但在少數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適應的現實境況中,更多的是處于非主流方去適應主流文化,因而更多的變化往往發生在弱勢群體一邊。在這種情境下,少數民族選擇何種策略、社會主體采用何種態度就顯得無比關鍵,貝瑞所提出的“整合”策略及其所對應的“多元文化”舉措不失為一種明智之選。
在文化變遷中,“很多情況下都是物質文化變遷在先,所引起的其他變遷在后……社會運動相對于物質文化變遷的滯后引起社會失調。[1](P.144)”“特定的文化變遷不僅需要個人與之調適,而且更需要文化的其他各部分與之調適[1](P.65)”。生活在這種文化轉型中的人們,必將經歷劇烈的文化沖突及失調,免不了會陷入迷惑、彷徨之中甚至迷失自我。當布朗族面臨新的文化環境時,如果完全抵制主流文化,即貝瑞所指的“分離”模式,則必然與社會脫節,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如果消極地全盤接受主流文化,即貝瑞所提的“同化”模式,則完全有可能喪失原有文化,失去立身之本。如果面對主流文化的沖擊,沒能及時調整好“文化震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既對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又不能認同外來文化,處于認同虛無狀態,游離于兩種文化之間,即處于文化“邊緣化”之中,必將漸漸失去自我,嚴重影響著本民族的長遠發展,這是最為不利的文化適應結局。因此,創造出新的文化來適應主流文化,成為布朗族既保持原有文化又能融入主流社會發展的最佳方式。這個“創新”的過程就是一個文化調適中的“整合”過程。這個過程是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它意味著對原有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解釋,意味著對行為價值規范的再取向。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曾對這一文化“整合”過程做過精要描述“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種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 人們從周圍地區可能的特質中選擇出可能利用的東西, 放棄不可用的東西, 人們還把其他特質加以重新鑄造, 使它們符合自己的需要。”[12](P.36-37)因而,文化適應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學習和揚棄的過程, 也是產生新文化和建立文化模式的過程。文化持有者就在這一整合過程中,不斷調適自身的文化因子,在保存自身精華的同時適應主流文化,以期求得長遠發展。只有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精華,才能夠樹立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夠自立,有了自立,才能夠談發展;只有適應主流文化,才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納,才不會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與外界脫節,才可能跟上主流社會發展的步伐。有鑒于此,我們在面對布朗族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時,必須意識到,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延續的實質是其在文化的變遷中與其生境進行不斷調適和發展的過程, 即:在文化調適中尋求發展,這應當是布朗族走向更美好未來的最佳途徑。
注釋:
①圖片資料來源于參考文獻[1]-[7]中的相關信息.
參考文獻:
[1][美]威廉·費爾丁·奧格本.社會變遷——關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質[M].王曉毅,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F. W. Rudm in,“Field Notes from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Use of ‘Acculturatio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7, 2003.
[3]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F. W. Rudm in,“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 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Review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 2003.
[5]孫進.文化適應問題研究: 西方的理論與模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5).
[6]J. W. Berry,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J. Berman ( ed. ) ,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C 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L in 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7]楊寶琰,萬明鋼.文化適應: 理論及測量與研究方法[J].世界民族,2010,(4).
[8]羅康隆.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9]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10][美]托馬斯.哈定,等.文化與進化[M].韓建軍,商戈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1][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趙旭東,方文,譯,王銘銘,校.北京:三聯書店,1998.
[12][美]露絲·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王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