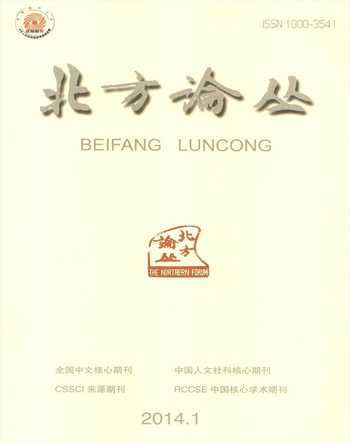西學東漸背景下明清道教與傳統數學之互動
楊子路
[摘 要]明清時期傳統數學中非理性因素淡出,但此時道教與傳統數學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仍有廣泛互動。大量道教學者參與數學、天文歷算學研究,世俗數學家也多受道教思想的影響。這一時期,道教與傳統數學互動有著鮮明的歷史局限性。一方面,傳統數學以及部分道教學者接觸到的西方數學和科技,并未能成為推動道教發展的思想動力;另一方面,以李明徹為代表,道教學者已經開始學習西方先進的數學和科學技術,然而,卻并沒有得到道教界的普遍響應。道教始終未能營造出積極吸收西方科技的文化氛圍,這也正是中國傳統科技衰落的表現之一。
[關鍵詞]明清;道教;西學東漸;傳統數學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1-0000-06
梅榮照先生曾總結:“明清數學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明代傳統數學的衰退;二、西方數學的傳播;三、清代傳統數學的復興。”[1](p.3)明清時期傳統數學由衰轉興的過程,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其一是國內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世俗理性的興起,其二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傳入。在此過程中,附著在數學上的非理性因素,如術數、宗教等,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明清數學家在研究傳統數學過程中,不斷為數學本身祛魅,并構建出符合于時代認知標準的“中國數學史”。阮元便認為:“步算、占候自古別為兩家,《周禮》馮相、保章所司各異”,他編寫《疇人傳》時,“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云氣、虹霓占驗吉兇,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之流涉于內學者,一概不收。”[2](凡例)頗涉內學的道教與傳統數學之間的距離亦漸行漸遠。但如果我們不去預設某種既定的歷史“共識”,從一些文獻史料中,則能發現另一種動向,即道教與傳統數學交互影響之傳統的延續。
法國思想家福柯曾指出:“權力制造知識……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3] (p.29)其言雖顯偏頗,但我們在研究古人的數學史觀念時,確屢見權力對于知識的干預。如清康熙帝下令編撰的《數理精蘊》宣稱:“粵稽上古,河出圖,洛出書。八卦是生,九疇是敘,數學亦于是乎肇焉。蓋圖書應天地之瑞,因圣人而始出;數學窮萬物之理,自圣人而得明也。昔黃帝命隸首作算,《九章》之意已啟。堯命羲和治歷,敬授人時,而歲功以成。周官以六藝教士,數居其一。周髀商高之說可考也,秦漢而后代不乏人,如洛下閎,張衡,劉焯,祖沖之之徒,各有著述。唐宋設明經算學科,其書頒在學宮,令博士弟子肄習。”[4] (p.12)如此,康熙便構造了一條從上古至唐宋,數學起源與發展的歷史脈絡。如果僅以此為據,恐怕只能看到儒家傳統對于數學的貢獻,而見不到道家道教的影子。
實際上,把數學僅視為儒學附庸的觀念,由來已久。齊隋之際學者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稱:“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5] (pp.524-525)宋徽宗時禮部員外郎吳時亦稱:“數學,六藝之一耳。”[6](吳時傳)直至19世紀中葉,晚清思想家王韜還一度認為:“數者,六藝之一耳,于學問中聊備一格。即使天地間盡學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間竟無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7](p.3)因而在特定的話語權力下,道教與數學的聯系難以得到承認。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從明清時期相關的史料中,發現這一傳統的延續。
一、 明清道教學者對傳統數學的研習
明清時期,道教雖然逐漸面臨西方宗教與西方科技的沖擊,但仍然延續了重視數學的傳統。通曉數學,鉆研律數、歷算等學問的道教學者不乏其人。
元末明初道士冷謙,道號龍陽子,以養生、丹青著名于世,為后世道流視為仙人。謙亦精于律歷易數,明太祖曾置太常司,召其為協律郎,“令協樂章聲譜,俾樂生習之。……乃考正四廟雅樂,命謙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罄等器,遂定樂舞之制。”[8](樂志)著有《太古遺音》琴譜,已佚;另撰有《琴聲十六法》(署名冷仙),其中談到:“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其有分數,以位其音。”[9](p.56)可見,冷氏對律數當有所研究,可謂開明朝數理樂律學研究風氣之人。此外,冷謙“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眾技皆能通之。”[10](p.8)對于邵雍一派的象數學及天文歷算都有研究。
明初學者宋濂,元朝末年曾“寄跡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11] (p.2569),修道十余年。宋濂亦精通歷算學,曾受命“與詹同、樂韶鳳修日歷”[8](宋濂傳)。宋氏所著《楚客對》一文在天文學上亦頗有價值和影響[12] (p.19)。明初著名政治家劉基,素有神仙信仰,“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清凈,亦欲作道士,未遂”[13](《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劉基所著《郁離子》便深受道教《陰符經》影響,可謂道教學者,這也正是他被后人仙化的癥結所在。劉基熟諳天文歷算,曾于吳元年擔任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歷》。逝世前數日還以《天文書》授子劉璉,《明史·藝文志》亦著錄其所撰《天文秘略》一卷。他的天算學或源于道教傳授,明焦竑《玉堂叢語》卷八便記載了他于青田山石室得書,受道士教之傳說。
明寧獻王朱權,“自言前身乃南極沖虛真君降生,不樂藩封,棲心云外。”[14](p.736)其著述甚豐,“經子、九流、星歷、醫卜、黃冶諸術皆具”[15](p.761)。在道教方面的著作“就不下二十種”[16](p.12)。在星歷方面,朱權撰有《臞仙肘后經》二卷,《絳云樓書目》編入天文類,另有《肘后神樞》、《運化玄樞》、《歷法通書》著錄于《明史·藝文志》。可見他棲心道門后便從權力斗爭中解脫出來,有閑暇研究歷算音律之學。
明代中晚期學者周述(字繼志)學,“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于易、歷……自歷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一千余卷,總名曰《神道大編》。”[17](《周云淵先生傳》)其中,圖書易、邵雍《皇極經世》之學均源于陳摶之道教易學,其余諸門術數學尤其是兵符、六壬、遁甲與道教淵源頗深。又《浙江通志》引徐階《周云淵傳》稱周述學號“云淵子”,蓋為道號。龔鵬程《道教新論》亦認為周述學為道教中人。
黃宗羲曾談到,周述學“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推究五緯細行,為《星道五圖》,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歷,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于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歷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17](《周云淵先生傳》)對其歷算之學評價較高,黃本人壬遁之學也源于周述學。《明史·周述學傳》更刪去“然于西域之理未能通也”一句[8](《明史·周述學傳》)。李迪、白尚恕教授研究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所藏《神道大編歷宗通議》抄本后,亦認為此書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18] (p.89),與黃宗羲的評價可相印證。
朱載堉更是明代中晚期杰出的科學家,讓爵后自稱道人。嵩山少林寺保存他所作《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石碑,此圖實際上將大致于同時代傳出的《性命圭旨》卷首所標《三圣圖》圣像合三為一,反映了明代中晚期道教“三教合一”的思潮。朱載堉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創建了十二平均律的數學理論。在算學方面,朱載堉又首創珠算開方、找到九進制和十進制的小數換算方法,以及確立計算等比數列的方法,此外他還進行過圓周率的計算。實際上,朱載堉的科學思想與道家道教亦有著密切的關系。朱載堉不僅從道教習得狂狷之氣和視爵祿如腐鼠的態度,更頗有道教式的數學理性和實證精神。朱載堉曾談到:“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19] (p.355)“無端”見于《莊子》在宥、達生、田子方數篇,“玄”、“妙”則出于《道德經》首章。不過,道教雖宗老莊道圓、玄妙之論,但也強調天地有數可循。晉末南朝時期,古靈寶經稱“諸天星宿,各有分度”[20](p.189),《黃帝陰符經》亦謂“日月有數,大小有定”[21](p.821)。受道家道教影響,朱載堉既承認天地運行玄妙無端,亦強調天地運行規律可以用數學方法認識。就前者而論,朱載堉基于老莊道圓思想,強調十二律“黃鐘為始,應鐘為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此自然真理,猶貞后元生,坤盡復來也。”[22](p.10)他提出的十二平均律便徹底解決了三分損益律不能使黃鐘還原、不能旋宮轉調的難題;就后者而言,朱氏強調:“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19](p.294),反對對天文現象作超自然的解釋。朱氏指出:“日月交食,故皆常理,實非災異。趙友欽曰:‘日月之食,其所行交道有常數,雖盛世所不免,故可以籌策推,非若五星有反常之變也。此言得之矣!”[19](pp.302-303)可見,朱載堉繼承了道士趙友欽的科學思想,將尚圓的美學觀念與萬物有數可循的理性法則統一起來。朱載堉還從認識論上摒棄了程朱理學的先驗因素,強調“新法所算之律,一切本諸自然之理。而后以數求合于聲,非以聲遷就于數也。”[23](p.46)他從道家自然(即事物本然)觀出發,強調樂律數理本于客觀的聲學現象,并應以聲律實踐加以檢驗。朱載堉不滿足于三分損益律在數學形式上的簡單性,而是以81檔特大算盤連續開平方、開立方,最終求出2的12次方根的近似值1059463。道家道教的實證精神,正是這一認識論來源的基礎。
被錢大昕目為“國朝算學第一”的清初數學家梅文鼎,曾直接受教于道教歷算學者。27歲時“師事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旋所藏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鼏共習之。稍稍發明其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后增為四卷,倪為首肯。”[24](梅文鼎傳)梅文鼎及其兄弟師從道教歷算學者倪觀湖學習日月交食之原理及計算方法,為梅氏家族日后在歷算學上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礎。可見,道門中人所傳承的數學、天學在清代早期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另外,李光地曾對梅文鼎談到:“歷法至本朝大備矣,而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趣也。宜略仿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24](梅文鼎傳)梅文鼎于是著《歷學疑問》三卷,果然“仿元趙友欽《革象新書》,務從簡要”[25](p.419)。故而道士趙友欽之天算學術,在梅氏開清代歷算學風氣時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清初醫家徐大椿,以內丹術語“靈胎”為字,晚號洄溪老人、洄溪道人,頗好道學,曾注《道德經》、《陰符經》,收入《四庫全書》。此外,徐氏還撰有《洄溪道情》這樣的道教文學作品,傳誦一時。徐大椿曾謂:“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蓋六經為中古以后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于上古圣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并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26](p.522)這種“離經叛道”的“異端”的言論,自然招致非議。《四庫提要》便批判其書“躋《老子》于六經上,則不可以訓”[26](p.522)。但是,我們由此也以看出,徐大椿并非一般儒生,而更是一位道家道教學者。此外,據袁枚所著《徐靈胎先生傳》記載,徐大椿“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27] (p.579)。可見他亦曾研究天文、地理、數學、音律乃至軍事技術。
乾嘉時期,廣東著名道士李明徹,“有茅容之風”[28] (p.745),12歲便到羅浮山沖虛觀入道,并自習西洋油畫。他一生研修道學道術不輟,年逾八十仍神氣不衰,曾注釋《道德經》、《黃庭經》,撰《證道書》一卷、《修真詩歌》三卷。李明徹更曾學習西方天文學、地理測繪學和三角幾何學,著有《圜天圖說》三卷、《續編》二卷,又協助兩廣總督阮元,參與《廣東通志》中的地圖繪制工作。晚年創建純陽觀,在觀內建造朝斗臺以觀測天象。《圜天圖說》卷上論及太陽系天體位置及運行、日食月食、晝夜節氣變化,卷中除關于行星、恒星觀測及計算問題外,還記載了全國19處府地的日出日入及諸節氣時刻的測定記錄;卷下談論地理學問題,其中收錄了全國21省首府(含京都順天府)北極出地度數。《續編》除補充天文學內容外,還設專節科學地解釋了各種常見的天文、地理現象。阮元對《圜天圖說》有較高評價,認為:“欲為天學者得是書讀之,天體地球、恒星七政可以了然于心目間,回之以求弧矢割圓諸術甚易也。是書可為初學推步之始基矣。”[29](p.628)并將《圜天圖說》三卷著錄于《廣東通志·藝文略》。限于時代背景,李明徹天文學體系仍以地心說為基礎,較之西方天文學的發展水平仍有較大差距。但此書對于當時中國的科學普及,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圜天圖說》中的數學內容,主要是討論測量問題的幾何、三角知識,見于《表度說》、《用日高分直景倒景立算》、《分表立表用法》、《隨地測節氣定日》諸節。從中可見,李明徹除繼承中國傳統數學外,亦多吸收西方數學知識。但需要探討的是,李明徹的數學、天文學與其道教信仰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呢?過去學者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或逕稱崇尚科學和追求實證本是道教的精粹[30](p.52),或認為李明徹之個案已體現出道教與科學的新型關系,表現在“道教旁征博引的包容性,以及道教和科學互相補充、相輔相成的關系”[31](p.65)。然而,筆者認為,李明徹研習科學與其道教信仰本身有著內在的關系。
其一,研習科學可以積善累德,以全真行。全真道素來強調修道除內煉真功外,尚須外積真行。作為全真龍門派第二十代弟子,李明徹一生積功累行,不事舉業以追逐名利。除刊布道書、捐資立觀度人外,他還曾運用天文氣象知識,預見廣東當有旱情,勸阮元進口洋米備旱,成功地避免了一場災害。明徹“雖為當道所重,然清靜自守,有請托者,輒以世外人拒之”,故陳伯陶稱贊他“仁言利溥,真有道之士”[32] (p.255)。
其二,對于李明徹而言,研習科學亦可以升華其道教信仰。李明徹一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六合八荒,千仞三泉。凡前人推步占驗之書,無不留心考究。”[28](p.745)李氏治學之動力,正源于天文星象在道教中所具有的神圣意義。《圜天圖說》卷上《渾天十重圖》第十重注明:“天皇大帝諸神圣所居,永靜不動”[29](p.639),其說雖源于西方天文學,但對于李明徹而言,“天皇大帝”及“諸神圣”顯然是道教意義上的。他晚年在道觀內建朝斗臺,亦兼有神學與科學雙重意義。黃一桂跋《圜天圖說》稱:“青來道人清靜寡欲,而于事物理趣多所窮究,得輒默識于心,未嘗為人言,人亦無知之者。年七十矣兀坐終日,泊如也。”[28](p.743)可見他寄情于科學研究時,其心境亦臻于清靜無為的境界。其治學路徑頗似邵雍,合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為一爐。
總之,研習天文、地理、算數之學對于李明徹來說,與其道教信仰和修道實踐,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這與明清以前的道教科技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在明清時期,道教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心態,吸收西方科學中的先進因素。
李明徹并非當時唯一一位學習西方科技的道教學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亦提到一個通曉西方天文、地理知識的道士。此道士概述了西方傳統地心說的宇宙圖景,稱“天橢圓如雞卵,地渾圓如彈丸,水則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皺。橢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并在地圓說基礎上分析到:“海至廣至深,附于地面,無所障蔽,故中高四隤之處,如水晶毬之半。日未至平地,倒影上射,則初見如一線。日將近地平,則斜影橫穿,未明先睹。今所見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33](p.16)闡明了日出大海時所涉及的光學原理。
當然,該道士所批評的儒、佛兩家宇宙觀,僅僅是某一歷史階段某些儒生和佛教徒的自然圖景。但我們從這段資料(蓋非信史)中,卻可以看到批評者所持有的某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認為道教掌握更為先進的天文歷算學。儒家學者在記錄這段故事時,似乎也默認了這種觀念的合理性。可以認為,這種自信既源于道教的科學傳統,亦反映出清代道教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包容心態。李明徹正是在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下,積極地學習西方先進的數學、天文學,并加以吸收轉化。
乾嘉時期另一位學者紀大奎,有人盛贊其學“聯儒釋道為一家,合天地人為一體”[34] (p.1)。就道教方面來說,紀氏曾師從傅金銓學習道教內丹術。故雖案牘勞形,而享壽八十[24](紀大奎傳)。在內丹學方面,撰有《周易參同契集韻》、《俞氏參同契發揮五言注摘錄》,并輯訂《悟真篇》三卷。《清史稿·藝文志》還著錄其《老子約說》四卷。除丹道、老學外,他又撰《筆算便覽》一卷,梅啟照重刻《算經十書》時附錄此書。因紀大奎在數學上的貢獻,諸可寶《疇人傳三編》、張之洞《書目答問》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算學家》補《疇人傳》、《續疇人傳》之遺時,均將紀氏收入。
二、道教對明清數學家的影響
明弘治、正德年間學者鄭善夫,除以詩文聞名外,亦精于數學、歷法,著有《序數傳》、《九章乘除法》、《九歸法》、《改歷元疏》、《日宿例》、《時宿例》、《田制論》等。正德十五年(1520年),鄭氏研究日食后發現現行歷法已誤。上疏請求改歷,強調“宜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刻分秒,必使奇零剖析詳盡。不然,積以歲月,躔離朓朒,又不合矣。”[35] (p.3529)可見他對于歷法數學精確性的要求和科學實證的精神,這與朱載堉舍棄三分損益法而求新法密率的態度是一致的。
實際上,鄭善夫又信奉道教,曾自嘆“少年逐鉛槧,學道苦不早”[36] (p.127),感慨自己追逐詩文而沒有早日學道。他親身實證道術,先是燒煉外丹,以為“驅辟百邪,為須金石之藥”[36](p.188)。遭遇失敗后又轉向內丹性功,詩云“有身終是盡,學死始長生。吾將煉真性,去去凌紫清。”[36](p.127)鄭善夫雖學本陽明心學,但亦明確反對俗儒排斥佛老的做法。據稱,鄭善夫“卒年三十九,卒之日,紫氣勃勃不散。先是,善夫衣褐走雪中,游天臺山,人以為神仙。”[36](p.301)可見鄭善夫與道教的淵源之深。而道教內外丹術的實證精神,對鄭善夫潛心數學、歷算研究,當有一定影響。
弘、正年間另一數學家顧應祥,號箬溪道人,亦為陽明門下。顧氏又信奉道教,認為道家之術其一為“祠禱”,而“人之生也,不能無疾痛患難,不能不禱于神明,必藉夫能事神者,以達其意”[37] (p.35)。可見顧氏所祈禱的對象,當為道教神靈。顧應祥又稱:“自幼性好數學,然無師傳。每得諸家算書,輒中夜思索至于不寐,久之若有神告之者,遂盡得其術。”[38](p.975)雖然“神告”只是比喻,但也可見道教信仰實則構成了顧氏研究學問的心理動因。此外,顧應祥著《測圓算術》時,還曾引孫思邈“膽欲大而心欲小”[38](p.1109)之語,顧氏《靜虛齋惜陰錄》卷六曾摘錄長春真人丘處機論日不入地之言[37](p76),故而道教科學思想對他亦有一定的影響。
嘉靖年間學者唐順之,“歷數之學得箬溪顧尚書傳其法,又得東皋周臺官秘書印證。常云:‘知歷理,又知歷數,此吾之所以異于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于歷官。”[39](p.105)一般儒生只知歷法原理,并不一定精通歷數;歷官雖知歷數,卻不知人自身亦有身心變化的規律。此“活數”一則有心學涵義,二則有道教內丹學的影子。王慎中便曾論及唐順之的內丹修為:“荊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40](pp.116-117)即是丹道所謂精氣不耗的筑基功夫。唐順之著有《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等,對周述學、程大位等數學家有一定的影響。
明末學者徐光啟談到中國數學衰落原因之一,在于“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實事”[41](p.77),但誠如陽明弟子萬虞愷所言:“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40](p.118),道教內丹學、陽明心學均為針對人身心的實證功夫,并不僅僅是理性思辨之學,此種實證態度與自然科學精神本可以相通。另外,陽明心學在技術層面又多受內丹術影響。上述鄭善夫、顧應祥、唐順之等人,之所以能于數學、天學方面做出成就,與內丹學講求實證的傳統是一致的。當然,廢棄實學、空談心性,則為王學末流之失。
除心學一系的數學家頗有信仰道教、實修道術者外,陳壤、袁黃師徒,亦為受道教影響較深的歷算學者。袁黃曾著《歷法新書》五卷,“其天地人三元,則本之陳壤”[35](p.3554)。由《疇人傳·袁黃傳》的記載可知,其三元之說,是對歷法中上元積年計算問題的發展。又《千頃堂書目》卷十三提到,他“得歷法于終南隱者陳星川”[42](p.360),星川當為陳壤之字號。而道教崇尚天地人三元,金元數學史上的重要成就天元術與道教有深刻淵源[43](pp.121-136),終南山又素為道教隱修勝地,陳壤當受到過道教文化包括道教數學思想的重要影響。其徒袁黃,對善書文化影響深遠,是明代著名的佛教居士。但據酒井忠夫先生考證,袁黃“在其修道的最初階段受到過道教信仰的洗禮,而且在進入立命信仰的時代以后,雖然他拋棄了道教中的宿命論要素,但并沒有脫離道教信仰”[44](p.325)。袁黃對天文、河洛、水利、役賦,以及奇門、六壬、歧黃、堪輿之學,都有研究,尤其精于象緯歷法,知回回歷術,是明末少數非歷官而知歷者。
清代之初,朝廷對道教有所限制,西方科技的影響力亦逐漸擴大,但道教對傳統數學的影響仍然持續。清初名臣李光地便好道家言,更自稱“因《參同契》悟得《易經》道理”[45](p.355)嘗奏康熙帝曰:“臣有一親戚好道家說,臣嘗問之云:‘鐵亦好物,可以定子午,道家總不貴重,只說丹、砂、鉛、汞。豈以其為爐鼎之用,烹煉大藥,可以服食耶?他應曰:‘然。臣曰:‘以愚觀之,殊不爾。蓋銅鐵煉到底,只是銅鐵,惟砂里有金,鉛里有銀,都非從外覓得,可以煉出寶來。以喻人血肉之軀,有至寶存焉。”[45](p.355)可見,李光地認同道教內丹學,對內丹修煉的要領亦有領悟。李光地還指出:“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45](p.359)并特為表彰重心性修煉的魏伯陽一系之神仙道教,他對符箓道派雖有微辭,卻亦能有同情之態度。李氏對《陰符經》又頗推崇,曾發揮《陰符經》“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45](p.355)之旨。總的來說,李光地是一位受道教思想影響較深的學者,他所著《參同契章句》、《陰符經注》,均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歷算方面,李光地著有《歷象本要》二卷,還曾向康熙帝推薦梅文鼎。梅氏至京時,曾設館于李家,為光地及其子、弟數人教授歷算,李氏之子、弟亦各有著述。應當說,李、梅二人之間的交游,不但促成了兩個歷算學家族在學術上的進步,對于清代歷算學的發展也起到不可忽視的影響。
年希堯,嘗任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等職,亦為清初受道教影響較深的數學家,曾向梅文鼎請教數學。著有《測算刀圭》三卷,《面體比例便覽》、《對數表》、《對數廣運》各一卷,《視學》二卷,校刊梅文鼎《方程論》及《度算釋例》。年希堯博學知醫,所輯《集驗良方》中不但收錄有許真君七寶如意丹、天河不老丹等大量道門驗方,其中《養生篇》所述養生功法更源于《靈寶畢法》等道教養生著作,而他在輯錄這些道教修煉要旨及驗方時曾經指出:“竊幸發命意志,先得我心之所同。”[46](p.1)則表明年氏深曉道教養生之法,其所撰《測算刀圭》一書更以金丹術術語“刀圭”為題,亦可證年氏數學學術與道教之淵源。
清代著名文學家劉熙載,“生平于六經子史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一以躬行為重”[24](劉熙載傳),嘗作《戲為嬰兒頌》,稱“我與‘嬰兒,雖一生之相從兮,亦嬰兒為主,而我但為賓”[47](pp.657-658),表明他對老子嬰兒本論的推崇和躬行。劉熙載不但長于經學、文論,兼通仙釋,對數學亦有心得,曾著《天元正負歌》,以歌訣形式概括了算術中的正負問題。
清末道士李理安長于天文歷算,曾供職于欽天監,傳《天文圖》于世。并在1936年于長春觀重刻《天文圖碑》,此碑中部為天文圖,繪有二十八宿星座。他還編撰有《長春觀志》四卷,有1936年排印本,收入《藏外道書》、《中華續道藏》、《中國道觀志叢刊》。該志卷三節錄《周髀算經》,并于《天文詳節》、《卜歲恒言》兩節中,收錄有天文、氣象方面的資料。
三、明清道教與傳統數學互動的歷史影響
明清時期,盡管面臨著西方數學和西方宗教的沖擊,道教與傳統數學仍然各有發展,并相互影響。就其積極意義來說,大量道士或道教學者直接參與數學,以及與數學密切相關的天文歷法、律學等科技領域的研究,直接推動了明清傳統數學的進步。清代梅文鼎曾受業于道士倪觀湖,開啟清代傳統數學復興先河,即是典型例證。其次,道教的科學實證精神一度成為明清數學家突破禁錮、取得成就的重要思想資源。正是如此,朱載堉方能徹底舍棄載于儒家經典的“三分損益法”而另創密率。最后,道教特有的包容精神,使得道教在繼承傳統數學的同時,亦能吸取西方科技的長處。嶺南道士李明徹不但繼承傳統的數學、天學和養生學,對于西方科技、藝術亦能學習、研究,成為近代廣東著名的道教科學家。
然而,明清時期道教與傳統數學互動的歷史局限仍然是明顯的。就數學對道教的影響來說,與以往數學研究推動道教思想更新不同,明清時期傳統數學以及部分道教學者接觸到的西方數學和科技,并未能成為推動道教發展的思想動力。傳統數學對道教的影響,也僅略見于內丹技術之中,且明清兩代已經沒有如元代趙友欽一般,在丹道與科技兩個領域都能發揮重要影響的學者。數學不再成為道教思想發展的動力,這也正是明清道教學術衰落的一個重要表現。
就道教對數學的影響來說,雖有述積極方面,其消極作用也必須正視。李申教授曾談到,清代乾嘉時代漢學家們“認真鉆研古代傳統數學的時候,也減少了對西方數學的興趣。他們不是把數學引向未來,而是引向過去。”[48](p.420)這一評價對于道教學者也是適用的。雖然李明徹等道教學者已經學習、融合西方先進的數學和科學技術,然而,這一努力卻并沒有得到道教界的普遍響應。道教始終未能營造出積極吸收西方科技的文化氛圍,這也正是中國傳統科技衰落的表現之一。
[參 考 文 獻]
[1]梅榮照.明清數學概論[A].明清數學史論文集[C].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2]阮元.疇人傳[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3]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 三聯書店,2003.
[4]御制數理精蘊[A].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數學卷三) [C].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5]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第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7]王韜.弢園尺牘[A].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C].北京:中華書局,1982.
[8]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冷謙.琴聲十六法[A].項元汴.蕉窗九錄[C].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0]姜紹書.無聲詩史[A].于安瀾編.畫史叢書[C].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11]戴良.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A].宋濂全集[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2]吳一琦.宋濂《楚客對》中的月食知識和地形觀[J].中國科技史料,1994,(1).
[13]誠意伯文集[A].四部叢刊初編集部[C].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14]逍遙山萬壽宮志[A].藏外道書(第20冊)[C].成都:巴蜀書社,1992.
[15]藩獻記[A].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9冊)[C].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16]曾召南.試論明寧獻王朱權的道教思想[J].宗教學研究,1998,(4).
[17]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8]李迪,白尚恕.新發現的抄本《神道大編歷宗通議》[J]. 內蒙古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1,(2).
[19]劉勇,唐繼凱.律歷融通校注[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
[20]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A].道藏(第6冊)[C].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1]黃帝陰符經[A].道藏(第1冊)[C].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2]馮文慈點注.律呂精義[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
[23]馮文慈點注.律學新說[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
[24]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5]吳格整理點校.嘉業堂藏書志[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26]徐大椿.道德經注[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5冊)[C].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7]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小倉山房續文集[A].四部備要集部[C].上海:中華書局,1936.
[28]陳鴻章.圜天圖說續編序[A].藏外道書(第24冊)[C].成都:巴蜀書社,1992.
[29]圜天圖說[A].藏外道書:第24冊[C].成都:巴蜀書社,1992.
[30]王麗英.真有道之士——晚清道士李明徹散論[J].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報,2006,(1).
[31]甄鵬.清朝道士李明徹及其科學成就[D].山東大學,2006.
[32]陳伯陶.道士李明徹傳[A].廣東文征(第6冊)[C].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3.
[33]紀昀.閱微草堂筆記[M].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
[34]紀大奎.紀慎齋先生全集(第1冊) [M].清嘉慶十三年刻本,1808.
[35]明史·歷志一[A].歷代天文律歷等志匯編(十)[C].北京:中華書局,1976.
[36]鄭善夫.少谷集[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9冊)[C].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37]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A].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4冊) [C].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
[38]顧應祥.勾股算術序[A].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數學卷二)[C].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39]周暉.金陵瑣事[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40]王畿.王龍溪全集(一)[M].臺北:華文書局,1970.
[41]李之藻,等編譯.同文算指[A].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數學卷四)[C].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42]黃虞稷. 千頃堂書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3]蓋建民.道教科學思想發凡[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44]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M].劉岳兵,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45]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5.
[46]才惠珍點校.集驗良方序[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
[47]薛正興點校.劉熙載文集[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48]李申.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隋唐至清代之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作者系西南大學講師,哲學博士)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