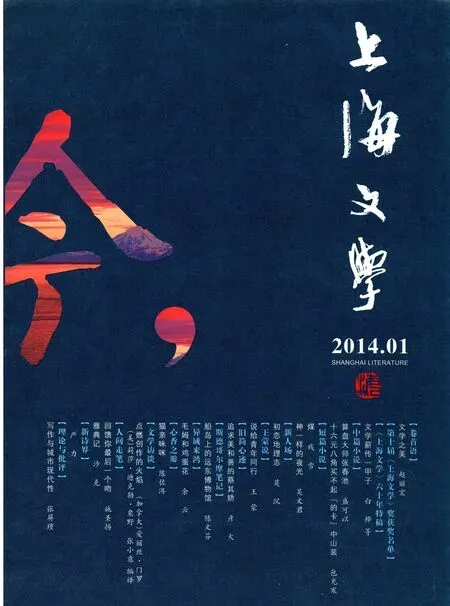好像親人在注視你
孫頻
一個小說作者和一本雜志之間也是有緣分存在的,這類似于兩個人之間的神秘相通。現在想來,我和《上海文學》之間就是這樣的。
那是2009年的時候,我剛開始寫小說不久,一共也沒發表出兩三篇小說。當時我剛剛寫好了一個短篇小說《魚吻》,因為一個雜志編輯都不認識,只能往郵箱里亂投稿,這個小說碰巧投給了當時《上海文學》的編輯張重光老師。一個剛開始寫作的年輕作者發稿子是很費事的,投出去經常就杳無音訊了。我投出去后也沒報太大希望能得到回音。可是沒想到,大約兩個月之后張重光老師忽然給我打來了電話,說《魚吻》那篇小說他很喜歡,并說我如果是“80后”的話,他打算把這小說推薦到《上海文學》“中環杯”短篇小說大賽中去參賽。我聽了很高興,但也沒報太大希望會得獎。沒想到在2009年年底的時候我得到《上海文學》的通知,說我那篇《魚吻》獲了二等獎。
雖然寫作至今也沒得過幾個獎,但這個獎是我開始寫作后獲的第一個獎,所以意義不凡。當時,對一個剛剛開始寫作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鼓勵。我在興奮之余才知道,在評獎開始時張重光老師就退休了,后來編輯修改我這篇小說的是《上海文學》的年輕編輯甫躍輝。他當時剛去《上海文學》工作,后來他一直是我的責編。因為他自己也寫小說,我便經常與他交流些寫作上的問題和困惑,受益很大,這幾年時間里他給了我很多啟發,也給了我很多信心。
2009年至今,四年已經過去了,回頭想想,從《上海文學》這里真的得到了很多。除了文學上的鼓勵,還有一份人間的溫暖。有時候去了上海便去他們辦公室小坐,和責編聊聊小說,有時候金宇澄老師也在,便也向他討教幾句,感覺他為人隨和卻目光如炬,似乎幾眼就把人看到底了。原來只以為他是個好編輯,后來看了他的《繁花》才知道,原來他的小說寫得這么好。我至今懷念他們那洋房里的辦公室,巨大的吊燈,盤旋而上的樓梯,華麗的彩色玻璃,還有那高大房屋里的壁爐,象征著獨特的海派文化,以及爬了一墻的蒼翠爬山虎。這里被王蒙老師稱為是海派文學的主辦基地。王安憶的《小城之戀》、阿城的《棋王》、韓少功的《歸去來》、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都是發表在這里的。對于一個年輕的作者來說,寫作能從《上海文學》起步是一種榮幸。
幾年時間里《上海文學》對我還是一貫的扶持與鼓勵,從2009年《魚吻》之后,我又陸續在《上海文學》發表了小說《磧口渡》、《月煞》。每次在《上海文學》發表小說后都會陸陸續續聽到有人和我說,剛在《上海文學》上看到你那個小說了,感覺不錯啊。選刊也關注著我在《上海文學》發表的小說,想來這還是因為《上海文學》這么多年的文學口碑以及擁有自己固定的讀者群,我發表的小說才會受到關注和喜歡。
有這樣一份雜志在你身后,就好像一個親人在默默注視著你,讓你溫暖而無所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