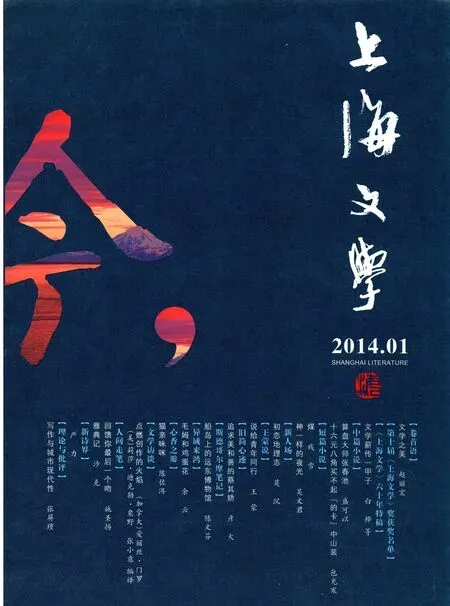船島上的遠東博物館
陳文芬
楔子:初見遠東博物館
七年前,一個夏天的早晨,飛機即將抵達斯德哥爾摩。
坐在我前座的日本歐吉桑指頭敲敲艙窗,要我快看地面,滿目的綠樹森林與湖泊,小積木一般美麗的木屋。有一部上了年紀的Volvo汽車到機場來接我。我們只在“燕鼻子住客之家”的單身公寓小坐片刻喝碗清茶,開車直奔東方博物館,到那里找史美德、張琳跟遠東圖書館的馮遼。
歐洲人稱斯德哥爾摩“北方的威尼斯”,風景像一座老式風景電影三百六十度全銀幕展開來,波羅的海內灣的海洋全景,將一座魁偉的正字形王宮包括在內。東方博物館高踞在王宮對面一處出峭的高地,實則是一個獨立的島,叫船島。
遠東博物館旁邊的現代美術館,在世界上的美術藝展頗有聲名,船島上擺設了法國女藝術家Niki兒童趣味濃烈的女性雕像,等春天那些雕像噴水綠草發芽時,船島就鮮亮起來發光了。
遠東博物館本身是座名建筑,它原來屬于海軍轄下的房舍也許具有一些防衛的功能。建筑師是跟建筑王宮的“田系”家族是同一個家族。王宮以及隔著海正對著王宮的國立美術館(皇家美術館)都是這位建筑師的作品,從美術館走到船島要經過一座橋,你從橋上望見整座島旁邊的風景,有些搖曳古老的小船,跟著海浪搖晃穩定的鵝鴨,偶然隨陰天刮風尖叫的海鷗,一座巨大的帆船泊在島的岸邊。我有好多次望著那艘船想著,1901年地質學家安特生跟著諾舍德探險隊去南極不會是這艘船,可型式也相去不遠?那時候,他開始想到他去中國了嗎?
我很慶幸我到瑞典的第一天見證了博物館史美德、修復紙張專家張琳、圖書館長馮遼一起工作的時代。但凡是在博物館跟圖書館工作過的人明白那些美好的時光,總是包含三個元素:建筑物、藏品、人。人——包括了工作人員與參觀者,只有“人”的元素能將過去的時光與現在的時光像針線一般密密地縫合起來。
史美德是挪威人,年輕的時候來到斯京跟馬悅然學漢語,很早就立志做藝術古物研究。她的身形富態,金發,看起來有點累。漢語說得非常流利,眼睛總半瞇著,眼鏡掛在鼻梁上,隨時說話都好像在調整視焦想看清楚古物上的圖騰與花紋。
我曾經聽說過關于她的故事,可以聯想魯迅贊賞哈姆生小說里頭挪威人的高貴品格。一個年輕女學生在雪夜里頭扛著報紙送晨報,倚靠送報的收入完成學業,連她的業師悅然也十分尊敬她求學的品格。1968年左派學運熾熱時,學生們之間總有十足的熱情講些非關學業的話題,我偶然聽到這段“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革”課堂小片段來跟她求證,那段近乎見義勇為喝斥同學的談話,據說從此為大家節省很多力氣,專注學業。她那時很吃驚地反問我,“老師抱怨了這件事情嗎?我知道老師當年非常辛苦。”我說,“一點也不!他說這段故事只是為了贊賞你的品格,不是每個人都能這么懂事又爽快的。”美德聳聳肩膀有點不好意思說,“我們年輕的時候沒有誰是‘不左的,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當時我忍不住說了他們一句,大家都是來讀書求學,不要那么不痛快。”
史美德在臺北故宮、北大古物學術圈有很好的人脈與自己的研究專業的仰望。她將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遠東博物館,她去年退休以后,當然成為北歐某種“博物館研究人員”時代過去的一種象征。她是歐洲博物館界少數既有漢學專才又是藝術史學者的專業人士。
有一次我專程到她的辦公室談話,當時試圖收集當代漢學方面的采訪資料。想問她年輕時基于什么考慮選擇到斯德哥爾摩來讀書。她說,“非常容易回答,一是斯京有漢學,二是斯京有博物館、有藏品。兩件都有,這個城市值得來,我就來了。”
史美德說得對。環顧歐洲有許多迷人的古老城市,哪一個城市在正確的歷史時機,既有漢學又有中國藝術品的研究收藏?
史美德描述自己青年時代的抉擇時,是那么準確地描述這座船島在地球上的形象。
從古生物、考古、青銅、玉器、藝術收藏、漢學語言學,所有古典的“中國研究”知識學派,遠東博物館將這一切包括在內。
安特生的時代
2013年秋天,馬悅然跟我返鄉回臺北探親,在南海路的歷史博物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歷史文物陳列館一次接著一次看到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展館的陳列室佇立的照片跟形象。人們尊稱他是“中國現代考古之父”,當之無愧。跟斯文赫定比起來,安特生在瑞典歷史的名人形象里頭,帶著一種沉靜的形象。他有個雅號叫“中國的Gunnar”或“中國的安特生”。
我讀初中的歷史老師,是個大陸來的女老師,她講故事可真起勁。她講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直立人”,中國大片江山歷史一下子穿越時空進入了史前史,我們真喜歡她。她是浙江來的,口音軟軟的,常常講些自己的歷史價值觀。她說“政治都是不高妙的,‘黨這個字尚黑”之類的,這在當時臺灣的教室里不多見。那時的歷史老師多講南京,民國政府跟南京比較有感情。那時的課本還堅持民國的“北平”,講考古會跟現實的政治驅離開來,自由得多,所以當她講到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跟北洋政府的合作發現,我們只稍稍注意到瑞典這個小國家,然后就沉浸在仰韶的彩陶文化中。彩陶也形似歐洲或非洲的古文明,史前史的世界在洲際、國際的界限之上,將外國人對此事的影響全然拋開,忘個干凈。
安特生早就對地質學感興趣。1901-1903年他參加了奧托·努登舍爾德(Otto Nordenskj?觟ld 1869-1928)的南極探險隊,安特生擔任第二領導人。旅途驚險,船擱淺了,安特生跟努登舍爾德兩人分散,安特生跟幾個人呆在一座冰島上,吃企鵝肉熬過艱苦的寒冬,一直等到春天才有人救他們。
1906年安特生做了瑞典地質考察研究所的所長。1914年北洋政府找上他,中國地質考察研究所的所長丁文江是安特生的上司。安特生從此帶領一批中國有志于此的學者,把他們領進了這一途。1914-1925年,他在中國發現仰韶文化等五十個考古遺跡。
1926年為了讓安特生帶回這些古文物,瑞典政府創立了遠東博物館。安特生帶回大量的考古文物,這是當時民國政府同意的,簽訂協議在1927-1936年,分成七次送回大量的中國文物。當時南京還有個考察研究所大樓,1936年文物送回中國,1937年安特生親自回到南京看過新展,以后他很遺憾地得知,多數送回的文物在那一年發生的戰亂當中丟失。
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的存在,首先是“仰韶文化”出土以后,一個新的史前史觀的世界象征。博物館以安特生在中國發現五十個史前史遺跡,準備做科學性的研究。當時瑞典的環境,若僅有一個“中國的安特生”還是孤掌難鳴。
描述遠東博物館館藏的關鍵人物以前,我想把安特生跟斯文赫定兩人的歷史地位做比較。
斯文赫定很早就立定志向成為探險家,十五歲時在斯城南區的高坡上看見諾舍德(Adolf Erik Nordenski?觟ld 1832-1901,他的姓跟努登舍爾德幾乎相同,拼法不同,都是貴族)從北極航向日本探險隊成功歸來,全城民眾鳴放煙火歡迎他的場面,激發了斯文赫定走向探險之路。南區的高坡就在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住家附近,每次到特翁家里的沿路上,我常常想到斯文赫定怎么看到全城的歡呼啊,肯定是激動歡喜升華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需知道,現在激勵瑞典人的具象方法,往往是伊布在足球場上對抗英國足球隊,以一記神奇的倒掛金鉤球入網,這樣電視反復播放到全瑞典民眾歡騰。
斯文赫定是瑞典歷史上最后一個,因為個人的科學成就封爵,從北歐出發到中亞,從地理學上確認羅布泊位置,確認長城曾經到過新疆,發掘樓蘭等古代城市,他也完成階級旅行,從平民走到貴族。他入選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瑞典學院院士(后者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機構),他的重要發現,主要收藏在瑞典人類博物館,發現的對象太多,館藏還有很多箱子留存許多年還沒打開來研究。
1950年,年輕的漢學家馬悅然從中國回來,報紙登了消息,斯文赫定請他到家里來喝茶,一派老君子的古典作風。我在瑞典生活過一段時間,已能理解上一個時代作為那種“保皇黨”的意義。斯文赫定的教育背景都在德國完成,當時瑞典的高級知識分子幾乎都是“愛德國”的納粹(可參考特朗斯特羅姆的青少年回憶《記憶看見我》)。由于他當時的言論跟表態的傾向,瑞典人后來有點矯枉過正,非常介意他的言論,影響了他的歷史評價。初到瑞典來時,我特別想找尋斯文赫定發掘的中亞古代城市的面貌介紹,始終沒見到博物館為他做專題大展,后來才知道,竟然瑞典學者要求他的肖像畫必須從皇家科學院的墻上卸下來,擺進倉庫里頭。
跟斯文赫定相比,安特生是個更加純粹的考古學者。前者長于古代城市的發掘,后者著重于中國史前史的遺跡。他比較年輕,沒有趕上封爵“最后的貴族”時代。要是在英國,Sir Andersson的燕尾服該掛滿勛章。安特生似乎沒有留下一個鮮明的脾氣品格或者什么特別的形象,他的家庭,他的后人很少留下印記。我認識斯文赫定協會的會長,根據他描述,斯文赫定個人終身未婚,赫定一家人從父親到姊妹們都對他呵護有加,幾個姊妹當他的秘書,也都沒有結婚。
創立于1925年的遠東博物館的藏品來源,一是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以來的考古遺跡;二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儲與“中國委員會”的收藏;三是鐵路工程師卡爾貝克(Orvar Karlbeck 1879-1967)為博物館購買藝術性藏品;四是接任安特生擔任館長的漢學家高本漢在《博物館年刊》開始發表跟研究科學性的論文,以此建立了博物館在西方世界絕無僅有的收藏研究地位;五是攝影家文物收藏家喜龍仁(Osvald Siren,1879-1966)留下的文物。喜氏的收藏本文暫且不提。
王儲與中國委員會
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儲(Gustaf VI Adolf,1950年登基,1950-1973年為瑞典國王)年輕時在烏普撒拉大學讀地中海、北歐考古學、歐洲藝術史,1908年訪倫敦,看了中國藝術大展,從此對中國的玉器、青銅器、瓷器感興趣,精研青銅器,特別喜愛漆器。1914年王儲在斯德哥爾摩策劃自己的中國藝術收藏,也從德國英國借展。
1919年他建立中國委員會,1921年開始擔任主席,曾經為諾舍德找到許多探險經費的Panlander,也是委員會成員,透過他的募款,委員會有了財源,購買館藏。1925年遠東博物館”創立屬于“皇家人文科學院”(有時譯為“歷史人文社會考古學院”,屬于古斯塔夫三世國王創立的三個學院之一)。
北歐王室歷史充滿才華洋溢的能人悍將,古斯塔夫六世王儲本人,若非王室成員,肯定是一個杰出的學者大師,他的叔叔尤金王子是著名的畫家,許多藝術家的贊助人跟支持者,自己的收藏甚多,也留下一座美麗的美術館,他的弟弟是丹麥著名的銀器裝飾公司George Jensen的設計師。
王儲在中國委員會主席任內,于1926年遠赴中國跟日本訪問。在山東參加一個研討會,也在山西太原見到閻錫山,王儲對閻錫山的印象非常好,跟閻錫山吃過飯,認為他是一個謙謙君子。可以跟這個故事連結的是高本漢,1910年在山西大學堂教書,親臨了辛亥革命巨變的中國,閻錫山的軍隊打進太原城門,高本漢目睹過程,寫了一篇新聞報導寄給他在《每日新聞》報當總編輯的哥哥刊登。
1928年,瑞典王儲還在北京戲臺看了梅蘭芳演戲。王儲看戲肯定成為他登基國王以后頒贈勛章給梅蘭芳的因緣,1956年瑞典王國贈給梅蘭芳的勛章,授勛儀式在北京王府井旁邊的南河沿瑞典駐北京大使館的夏天花園里舉行,擔任大使跟梅蘭芳的翻譯是使館當時的文化秘書馬悅然。
阿道夫古斯塔夫六世國王將自己所有的中國文物收藏都贈給了遠東博物館。以后,國王的孫子古斯塔夫十六世繼任王位,2012年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王依例在王宮宴請諾獎得主,宴會以后國王跟莫言談話甚久,這是比較少見的情況。我猜現任國王跟祖父的感情很深(國王五歲的時候,父親飛機失事猝逝),國王童年時期的照片多數與祖父攜手出現。相信國王很為祖父的中國藝術品收藏感到自豪。他跟莫言談得來,也是因為莫言的農民背景,國王熱愛農業豬馬牛羊,還說受歐盟補助來務農。
1925年遠東博物館創立以后,出現一個專門替博物館購買藏品的專家卡爾貝克,他是修筑京滬鐵路的工程師。他在長達二十年修建鐵路的過程中,學會收集戰國漢朝的青銅器,是銅鏡專家,也精于欣賞瓷器,1927年回到瑞典。1928-1934年之間,常常回中國為博物館買東西,眼力很好,為國王、有錢的商人買東西,卻不為自己買東西,1934年回到瑞典。這段時間博物館的收藏量大增,收藏也比較全面。
高本漢時代
對遠東博物館有影響力的第四個人是漢學家高本漢。
高本漢(Berhard Karlgren,1889-1978)1915年在烏普撒拉大學考了博士,1918年任歌德堡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當了好幾年的大學校長。1939年自愿離開歌德堡大學校長的位子,開始對青銅器感興趣。高本漢在漢學語言學方面重要的著作早已經發表完成,忽然采用語言學的方法來研究青銅器的花紋,這是偶然發生的,他認為青銅器的紋飾是一種語言,完全可以使用語言邏輯來研究。1940年代他開始寫大量的青銅器研究。而遠東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向政府請求,他的繼任人選必須是高本漢先生。
高本漢是最早利用青銅器將殷商周分類出來的學者,1933年王儲建議他策劃一次早期的青銅器展覽。王儲自己也提出一套青銅器的分類的方法,而高本漢也延用了這個方法。
從1929年開始,高本漢為了研究館藏品做出很大的貢獻,他在1939年正式接任館長以前,已經出版八卷年刊,每一卷都有一篇到幾篇很有價值的科學論文。
高本漢發表《中國音韻學》以后曾震撼整個中國,但是他沒有將任何著作論述拿到美國出版社去發表,去掙得非常可觀的版稅。他安安靜靜地把著作全放在博物館的年刊,沒有稿費,他是一個完全不懂得也不去想經濟問題的學者。
故事寫到這兒,我仍不明白1940年代到1960年代,遠東博物館的館址在哪兒?船島上的遠東博物館1963年才搬進來。我記得每次從國立美術館旁的橋走向船島,橋上有個王冠,形象好看,無數的觀光客在此留影,把自己跟王冠跟船島的背景入鏡了。遠東博物館高踞在那里,人們可以仰望,那是夏天。可在寒冷的冬天,高本漢提著公文包,走向船島,無情的北風刮向身材不高的偉人,高本漢最不喜歡走上這座橋。我也不喜歡,冷得可怕極了!好幾次遠東圖書館友誼會開會得從高處走下來,在橋頭等待公交車接駁進城。等待好煎熬,從高處落下來的海風只能把身上的冬衣裹得更緊。
馬悅然第一次與高本漢見面,高的辦公室在高等商業學校,樓房在斯微亞路現在的城市圖書館旁邊,以后遠東博物館跟歷史博物館共享同一棟樓房,高本漢的辦公室在頂樓,現在旅客去歷史博物館底下參觀維京時代所藏金子。1950年代馬悅然從中國回來到博物館拜訪老師,那時候安特生耳朵有點背,因為身形還魁梧,看起來說話嗓門有點大,而高本漢總在那張大書桌桌案埋首,從書桌抬起頭來看著安特生。
一如安特生的愿望,高本漢來擔任館長,還很費了一番力氣,當時許多政客反對,幸虧有一個能言善道的教育部長發表演說,為高本漢贏得館長的席位。無論如何,考古、藝術研究跟漢學的相逢,實則是個歷史的偶然。
高本漢一方面在博物館任職,一方面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中文。斯德哥爾摩大學是一個后起的大學,無從對這方面的知識做學術的準備,當時美國已經認識到理解中國的知識對于世界多么重要,高本漢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專家,美國煤油大王出了一筆學術經費讓高本漢收了學生教漢學。那時候高本漢的教學概念不是教大學生讀書,學會講漢語,而是要教出“學者”來,這些學者顯然必須一學上手,就得踏上中國方言調查之路,交出音韻學的“研究”成果。至于上課的地點,完全看高本漢想要講“文本”還是“音韻學”,前者上課地點在斯大的法律系教室,后者在遠東博物館里頭。教學狀況很接近中國古代的書院,在遠東博物館學漢學,高本漢這批在斯大的學者徒兒耳濡目染都能辨識文物,對考古也都有相當程度的知識。
斯德哥爾摩大學建立中文系是馬悅然從澳洲堪培拉大學返瑞以后,在1965年建立的,在斯大擁有中文系以前,遠東博物館是北歐漢學家的教室。跟馬悅然同期的同學易家樂(S?觟ren Egerod)先生,遠從丹麥到斯京求學,后來成為丹麥漢學重鎮,研究著重漢語歷史、漢語音韻學、漢藏語系、泰國語歷史、臺灣原住民泰雅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