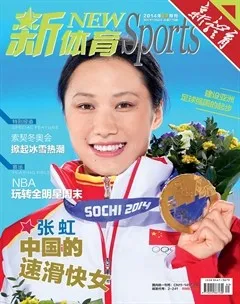球隊更名的背后
熱衷于制造麻煩的朱駿離開了,可是圍繞著申花的風波卻未結束。作為新入主的投資人,上海綠地集團燒起的第一把火就是“改名”:俱樂部名稱從“上海申花聯盛”改成“上海綠地”,球隊名稱則從“上海申花”改成“上海綠地申花”。更改的方向很明確,那就是強化“綠地”的品牌屬性。
但“申花”畢竟是一個從1994年被使用至今的名字,因此面對綠地集團的改名決定,也有不少申花球迷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還找到了規則上的依據——根據網上搜索到的《中國足球協會關于中超俱樂部產權轉讓的規定》,其中第十五條規定,如果轉讓前俱樂部為中性名稱(不含股東企業名稱、商品名稱或品牌等)的,轉讓后不能對其名稱進行變更;如果轉讓前俱樂部為非中性名稱的,只能變更為中性名稱。倘若嚴格執行上述規定,那么“綠地”這兩個字似乎不能被加到俱樂部的名稱之中。
可問題在于,上述規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就在該版本的規定中,最后還有一條內容:“本規定在中超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及中國足球協會主席會議批準后生效。”那么有關“中性名稱”的規定是否被批準生效呢?至少從公開可查詢的范圍來看,這個問題對外并沒有明確的答案。而以國內足壇近年來的實際情況而言,俱樂部在被收購之后更換新東家名稱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原本具有中超身份的“陜西寶榮浐灞”,就在2012年把名字改成了“貴州人和”,這個明顯與其投資者人和商業集團有關的非中性名稱,照樣獲得了中國足協的認可。
由此可見,當年推動中超俱樂部使用中性名稱的設想,如今并沒能成為現實。原因很簡單,爭取為足球俱樂部打造百年品牌的大道理誰都會講,但這往往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比如當原有投資者無力繼續運營俱樂部時,必須依靠引進新投資者來實現起死回生,可此時對后者最具吸引力的條件就是在俱樂部名字里添加其品牌。倘若阻止這一點,結果很可能是俱樂部由于轉讓受阻而趨于消亡。所以在殘酷現實面前,理想化的設想也就只能被拋在一邊。
再進一步看,國際足壇近年來也有曼聯、國際米蘭等諸多豪門經歷了易主,為何他們的名字就沒有發生變更呢?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更悠久、名稱限制更嚴格還是投資者更尊重傳統呢?或許以上原因兼而有之,但另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那就是這些俱樂部高度發達的營收模式。
以曼聯在2012年重新上市前公布的財務報表為例,俱樂部在2011年的收入高達3.31億英鎊,其中1.11億來自門票收入,1.17億來自電視廣播收入,另外還有1.03億來自商業運營。倘若格雷澤家族敢于將“曼聯”改成“曼徹斯特格雷澤”之類的名稱,那么只要有一半主場球迷以拒絕購票來表示抗議,其經濟損失將在5000萬英鎊以上。至于原先建立在“曼聯”品牌基礎上的商業運營,顯然也會由于更名而嚴重受損。可見對于歐洲足球俱樂部的投資者來說,背棄傳統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沉重,結果就是大多數投資者都會選擇延續傳統。
中國足壇又是一種什么情況呢?曾幾何時,“申花”被譽為國內最值錢的足球品牌。1999年,一家資產評估事務所宣布申花的商譽價值為11.38億元。可是這個數字似乎僅僅具有“紙面富貴”的意義,從俱樂部實際創收的情況來看,即使在引進德羅巴和阿內爾卡的2012年,申花的門票收入也不過2000萬左右,而這已經是近年來的最高峰。至于其它建立在“申花”品牌基礎上的商業收入,更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相比之下,目前運營一家中超俱樂部所需要的年度投入,已經上升到一兩億只能保級、三五億才能沖擊亞冠的水平。既然投資者無法依靠來自于球迷的微薄收入來填補虧損,也就很難指望他們出于尊重球迷意愿而延續傳統。純粹從資本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似乎還是直接獲得冠名收益這種背棄傳統的行為更劃算,而這正是大部分國內投資者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