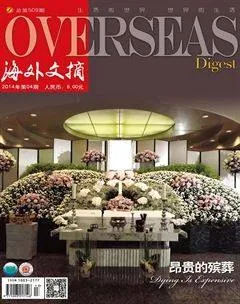兒童日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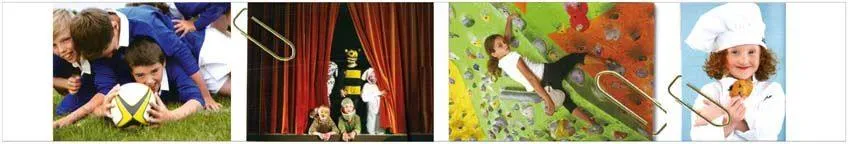

如果達利婭的閨蜜晚上7點半給她打電話,問她這一天過得怎樣,她的回答一定是:“哦,我快要累死了!”
達利婭是一位40歲的米蘭媽媽,有3個孩子,年齡分別是13、11和9歲。“我正在接托米回家,小家伙剛在足球隊訓練完。契卡這會兒和他的朋友盧卡在上網球課,下課后盧卡的媽媽會把兩個孩子一起接回來。呼,幸好卡米拉上完鋼琴課可以自己回來……明天托米還有國際象棋課,契卡有游泳競賽班,而卡米拉上完英語課后還得去學桑巴舞,哦,我想想,她的作業只能在晚飯后做了……這周末如果下雪,我們還得去滑雪俱樂部。所以每個周末,我都祈求雪化得快一點兒,這樣就不用去了。”這時,達利婭停下來喘了一會兒,舒緩了一下情緒繼續說:“雖然現在孩子們才開學一個月,可我覺得快要累死了!”
給孩子們的課余時間排滿興趣班是當下意大利家長們的喜好,也許是出于他們的某種補償心理吧:小時候的他們只能抱著電視機獨自看無聊的肥皂劇,或者在院子里跑跑跳跳……生活太過單調乏味!這就造成了如今一個奇怪的局面:大人們仿佛成了永遠也長不大的孩童,而孩子們剛滿3歲就已經變成了“小大人”。
“這些早熟的孩子們都是小全才。他們過早地接觸了高科技,獨立自主,跟家長們一樣忙。他們是家長們的杰作。”心理治療師克里斯蒂娜·科里說。
而這些“杰作”是通過無數特長班和補習班培訓出來的:從霹靂舞到卡波耶拉舞,從時尚設計班到瑜伽課,從攀巖到薩克斯課……如果你的計步器上顯示你去年走過了1000公里,而你根本沒離開過這座城市,那么恭喜你,你已經和中國家長一樣,成為了最棒“虎媽”。弗朗切絲卡·莫拉蒂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她的瑜伽店有專門為青少年設置的課程,“一開始上課的只有我的女兒和幾個朋友的孩子,后來學員爆滿,甚至有人要求為才3歲大的孩子開設瑜伽課。家長們想通過瑜伽課讓孩子們在爭分奪秒的興趣班后放松身心。”這些“小大人”和家長們一樣,早上8點出門,晚上8點回家。
“這些孩子們每天都非常忙碌,沒時間玩兒”,克里斯蒂娜·科里說,“因為他們被給予了過多的責任,也因此承受著太大的壓力。其實孩子們能來我這里做心理咨詢也挺難得的,因為他們得在游泳、羽毛球等培訓班之間擠出寶貴的時間。”
對于那些選擇了運動(游泳、足球、網球等)作為愛好的孩子們來說,難度也大大提高。意大利出現了很多針對兒童的體育競賽班,孩子們需要在放學后不斷訓練。對很多家庭來說,孩子從3歲開始學英語是必須的,如果孩子到7歲了才開始學中文則為時已晚。
在意大利,音樂是人生的必修課。除了鋼琴、小提琴這些常見的樂器,孩子們還要學一些很少有人接觸的樂器,例如打擊樂器和尤克里里(又名“四弦琴”,起源于夏威夷)。
家長們為了炫耀孩子所學課程的稀有,會互相攀比:滑冰、弗拉明戈舞、啦啦操、冰球,甚至還有樂高培訓(最近十分火爆,教授孩子們用樂高積木造出自動機器人)。音樂劇培訓課和小馬戲團訓練營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兒,此外,還有知識答疑班——可能也很快就會被升級為競賽班了。
“我們愛孩子,盡可能地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個全面人才,好讓他們在長大后擁有一個燦爛的未來。但我們誤解了‘愛’的意義。我們總認為給孩子們足夠的激勵、讓他們盡快成熟起來就是愛。可是孩子們的‘早熟’恰恰反映了大人們的‘不成熟’。我們把孩子們當作大人來對待,其實是在圖省事。”伊萊納·貝爾納爾迪尼說,她是暢銷書《孩子就是孩子》的作者。她的好友辛西婭就是一位焦慮的母親。辛西婭的孩子今年6歲,她說:“現在學英語已經有點晚了,為了讓兒子跟上同齡孩子的進度,我給他買了隨身聽,這樣在他吃飯和走路的時候都能聽英語。現在他參加的興趣班有擊劍、足球、陶藝和戲劇表演,我還打算給他報個樂器班,因為別的孩子都在學,我不能讓他落下。”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警告那些給孩子過多壓力的家長。文章認為,這種教育現狀與家長長期的獨裁密切相關。目前在“競爭性過強”的教育體系下,培養出的是脆弱、抑郁、瀕臨崩潰邊緣的、不幸福的一代。孩子們變得激進而易怒,他們對于學習和活動帶有越來越濃重的功利色彩。那些小型足球趣味賽已經變成大型冠軍爭奪賽,而媽媽們則在球場外不斷地喊:“把他的腿別斷!”
家長們總認為,未來成功的大門只向有準備的人開啟。于是孩子在剛滿6個月的時候就被帶去游泳池學“小狗刨”(筆者那可憐的小侄子就是這一課程的受害者,如今他一看到水池就止不住地哭喊),剛過3歲就得穿上柔道服、學唱日本歌曲,4歲時則身穿比自己體格大很多的救生服學習劃帆船……曾經人跡稀少的意大利華人區——羅馬的維多里奧廣場,也因為“學中文”的熱潮,一夜間成為了最受家長和孩子們青睞的地方。博客撰寫人和作家切奇麗婭無比自豪地對人們說:“在倫敦,5歲的孩子已經開始學第3門語言了,我的孩子上了時尚設計課后就會自己縫紉衣服了……”
“我們把自己的理想強加到孩子的身上,而孩子則沉浸在父母的期望中不能自拔,他們的成功給父母帶來了無比的自豪。可是看看我們到底做了什么?有一次我竟然看到一個男孩在足球訓練前服用鎮定劑!”克里斯蒂娜·科里說。
由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鑒于每一位“小大人”的日程表上都有鋼琴課,難道大家希望未來施坦威鋼琴像大白菜一樣隨處可見嗎?
[譯自意大利《全景》]